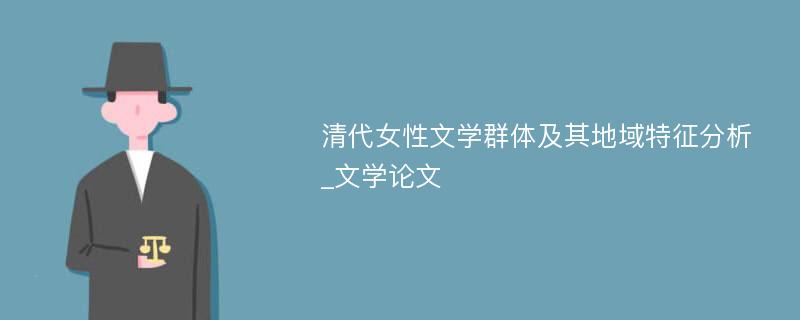
清代女性文学群体及其地域性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性论文,清代论文,群体论文,特征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后,女性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清代女性文学,因女作家数量众多及著述成果突出,更为引人注目。清代女性文学具有家族性、群体性、地域性特征,三者互为因果、相互依存。地域性在三者中更处于中心位置,因为地域是家族与群体活动所依赖的空间。空间内家族与群体分布的广狭决定了女性文学发展的荣衰;一个地域内文学群体的多寡与文学活动的有无决定了本地域女性文学的地位与影响。所以女性文学地域分布的多元性说明了女性文学繁盛的程度,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表现了女性文学发展的复杂态势。分析不同地域间女性文学的同一性,可以发现温柔敦厚的儒学诗教是清代女性文学一直秉承的大传统;而对比同一地域内不同的女性文学群体,又会发现即使在同一地域内仍存在着文学观念的差异性。女性文学内部的复杂与多样性,文学观念的丰富与多层性,都说明女性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系统,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特殊性,对于文学史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女性文学地域分布的多元性:三个核心区域的形成
从王端淑《名媛诗纬》、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黄秩模《柳絮集》、单士厘《清闺秀艺文略》、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记载来看,几乎全国各省都有女作家及作品。著名群体如袁枚随园女弟子群、陈文述碧城仙馆女弟子群、吴江叶氏家族群、蕉园诗社、吴中十子等女性群体,都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不仅苏州、松陵、常州、湖州、阳湖等地的女性群体被关注,福建、广东,甚至偏远如贵州地区的女性文学群体都有文章论及。
从作家数量及著述成就上看,江苏、浙江两省毫无疑问名列前茅,其次是福建、安徽、湖南、江西、山东等省,而江苏、浙江与福建堪称是清代女性文学的三大核心区域。所有这些省份排名在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都有女性诗文总集与选集的编纂。
女性诗歌总集与选集编纂时,由于编纂者对本地女作家的作品所知所得较其他地区容易,收录自然较多;且因编者的桑梓之情,对本地女性及其朋侪之间的往来唱和酬赠之作也多有收录,特别是自己家族女性的作品,收录更多。因而这些总集与选集更详细地记载了编纂者乡里女作家的著述,传述她们的事迹,评论她们的作品,不仅提高了本地女作家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本地女作家的传播范围。如刘云份《翠楼集》、汪启淑《撷芳集》、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闺秀诗钞》记载的安徽女作家数量较其他省份多;王士禄《燃脂集》、《宫闱氏籍艺文考略》及许夔臣《国朝闺秀香咳集》则更多地关注山东女作家的著述;蔡殿齐在编纂《国朝闺阁诗钞》与《国朝闺秀诗抄续编》之后,更编纂了专录江西一省女性诗作的选集《豫章闺秀诗钞》。湖南除了左宗棠辑《慈云阁合刻》外,还有闺秀郭润玉编《湘潭郭氏闺秀集》、毛国姬编《湖南女士诗抄》等,这使得清后期湖南女性文学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事实上,女性诗文选集的编纂对女性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中女性编纂的诗文选集或总集的影响力尤其大。江浙两省女性自己编纂的闺秀诗歌总集最多:江苏有季娴《闺秀集初编》、柳如是《历代女子诗选》、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多种。明末沈宛君的《伊人思》是才女自编诗文总集的开山之作;武进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所收女性著述家近千人,对清前期妇学观念作了回顾和总结。这两部选集的存在就足以说明江苏何以能一直引领女性文学风向。浙江有王端淑《名媛诗纬》与《明代散曲集》、归淑芬《古今名媛百花诗余》、查昌鹓《学绣楼名媛诗选》、王谨《闺秀诗选》、张维《汉魏六朝女子文选》、单士厘《清闺秀正始再续集》与《清闺秀艺文略》、王秀琴《历代文苑简编》、徐畹兰《香艳书札》等。王端淑《名媛诗纬》是清初最重要的一部女性诗歌总集,汇集了800多位女诗人的作品,保存了大量的明末清初女性文学创作及活动的资料,具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
福建除了胡履春《麦浪园女弟子诗》、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丁芸《闽川闺秀诗话续编》外,还有闺秀薛绍徽的《女文苑》与《闺秀词综》、陈芸《小黛轩论诗诗》等女性编纂的诗文总集、诗论。薛绍徽为陈芸所作的序言中说自己“修《女文苑》一书,即以尔所述者(《小黛轩论诗诗》)为目,选列诸家名作,并复以尔之所谓无可附丽者,庶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致付诸荒烟蔓草湮没也”。①这种怀着对女性理解之同情的心态,不愿前代闺秀作家“付诸荒烟蔓草湮没”而编纂女性诗文的行动,是一种文学自觉性的表现。
要成为女性文学核心区域,除了女作家数量及著作成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本地女性的文学自觉意识。这需要女性在家族和地域文化的熏陶、润泽下,有意识地建构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并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与文学理论。所以在这些排名靠前的省份中,能与江浙女性文学相辉映的,只有福建省。其它省份尽管女性文学成就斐然,如安徽省与江、浙两省共同构成清代的人文繁盛之区,②出现很多女性作家与著作,但仍不能成为核心区域,因为没有形成皖派女性文学理论体系。闽省之所以能够与江浙并列为女性文学三大核心地域,则是因为有闽派的女性文学传统与文学理论。
江、浙、闽三省的女性诗文选集中有很多是女性自己编纂的,更重要的是这些选集与闺秀诗话还建构了自己的女性诗歌理论。只有形成自己的女性文学传统与文学理论的地域,才拥有强烈的辐射力,成为引领女性文学发展的核心区域,促进女性文学整体的繁荣与进步。目前所知闺秀诗话约30种,编纂者为江浙女性的有王端淑《名媛诗纬》、沈善宝《名媛诗话》、王琼《爱兰轩名媛诗话》、张倩《名媛诗话》、杨芸《金箱荟说》、苏畹兰《名媛诗话》、蒋徽《闺秀诗话》、苏慕亚《妇人诗话》、雪平女士《红梅花馆诗话》、施淑仪《国朝闺阁诗人征略》等,其中以王端淑的《名媛诗纬》、沈善宝《名媛诗话》最负盛名也最有价值,尤其是王端淑的《名媛诗纬》最能代表清代闺秀诗话的水平。不仅因为它出版时间较早,更重要的是,在清初博大恢弘的学术氛围下,王端淑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反思前代的文学理论,对闺秀文学理论加以总结归纳,赋予了“秀”这个男女都适用的诗学话语以新的内涵,使之更具女性特色,成为闺秀诗学的核心审美范畴。③
福建薛绍徽的《闺秀词综》、《女文苑》及陈芸《小黛轩论诗诗》除了对历史上的女性文学谱系加以梳理外,还特别关注福建地区女性文学的发展,刻意构建了闽派闺秀诗学的历史谱系,发扬闽地“里闾之光”。薛绍徽以江采频、陈金凤、孙夫人、阮逸女等人为闽派女性诗学的开端人物,“是以江采频斛珠慰寂,陈金凤艳曲乐游,孙夫人柳结同心,阮逸女鱼游春水,纵内言不出,尤有词翰流传。而女作登于男,实秉山川灵秀”④。到了清初,闽派女性文学发展迅速,出现了以光禄派闺秀文学群体为首的闽派女性诗歌潮流。薛绍徽序丁芸《闽川闺秀诗话续编》云:“迨国朝以来,衍光禄一派。黄家姊妹,《香草》留其遗徽;梁氏妇姑,茞林创为专集。一则备列附编,一则如传家乘。曷若博搜载记,扬彤管之辉光;细刻苕华,征故乡之文献乎?故耕邻先生有《闽川闺秀诗话》之续焉。”⑤这里提到的光禄一派,是指福州许氏家族才女群体。陈芸《小黛轩论诗诗》载:“福州城内有巷曰光禄坊,宋法祥院旧地。中有小丘曰玉尺山。熙宁时知州事程师孟以光禄卿游其地,并书‘光禄吟台’四字刻于石。明末为邑绅许豸宅。清初,豸子友仍居之,著《许有介集》。其家妇女皆能诗,多与戚属女眷相赠答,诗筒往返,婢媪相接于道。轻薄子弟,恒贿赂而盗窃录之,称‘光禄派’。”⑥福建闺秀诗坛在光禄派大盛之后,以黄任与郑方坤两个家族女性群体最为著名。陈芸说“派传光禄记吾乡,姊妹黄家草亦香”⑦,光禄派才女一直到乾隆时期仍活跃在福建诗坛。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卷一载:“乾隆间,吾乡闺媛之能诗者,无过素心老人。”又载“素心名琛,字德瑗,瓯香先生友(即许豸之子友)曾孙女”,即是光禄派传人。此后,梁章钜家族才女群大放异彩。薛绍徽母女则是继梁氏之后的又一著名女诗人家族。薛绍徽及陈芸对历史上女性文学谱系的整理及刻意构建,使得闽派女性诗学具有了完整性与理论性。
更可贵的是,薛绍徽母女在提倡新女学的同时,怀着历史的使命感及对女性文学的终极关怀之情,积极致力于闺秀文学传统的延续。陈芸《小黛轩论诗诗》自序说:“方今异世,有识者咸言女学。夫女学所尚,蚕绩、针黹、井臼、烹饪诸艺,是为妇功,皆妇女应有之事。若妇德、妇言,舍诗文词外末由见。不于此是求,而求之幽眇夸诞之说,殆将妇女柔顺之质皆付诸荒烟蔓草而湮没,微特隳女学,坏女教,其弊诚有不堪设想者矣。家慈因是忧郁成疾,芸所滋惧也。”⑧薛绍徽母女“若妇德、妇言,舍诗文词外末由见”的观念,揭示了传统女学的精粹。她们通过女性文学总集与选集的编纂来诠释女性文学传统的正统性,这对于女性文学传统的传播、延续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
因此,无论从女性诗文总集编纂、闺秀诗话撰写、闺秀诗派群体的规模以及女性诗学理论的构建哪方面来看,福建都有与江苏、浙江并称的资格。特别是清代后期,福建不仅有薛绍徽等人编的诗文总集与闺秀诗话,还出现了萧道管《列女传补注》等学术著作,足以傲视他省,与江、浙并列为清代三大女性文学核心区域。这些核心区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带动了了本地女性文学的繁荣,并且通过各区域闺秀精英的共同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氛围,更多的女性参与到文学创作中,这样具有引领和辐射作用的核心区域与充满创作活力的遍布全国的女性文学创作区域共同构成了丰富与多元的女性文学图景。
二 跨地域的同一性文学观念: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传统
女性写作一直备受诟病,因此明清时期很多学者与闺秀精英试图建构一个以《诗经》为源头的文学传统,以彰显其写作的悠久性。与之相适应,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也被移植为女性文学的基本规范。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一则可以昭示女性写作的正统性,使文学活动具有合法性;二则与传统的妇德观念一致,与女性的气质秉性相契合;又因女性文学活动空间的不断扩大,女性之间的交游网络逐渐扩展,文学雅集活动愈加频繁,就更需要这种诗教传统为女性文学活动的合法性正名,因此在整个清代,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一直在闺秀诗歌的评论中被发挥和传承。
邹漪《红蕉集自序》曰:“《三百》删自圣手,《二南》诸篇什七出于后妃嫔御、思妇游女。”⑨承此观点,戴鉴序《国朝闺阁香咳集》说:“昔夫子订《诗》,《周南》十有一篇,妇女所作居其七。《召南》十有四篇,妇女所作居其九。温柔敦厚之教,必宫闱始。”⑩类似的说法不断积累,使得《诗经》是女性文学源头成为一种常识,而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闺秀诗学的基本规范。
清代的闺秀诗人一直都谨守着这一文学规范。清初王端淑编纂《名媛诗纬》,说:“客问于予曰:‘《诗三百》,经也,子何独取于纬也?《易》、《书》、《礼》、《乐》、《春秋》,皆有纬也,子何独取于《诗》纬也?’则应之曰:‘日月江河,经天纬地,则天地之诗也。静者为经,动者为纬;南北为经,东西为纬,则星野之诗也。不纬则不经。昔人拟经而亡,宁退处於纬,之足以存经也。《诗》开源于‘窈窕’,而采风于‘游女’,其间贞淫异态,圣善兴思,则诗媛之关于世教人心如此其重也。’”(11)这表明女性不仅宣告了闺秀诗学的典范意义,同时也阐明了“诗媛之关于世教人心如此其重”的女性诗教观。
随着女性文学活动空间的扩大、跨地域的女性交际网络的扩展,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也被不断强化。顾若璞(1592—1681)《延师训女或有讽故作解嘲》诗云:“不事诗书,岂尽兴生。”“大家有训,内则宜明。”顾氏孙女钱凤纶、孙媳林以宁等人组成的蕉园诗社成员都秉承这个传统。曾为蕉园诗社“祭酒”的柴静仪(1638?—1692)有《诸子问余诗法口占二绝句直抒胸臆勿作诗观》诗云:“更诵葩经与骚些,温柔敦厚是吾师。”肯定女性学诗基本方法就是背诵《诗经》、《离骚》,体会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女性跨地域的交往逐渐普及。《青浦闺秀诗存》载青浦闺秀曹鉴冰“与顾启姬等结淀滨诗会”。顾启姬名姒,是西泠蕉园诗社成员,《青浦闺秀诗存》在“曹鉴冰”条下还记载蕉园诗社的另一个重要成员林以宁也曾参与唱和,林氏“以闺友顾姒在青,来与唱和,数月即去”(12)。所以淀滨诗会至少有曹鉴冰、顾姒、林以宁等人参加,这是清初浙江与江苏不同地域间闺秀密切交往之例。闺秀们通过这种文学交游网络建立起自己的文学活动场域,在这个场域里,随着交游的扩大,文学活动的增加,温柔敦厚的传统也在不断加强。
清中叶方芳佩是杭州闺秀之首,杭世骏称其为“当今巾帼中所仅见”,被认为是蕉园诗社的传人。徐德音《在璞堂吟稿序》提到:“吾乡闺媛能诗者,惟蕉园五子,更倡迭和,名重一时。迄今六十年来,风雅浸衰,良可慨也。顷读方芷斋名媛《在璞堂吟稿》,其修辞琢句,清真沉郁,不类弱女子为之。加之博览群书,进而益上,则蕉园替人,舍芷斋其谁欤?”(13)徐德音还曾作《附和芷斋侍史》诗,“蕉园旧社重凝香,作手今推在璞堂”一联又重申方芳佩是蕉园诗社的后继之人的重要地位,其诗学自然也秉承诗教宗旨。
方芳佩与福建才女许琛交往密切,并且在其死后为之刊刻诗集。沈善宝《名媛诗话》卷四载:“三山许素心德瑗以苦节闻于当世,有《疏影楼集》。方芷斋随任之闽,耳名往访,诗篇倡和,时有馈遗。素心爱写梅菊,晚年窘甚,售诗画以自给。殁后,芷斋序其遗稿而梓之。其投芷斋诗有‘千仞龙门非易到,布裙来拜卫夫人。’芷斋之居贵不骄,爱才若命,亦可敬也。又有《题画赠芷斋》云:‘冷淡生涯二十年,枝枝叶叶锁寒烟。与君载去西湖畔,记取愁人闽海边。’”(14)许琛在闽与“闺秀廖淑筹、庄九畹、郑镜蓉、黄淑畹、黄淑窈结社唱和,诗学益进。后家益落,饔飨不继。会李夫人筠心、方夫人芳佩、福恭人宜鸾闻其名,结为文字知,皆厚资之,始得自给”。(15)郑镜蓉是著名诗人郑方坤之女,姊妹一门风雅。据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卷二载:“荔乡先生(郑方坤)一门群从,风雅蝉联,膝前九女,皆工吟咏。(中略)自古至今,一家闺门中诗事之盛,无有及此者。”(16)黄淑窕、黄淑畹是福建诗人黄任之女,姊妹二人的诗文“为时传诵”,“时人皆称之。”(17)许琛以“苦节闻于当世”,故而才德并称;郑镜蓉亦是“早寡以节终,得旌表”;廖淑筹则系“夫卒归里,困踬无以为生,乃写花竹以自适,课子孙读书。有‘清时弦诵重,廉吏子孙贫’句,为时传诵”。(18)可见以许琛为中心的闽县女诗人群体大多以节妇著称,而其诗文风调自然不离诗教传统。故而在许琛与方芳佩等人形成的系连了江南与福建女性诗坛的女性交游网络中,诸才女的诗歌写作无不秉承温柔敦厚之旨。
江苏吴中以张允滋为首的清溪诗社,则倡导以“以温柔敦厚之旨,写和平庄雅之音”。恽珠《正始集》卷十六载张允滋与“同里张紫蘩芬、陆素窗瑛、李婉兮嫩、席兰枝蕙文、朱翠娟宗淑、江碧岑珠、沈蕙孙纕、尤寄湘澹仙、沈皎如持玉,结清溪吟社,号吴中十子,媲美西泠”。(19)清溪诗社又称吴中十子,马素贞曰“诗道性情,故必以温柔敦厚为宗”,“余尝读任心斋先生所辑《吴中十子合集》,或议论沉雄,或词旨俊逸,不专一家,而究其旨归,殆与温柔敦厚之风庶几焉。”(20)清溪诗社虽在吴中,其诗风却受到杭州蕉园诗社流风余韵的影响。江珠《采香楼序》说:“惟昔西泠闺咏有十子之目,清溪欲步其风,乃先后酬赠篇什采集一编,为《十子诗抄》。”(21)可知张允滋等吴中十子是以蕉园诗社为榜样创建的。蕉园诗社对清溪诗社的这种跨地域影响与闺秀的师承不无关系。张允滋曾拜徐若冰为师,任兆麟《清溪诗稿叙》说:“清溪女史幼禀家训,娴礼习诗,尝以韵语质香溪徐夫人,香溪亟赏之。”(22)张允滋《潮声阁集》中有《灯花和香溪徐夫人韵》诗,小序曰:“香溪名暎玉,字若冰,昆山人,著有《南楼吟稿》行世。”徐若冰与杭州女诗人方芳佩交好,徐德音《南楼吟稿序》曰:“美人丽玉(谓芷斋夫人),林下盘桓;仙子飞琼(谓云清夫人),云端翰札。香灯小社,托毫素以题襟;花月深宵,话水天而接席。”(23)描绘了徐若冰与方芳佩、钱浣青联袂唱和的场面。沈大成序徐若冰《南楼诗稿》,称其诗“庶几窃附于《芣苢》、《汝坟》之义”,(24)肯定了徐若冰诗歌与诗教的密切关系。
扬州王琼与孔璐华等人的曲江亭唱和群体不仅遵循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更将之发扬光大。王琼《同音集序》曰:“尝谓选诗难,选名媛诗尤难。女子教本贞静幽闲,温柔敦厚,孔子列为风诗之首、王化之原,实基於此,抑何重也!后之选女子诗者,无虑百数十家,大率谓女子能诗,便称韵事,采录失之太宽,甚至以秾纤新巧谓颖慧,淫佚邪荡为风流,相推相许,近於寡廉鲜耻而不知,呜呼,可悲矣!”(25)王琼在此力斥“秾纤新巧”、“淫佚邪荡”的诗风,提倡风雅,以温柔敦厚为旨归,与清溪诗社的主张全然一致。说来王琼与清溪诗社成员也交往密切,任兆麟甚至说王琼是其女弟子。王琼有《怀清溪夫人并呈林屋先生》、《题潮生阁诗集后》等诗,张允滋闻王琼“诗宗唐贤,取所著《爱兰集》附刻于(《吴中女士诗抄》)后,时艳称之”。其诗集有张允滋题诗,张芬题序。这些闺秀的交游与家庭背景、个人兴趣等很多因素有关,但秉承相同的诗学宗旨,无疑会使她们更加亲密。
即使崇尚性灵的随园女弟子也不例外。随园女弟子席佩兰《与侄妇谢翠霞论诗》曰:“积理在读书,精粗要分晰。葩经三百篇,一一贞淫别。种树取芬芳,配壅必高洁。世俗见迂拘,谓妇宜守拙。余曰理不明,究于礼多缺。请观《周南》诗,谁非淑女笔?”(26)也在强调诗教传统的幌子下肯定了女性写作的正当性。
一直到清末,单士厘(1863—1945)《国朝闺秀正始集再续集》、《清闺秀艺文略》的编纂原则仍秉承这一诗学传统。《再续集》将恽珠、翁端恩、汪嫈、吴宗爱四人列于卷首,《凡例》说:“兹选一遵恽例,以雅正为主,故袭名正始。”“恽珠”条下按语说:“《正始》选例严正,续选宗之,故以恽作冠首,用志仰止。”(27)单士厘所提倡的雅正,就是温柔敦厚的换一种说法,这一儒家诗教传统一直被闺秀诗学奉为圭臬遵循着,在跨地域的女性诗歌交往和诗学言说中显示出一种趋同的一致性。这不用说是与封建社会强大的政教传统相关并受其制约的结果。
温柔敦厚的儒家诗学传统的坚守与文学创作的繁荣表明了心怀使命感的闺秀才女以严肃的态度、不懈的努力已经成功创建的一个具有学术性、艺术性、完整成熟的女性文学生态系统。这个文学生态体系的存在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文学史,而且使清代文学史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特质,其文学史及学术史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 同一地域文学观念的多层性
由以上论述可知,女性文学到清代明显已建构起以《诗经》为依托的大传统,但问题是,自古以来地域文化就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具体到特定的诗人群体,不可能不受到地方文学流派、家学风尚、个人兴趣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某些特异的倾向,从而造成不同地域之间文学观念和风尚的差异性。在这个问题上,清代女性文学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内容。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的记载,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女性著述囊括经史子集,包括诗词集、女教、史学、科技、学术等不同类型的著述;福建、湖南、江西女性的著述种类也较为丰富;广东偏重于女教、史学、文章等著述;山东、河南则偏重于学术、史学、文章等著述。同一地域内部女性文学群体的差异性则更能说明女性文学观念的多层性,这种多层性凸显出女性文学的丰富与多样生态景观。
周曰惠的绿凤仙花唱和群、随园苏州女弟子群虽然都隶属于江苏苏州,却各具特色。绿凤仙花唱和群体充满了浪漫闲暇的意味。亚里士多德说“人惟独在闲暇时才有幸福可言,恰当地利用闲暇是一生做自由人的基础”(28),在这种闲暇中读书交友、作画吟诗、享受生活的雅集唱和,是乾嘉才女诗意栖居之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这种闲暇雅集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审美愉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诠释了闲暇的哲学意义,通过闲暇雅集的方式追求文学的终极价值,这也是闺秀才女积极参与世事的一种表现,体现了文学女性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与这种以文学价值为终极目的的自由闲暇的雅集唱和不同,随园苏州女弟子群的雅集唱和背后充满了能使个人才名流传久远的渴望。席佩兰《闻宛仙亦以弟子礼见随园喜极奉简》诗有“诗教从来推内则,美人兼爱擅才名”的句子。屈宛仙、席佩兰等人曾作《蕊宫花史图》来记录嘉庆元年的一次雅集唱和。孙原湘详细记载雅集始末:“柔兆执徐之岁百花生日,婉仙夫人招集女史十二人,宴于蕴玉楼,谋作雅集,以传久远。患其时世妆也,爰选古名姬,按月为花史”。“自正月至十二月,为谢翠霞、屈婉仙、言彩凤、鲍遵古、屈婉清、叶苕芳、李餐花、归佩珊、赵若冰、蒋蜀馨、陶菱卿、席佩兰,长幼间出,不以齿也。爰命画工以古之装写今之貌,号《蕊宫花史图》,两易寒暑乃成。”(29)这种谋作雅集,以传久远的想法,与周曰惠等人雅集的闲适自得明显不同。
江苏扬州的曲江亭唱和群体以王琼家族及阮元夫人孔璐华等家庭成员在王豫家中曲江亭唱和、结集为《曲江亭唱和集》(30)而得名。曲江亭唱和从表面上看,不过是闺秀偶然雅集唱和的一段佳话,但王琼真正的意图确是希望将真实的曲江亭雅集唱和与历史上曲江亭的辉煌联系在一起,借助孔璐华圣裔身份所具有的古典意义,使被记录和镌刻的女性文学活动成为一种经典和永恒,从而使扬州地域女性文学成为女性文学史的典范和正统。
曲江亭在王豫家宅翠屏洲之右,现有张崟为王豫作的《曲江亭图》传世。阮元《题曲江亭图》曰:“此地乃汉广陵曲江枚乘观涛处。”(31)枚乘《七发》说广陵潮“春秋朔望辄有大涛,声势骇壮,至江北,激赤岸,尤为迅猛”,因其壮观之势,广陵潮的盛况常见于诗赋。后因江苏曲江广陵潮不及浙江钱塘潮闻名,渐被淹没。正如清代杭州蕉园诗社的雅集形式及其对女性文学正统地位的建构,使之成为女性文学的标志性的符号,清溪诗社诸闺秀就是慕蕉园十子之风采而号“吴中十子”,所以梁乙真说:“终清之世,钱塘文学为东南妇女之冠,其孕育滋乳之功,厥在此(蕉园诗社)也。”(32)王琼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借助曲江亭的历史记忆功能来建构扬州女性文学的辉煌,确立其在女性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使扬州地域女性文学成为女性文学主流。
女性文学作为一支独立的文学分支,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是由其自身繁荣度与成熟度决定的。数量众多的著述成果足以说明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上面所论述的闺秀才女对文学本质的哲学思考;闺秀才女对于自身的文学价值及本地域文学地位的重视与行动,足以证明女性文学体系内部的复杂性与成熟性。深入研究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不仅可以丰富文学史的景观,而女性差异性的文学观念也可以促进文学理论的研究。这些足以说明了女性文学所具有的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⑧(14)(16)(17)(18)王英志:《清闺秀诗话丛刊》,第1520页,第263页,第263页,第1531页,第1531页,第1519页,第414页,第213页,第1846页,第210页,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②参见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联姻与地域文化传统的形成》,《华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③参见宋清秀:《秀——清代闺秀诗学的核心概念》,《徐州师大学报》2011年第4期。
⑨⑩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第897页,第9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1)王端淑:《名媛诗纬》,清康熙间刻本。
(12)钱学坤:《青浦闺秀诗存》,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
(13)方芳佩:《在璞堂吟稿》卷首,清乾隆刊本,辑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0册。
(15)(19)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清道光刊本。
(20)(21)(22)任兆麟:《吴中女士诗抄》,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23)(24)(26)胡晓明:《江南女性别集初编》,第175页,第176页,第186页,黄山书社2008年版。
(25)王琼:《同音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刊本。
(27)单士厘:《国朝闺秀正始集再续集》,清刊本。
(28)J.曼蒂:《闲暇教育理论与实践》,春秋出版社1989版。
(29)孙原湘:《天真阁外集》,上海扫叶山房民国十四年(1925)石印本。
(30)王琼:《曲江亭唱和集》,国家图书馆藏清刊本。
(31)阮元:《揅经室集》,第885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32)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第38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