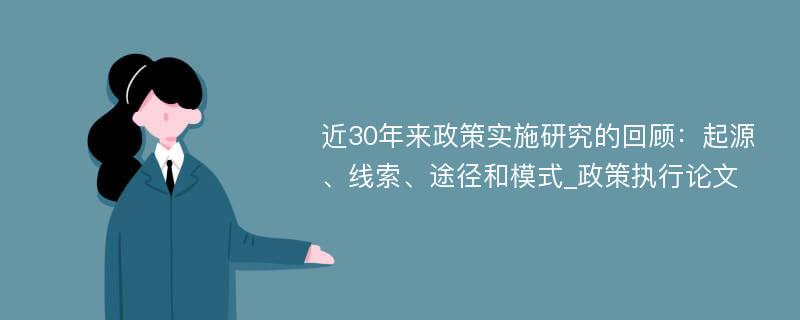
政策执行研究三十年回顾——缘起、线索、途径和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三十年论文,线索论文,模型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执行在英文文献中对应的词汇有Administration,Implementation,Enforcement,Execution。Administration泛指行政学,学者们一直也没有将Enforcement与Execution这两个语词作为一个行政学的研究领域来看待。Implementation这一语词则因为佩尔兹曼(J.Pressman)和威尔达夫斯基(A.Wildavsky)在1973年出版了《执行:华盛顿的宏大期望是如何在奥克兰破灭的,或为什么联邦政府计划被执行了一点是令人惊奇的》(Implementation:How Great Expectations in Washington are Dashed in Oakland)一书,揭示了政策制定(目标)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偏差,而成为指称政策科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一个特定的研究范畴的语词。至今政策执行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三代的发展。
一、政策执行的第一代研究和自上而下的途径
1973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是执行研究的第一代。第一代研究具有以下特征:(1)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Top-bottom approach或者top-down approach)。(2)第一代研究主要是小规模的案例研究,比如对奥克兰项目的研究等等。案例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总结执行成功和失败的因素,还没有形成一个关于执行的一般性的理论框架。[1](P34—36)
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Top-bottom approach或者top-down approach)是帕雷特(Susan Barrett)和佛杰(Colin Fudge)对7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这一阶段政策执行研究主导途径的概括。自上而下途径的最早代表人物是佩尔兹曼(J.Pressman)和威尔达夫斯基(A.Wildavsky),随后史密斯(T.B.Smith)提出的政策过程模型(1973)、霍恩(C.E.VanHoer)和米特(D.S.Meter)提出的系统模型(1975)、马兹曼尼安(D.A.Mazmanian)和萨巴蒂尔(Paul A Sabatier)提出的执行综合模型(1979)都采用了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
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的基点是解释为什么政策过程出现或没有出现成功的结果。这样的解释事先预设了一个所要取得的明确目标,这一点可以称之为“目标假定”。与这种分析性的目标假定相适应,政策执行研究的(价值)目的是怎样使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
第二,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待政策执行问题。“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观意味着:决定的重要性取决于它是在科层等级的哪一层做出的;因此,最重要的决策是由政府机构的最高人物做出的,而处于科层等级中级层次的人们,只是执行决策罢了。”[2](P61)
第三,“政策过程被认为是由一系列具有逻辑关系的阶段组成:从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意向经由决策再到行动,政策执行开始于政策制定终止的地方。
第四,区别作为创设初始条件的政策制定(意向合法化)和把政策假设转化为行动的项目设置。
第五,政策执行就是将政策付诸行动的过程。主要着眼于对政策执行机构的管理(合作、协调等)”。[3](P10)科层组织的原则和管理方式是提升政策执行能力和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第六,重视外部环境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还带有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印记。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这一研究途径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暴露了自身的缺陷,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很多批评,具体表现为:
第一,过多的关注中央行动者的目标和策略,其他行动者在执行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被忽略了。
第二,所谓的完美的行政的必要的条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具备的(例如资源的持续稀缺)。
第三,为了应付不确定性,各种组织都不可避免的拥有自由裁量权,基层官员的活动将由此产生“控制赤字”,因为他们发展出了应付压力的各种办法。
第四,通过强调中央的目标,不但忽视了基层官员的适应策略,也忽视了政府行为的意外结果。
第五,某些政策并不具有(已有的政策从来都不具有)明确的目标,他们通过一系列活动者的复杂互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展和演变而来,因此,并不存在明确的政策评估标准。
第六,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理论区分,在执行过程中无法维持,因为政策是在执行的实际过程中制定和修正的。”[4](P6)
二、政策执行的第二代研究和自下而上的研究途径
自下而上的研究途径(Bottom-top approach或Bottom-up approach)是70年代末以来执行研究的主导研究途径。李普斯基(M.Lipsky)对街头官僚(Street level Bureaucracy)的研究,埃尔默(Richard F.Elmore)对追溯性筹划(Backward mapping)的研究,贺恩(Benny Hjern)和波特(David.O.Poeter)对执行结构(implementation structures)的研究是主要的代表。
1975年维泽尔勒(R.Weatherley)和李普斯基(M.Lipsky)在《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了“街头层次的官僚和制度创新:特殊教育改革执行”(Street level Bureaucracy and Institutional Innvation:Implementing Special Education Reform)一文,随后李普斯基(M.Lipsky)在1977年发表了“街头官僚的理论面向”(Toward a Theory of Street Level Bureaucracy)一文,在1980年出版了《街头官僚》(Street level Bureaucracy)一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街头官僚理论。街头官僚理论是自下而上执行研究的典型代表,其核心思想在于: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中的作用,并不像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认为的那样,消极地、被动地执行上级的政策,恰恰相反,街头官僚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自由裁量的余地。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即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街头官僚的权力、利益、意愿和政策执行能力直接相关。[5]
追溯性筹划理论是自下而上研究途径的又一重要代表。1980年埃尔默(Richard F.Elmore)在《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上发表了“追溯性筹划:执行研究与和政策决策”(Backward mapping:implement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decisions)一文。作者区分了向前性筹划(Forward mapping)和追溯性筹划(Backward mapping)两种不同的政策执行的研究方式。与向前性的筹划相对,追溯性筹划是“从作为政策所要解决问题中心的个人和组织的选择,到与那些选择密切相关的规划、程序和结构,再到用以影响那些事项的政策工具,以及可行的政策目标的追溯性的推论。”追溯性筹划这一研究方式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环节:(1)研究出发点不是领导的意图,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正是这种行为导致的现象,产生了政策干预的需要;(2)分析一系列被认为能够影响这种行为的组织运作过程;(3)描述这些组织运作所预期的效果;(4)然后,明确执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对现实政策目标所发挥的作用。(5)如欲实现各自的目标,所需要的资源是什么?[6](P601—612)
执行结构理论也反映了自下而上的研究途径。1981年贺恩(Benny.Hjern)和波特(David.O.Poeter)在《组织研究》(organizationalstudies)上发表了“执行结构:一种新的行政分析单元”(implementation structures:a new unit of administrative analysis)提出了“执行结构”的概念。执行结构即是一种分析单元,又是区别于市场和官僚组织,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协调和联系方式。这种方式通过公共政策这一纽带将政策执行涉及的各种组织以相互依赖的结构联系起来。执行结构不通过权威设立,是在组织成员自我选择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执行结构的正式程度较低,权威关系不如行政组织系统那样明显;所处的社会环境较容易变动,其行动集合体并非具有法律地位的实体;参加项目执行的决定是模糊的,基于同意和相互妥协”。[7](P211—227)执行结构的概念提出后,学者们对其做了深化和细化,形成了大量的文献。在执行研究的第三代中,执行结构的概念进一步深化为政策网络的概念。
总结上述的研究成果,自下而上的研究途径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重视基层官员的作用。街头官僚(基层官僚)拥有巨大的行政裁量权,接近执行现场,拥有信息优势,对政策执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自下而上的研究途径将基层官员看作政策执行和政策创新的重要因素。
第二,认为政策执行活动是多组织或个人(包括公众、社会组织、国家行政机关等)之间互动的过程。通过组织间和个人间的互动形成的执行结构是影响政策执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第三,从基层和个人出发看待政策执行问题,政策链条中的底层是观察和分析政策执行的基点和焦点。
第四,政策执行过程是不同行动者表达自己意志,提出动议,行动者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过程。
第五,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是不可分离的,制定政策是执行过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主张用政策和行动关系取代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二分。
自下而上的研究途径也有自身的缺陷,学者们对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过分的强调基层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行动者的认知被辨认出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解释。讨价还价规则的起源,互动者之间资源的拥有情况,每一个参与者可资利用的策略范围等等,也有待解释。
第三,自下而上的主张者一开始关心的并非是政策执行问题(即政策执行了没有),而是关注在一个特殊的政策领域,实际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四,对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的批评有失公正,过分夸大了许多因素;有些政策确实具有明确的目标,因此,弄清楚这些目标是否实现是相当重要的。政策形成和执行的区分也并非是理论的精确描述,因为所做出的政策决定确实框定了地方或基层行动的决策环境。行动者相互作用的无处不在并没有取消这种区分。[8](P7)
第五,放弃政策形成和执行的二分法,使人们很难区分政治家和文官的相对影响。故尔排除了进一步分析民主负责和官员自由裁量这个问题的可能性。
第六,将政策过程视为一个变动的无缝隙之网,其中没有决策点,就排除了政策评估的可能性(因为没有政策可以评估)。同时也无法进行政策变迁的分析(不存在界定的政策之变动)。[9](P276)
三、政策执行的第三代研究和综合途径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执行研究的第三代。(1)第三代研究试图综合和超越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理论,具有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的多样性的特征。“就执行研究而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争论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它们各自力量的认识,并且综合的理论成就是众多的。”[10](P283)(2)第三代研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将执行扩展到府际关系的范围和分析层面。
这种综合的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成果达成了共识,肯定其取得的成果的同时认识到了两者的局限。对以往理论成果的总结和省视是理论综合的前提。
其次,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途径的超越和分析工具的丰富化。自从80年代以来,执行研究途径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分析工具也变得丰富起来。大规模研究、政府间关系研究、制度分析、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性选择、统计和计量方法被广泛的运用到执行研究当中,这些有助于综合的理解执行问题。
最后,第三代研究概念的形成。郭锦等人(Malcolm L.Goggin)在1990年出版了《朝向第三代的执行理论和实践》明确提出了第三代研究途径(a third-generation approach)。第三代研究途径区别与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研究途径,主张建立动态的执行图景。第三代研究途径运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 approach)以建立了一个整合模式来研究复杂的多层次的、多变量的执行问题,特别是府际关系问题。
与上述综合的趋势相关,20世纪80末期以来,涌现出了众多的、有代表性的执行理论、途径和模型。比如:门泽尔(Donald C.menzel)的组织间模型(1987),郭锦等人(Malcolm L.Goggin)的府际关系模型(1990),萨巴蒂尔(Paul A Sabatier)的政策变迁和学习模型(1993),麦特兰德(Richard E.Matland)的不明确冲突模型(ambiguity-conflict)(1995),瑞恩(N.Ryan)的综合途径(integrated approach)(1996),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途径等等。执行研究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综合和多元的时代。
1.门泽尔的组织间模型
1987年门泽尔(Donald C.Menzel)回顾了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的执行理论后指出:以往的执行研究忽视了组织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也没有一个组织理论或模型能很好的应用到政策执行研究(比如: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和自下而上的研究途径都不能很好的解释冲突和协调)。为此,门泽尔采用组织理论的分析工具,构建了政策执行的组织间模型。政策执行的组织间模型认为:执行的成功不但依赖于组织自身的选择,还依赖于其他组织的选择。该模型将焦点集中在互动网络中组织的相对属性上,认为组织间的依赖包括资源依赖和结构依赖两个重要的方面。[11](P3—19)
2.郭锦等人的府际关系模型(1990)
1990年,郭锦(Malcolm L.Goggin)等人提出了府际关系模型,该模型认为:第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冲突或合作关系;第二、州政府具有自主裁量权,可以解释联邦计划的内容也能够了解地方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不同时间或不同管辖权下具有不同的执行模式。
府际关系模型包括三个变量:(1)因变量:即州政府的政策执行。(2)自变量:包括两项:第一项为联邦政府层次的诱因与限制;第二项为州与地方政府层次的诱因与限制,两者形成交互依赖关系。(3)中介变量:包括州政府本身的决策后果与州政府本身的能力。前述自变量与中介变量构成州与地方政治的执行次级系统(implementation subsystem)。这一系统包括下列要素:州与地方政府机关首长、机关组织、州发言人、州立法委员、地方政府层次的行动者、州政府层次的能力、回馈等,这些要素都是互动性的、互赖性的、多元性的动态过程。[12]
3.萨巴蒂尔的政策变迁和学习的宣导联盟模型
萨巴蒂尔(Paul A Sabatier)在1993年出版了《政策变迁与学习:一个宣导联盟途径》(Policy Changand Leaning:An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一书,提出了政策变迁与学习的宣导联盟模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of policy change)。该模型建立在政治系统论、精英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的基础之上,认为政策执行过程本身就是改变政策内涵、政策取向学习(policy-oriented learning)的过程。这一模型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内容:[13]
(1)政策变迁受到两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一种是,相对稳定变项(relatively stable parameters),包括问题领域的基本特征、自然资源的基本分配、基本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结构、基本法制结构等。另一种是动态事件变迁(dynamic events),包括社会经济条件与科学技术的变迁、系统治理联盟(systemic governing coalitions)的改变、其它次级体系的政策的变迁等。
(2)行动者通过宣导联盟影响政策。行动者通过宣导联盟影响政策的基本过程是:具有相似信仰和利益的行动者构成联盟,联盟成员采取若干宣导与公关策略,影响政府的政策,政策的结果再回馈到宣导联盟。宣导联盟之间通过政策中介者(policy brokers)加以协调,以形成平衡的政策影响力。
(3)政策变迁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取向的学习过程。政策次级体系内的行动者从互动过程中修正自己的想法或行为,累积互动的经验,从而形成新的信仰体系,这就是一种相互学习的动态过程。
4.制度分析理论模型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都是关于执行过程的单一向度的分析,忽视了执行过程中多元主体的互动和由此形成的制度共识。“事实上所有的政策和规划都依赖制度行动,而且制度框架现在对于政策执行而言愈加普遍了,政策执行包括了远在官僚机构和市场传统焦点之上的特征。”[10](P283)
以奥斯特罗姆(Vincent.Ostrom)为代表的印第安那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试图将公共物品理论和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开创了一套理解复杂制度安排的方法——“制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这一框架具有以下要点:
首先,倡导多中心治理。“唯有多中心治理能够培养和维持地方社群的自治能力。”“‘多中心’意味着有许多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它们在竞争性关系中相互重视对方的存在,相互签订各种各样的合约,并从事合作性的活动,或者利用核心机制来解决冲突,在这一意义上大城市地区各种各样的政治管辖单位可以以连续的、可预见的互动行为模式前后一致地运作。也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作为一个体制运作的。”多中心作为一个一般概念包含着一种审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秩序的独特方法。[14](P831)
其次,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是多层次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区分了操作、集体选择与立宪选择三个相互影响的层次和领域。”执行就是这几个层次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15](P6)
最后,自主治理的框架。奥斯特罗姆在研究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的时候,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了“自筹集资的合约实施博弈”,论证了自主治理的可能性。自主治理是政府与市场之外的一种治理方式。政府和市场因为都无法很好的解决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的问题,所以不能有效地治理公共事务,需要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避免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取得共同的收益。[16](P34)
5.治理理论模型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途径在研究的出发点上都有单向度的特点。很难理解执行事务的复杂性。8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要求有新的组织方式和协调方式。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治理。“把治理当作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根源在于对社会科学流行的一些过于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的否定。”[17](P56)
90年代以来,以米尔沃德(H.Brinton Milward)、普罗旺(Keith G.Provan),斯铎克尔(Robert P.Stoker)、斯舵(Clarence Stone)、维博(Edward P.Weber)、巴贝奇(Eugene Bardach)、利恩(Laurence E.Jr.Lynn)、赫润奇(Carolyn J.Heinrich)、黑尔(Carolyn J.Hill)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将治理理论运用到执行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政策执行的治理理论和模型。
治理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核心内容:
首先,扬弃管理作为执行研究的分析工具,提出了治理的分析工具。研究治理的学者们认为治理是与管理相区别的概念。“治理…被认为是为私人、非赢利部门和公共部门机构达成一致的规则和集体行动创造条件。治理的本质是它对于治理机制的关注,如同意,合约和协定,治理机制并不单纯的依赖于权力和政府的批准。”[10](P279)
其次,将执行看作多变量的相互作用。“治理的主题和观点很难用精确度来衡量。尽管如此,这个话题仍关涉当今政策世界的一些相关维度。其一,政策行动的多变量特征。其二,治理考量任一情况下政策行为的结构、进程的设计及实施,是对强调制度的很好补充。其三,治理方法强调对多层次结构的统辖管理的理解,实行治理需要加入有关如何使行动一致的社会协作和主张。”[10](P276—277)
再次,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在治理研究中引入博弈论的框架是对早期的执行博弈模型的扩展和深化。博弈论的分析框架“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观点,说明了对多执行者行为进行分析的工具;超越了早期政策调查所总结出来的有关变量的研究成果。”[10](P277)
6.政策网络理论模型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途径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分析的出发点和分析单元的选择上,但是对于各个执行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缺乏分析和表述。
网络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概念,来源于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政策网络则是一种分析政策参与过程中团体与政府关系的方法,它是一群互赖行动者之间建立某种稳定程度的社会关系型态,以促成政策问题或方案的形成或发展。[18](P61)
就执行研究领域而言:90年代以来,在胡弗恩(Hans Hufen)、麦恩(Bernd Marin)、梅恩茨(Renate Mayntz)、约登(Grant Jordan)、舒伯特(K.Schubert)、马西(D.Marsh)、夏普夫(Fritz W.Scharpf)、图尔(LaurenceJ.O'ToolJr)、理查逊(Melissa Richardson)、克里因(Erik-Hans Klijn)、柯切尔特(Walter J.M.Kichert)、伯加逊(Peter Bogason)等为代表的学者们的持续努力下,政策网络已经成为超越官僚和市场机制的第三种治理机制;成为公共政策执行的要素,且有取代政策分析、新公共管理、新制度主义的趋势。
政策网络具有多元、分割、相互依赖、相互调整、建立共识、合作与互动的特性。政策执行的网络模型将政策执行过程理解为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互动,形成一定的政策结果,政策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行动者下一步行动的辩证过程。[18](P32—98)
其实第三代研究的理论模型有类似和交叉的地方;可以预见,政策执行的第三代研究将会在融合多种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取得一个在基本理念和操作规则上都不同与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理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