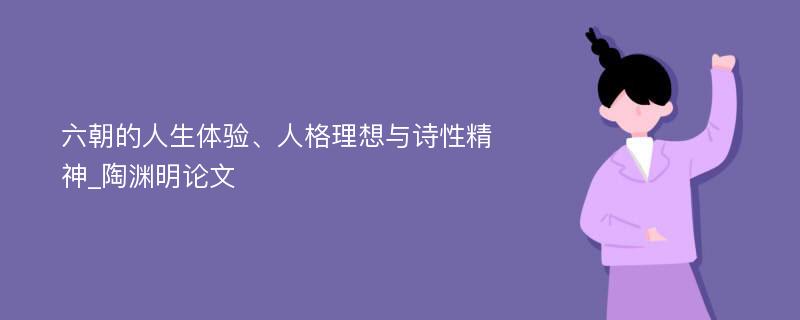
人生体验、人格理想与六朝诗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人格论文,理想论文,精神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1)01-0148-05
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诗学精神
“诗学”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关于诗歌创作实践方面的学问,并不完全是理论问题。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认为,中国诗歌对社会人生的渗透与影响较西方深刻得多,中国人在诗歌里获得了一般民族在宗教里才能获得的灵感,他甚至把诗歌称作中国人的宗教[1](P.240)。林语堂以文人的眼光,敏锐地感受到了中国诗歌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
“精神”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带有一些原始思维的特点。“精”和“神”的含义都与“气”有关。如《管子·内业》载:“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礼记·祭义》载:“气也者,神之盛也。”《乐记》载:“气盛而化神。”这种观念一直被后人所沿用。如清人王夫之说:“盖气之未分而能变合者即神,自其合一不测而谓之神尔,非气外有神也。”(《张子正蒙注·神化篇》)刘勰在《文心雕龙·养气》中也说:“气衰者虑密以伤神。”可见,“精”和“神”就是精气(或清气),实际上都是元气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成为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而人的精神意识乃是这种清气的禀赋与转化,其含义比较宽泛,包括人与自然在内,并不专指人的思维与意识[2](P.11)。
精神现象往往具有某种神秘莫测的性质,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上》)、“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荀子·天论》)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所有民族早期共有的观念。但是,就华夏民族而言,天地自然在古人的心中并不只是神秘和敬畏的对象,也是亲和的对象。在古人看来,寒来暑往,春种秋收,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宇宙万物在运动变化之中自身又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这一点在《周易·系辞下》中有明确的记载:“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神灵观念,形成了一种“有情的宇宙观”,它包含着宗教、审美和道德等诸多因素。对于这类问题,人们无法靠理智和思辨来认识,只能通过体验和感悟来获得,在人伦日用中通过“下学而上达”来达到对现实的超越和精神意蕴的把握。正因为如此,包括诗歌在内的审美活动就成为精神体验的重要手段。
二、人生体验与六朝诗学精神
六朝诗学精神与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汤用彤认为,六朝时期对于“文”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言‘文以载道’,一言‘文以寄兴’,而此两种观点均认为‘文’为生活所必需。前者为实用的……后者为美学的,此盖以‘文’为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鉴赏和享受自然……故文章当表现人与自然合为一体。《文赋》谓‘诗缘情而绮靡’,又谓‘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故文章必须有深刻之感情。而‘寄兴’本为喻情,故是情趣的,它是从文艺活动本身引出之自满自足,而非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3](P.206)。汤用彤所说的“文以寄兴”正是六朝诗学精神的源泉。
六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随着文学地位的提高,文学创作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生体验与文学创作的有机结合成为那个时代文人的自觉行为,并逐渐摆脱了传统政教观念的束缚。这里所说的“体验”不同于一般的生活经验,而是在生活经验中见出生命的意义、深刻的思想和动人的诗意,它包含着一种价值性的评判和领悟。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格尔·伽达默尔对“体验”一词作过这样的阐释:“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东西就属于体验。以这种方式成为体验的东西,在艺术表现里就完全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状态。”[4](P.79)这就意味着人生体验经过诗人的审美创造可以转化成诗学精神。
首先,人生体验与诗学精神的关系表现在对个体情感的重视上。钟嵘在《诗品序》中列举了社会生活中种种悲剧性的人生遭遇(如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负戈外戍等),指出“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汉魏以来的文学自觉正是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如曹植在《赠徐幹》诗中说:“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说明曹植对以诗抒情的自觉意识。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建安诗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在《时序》篇中说,这一时代的文学风尚是“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这种风气的形成与汉末以来“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因而,体现儒家忧时伤乱、渴望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就成为这一时期诗学精神的重要内容,后人常把“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相提并论,也是着眼于这一点。
对情感问题的重视也反映在这一时期关于圣人有情与无情的讨论上。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云:“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何劭《王弼传》又载王弼《答荀融书》云:“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总的看来,王弼一方面肯定了人的各种现实情感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圣人具有超越性的一面,能够做到“以情从理”,而这一切都是出于自然。也就是说,王弼既肯定了人的自然情感,又强调超越现实,体现了魏晋玄学本末体用的基本观念。王弼对自然情感的肯定,丰富了“自然”一词的含义,使人们对情感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也为玄言诗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表面上看,玄言诗“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背离了抒情言志的诗学传统,“诗骚之体尽矣”(《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玄言诗人似乎都是一些体道之士。但从现存的玄言诗来看,多数作品并非只是空谈玄理,而与现实人生毫无关系。如庾蕴《兰亭诗》云:“仰想虚舟说,俯叹世上宾。朝荣虽云乐,夕弊理自因。”虽然借用了《庄子·山木》中的典故,但庾蕴却从中引发了朝荣夕弊、盛衰无常的感叹。同样,王羲之在《兰亭诗》中也有类似的感慨:“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这使人联想到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发出的“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感叹。可见,阐发玄理的目的还是为了消释生命的感伤和焦虑,在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和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诗歌言志抒情的传统到玄言诗人并没有中断,不同在于情志的内涵与表现,玄言诗人是从理念的层面而不是从形象的层面抒情言志,或者说他们所抒发的是理念化之情”,由于“魏晋玄学整体上既重情,又要求超越形而下之情”,所以“情的内涵已由实入虚,变为‘高情’、‘至情’”[5]。
其次,人生体验与诗学精神的关系也表现在对生命问题的思考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生命体验,正因为人生有限,所以人们才渴望不朽,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但是,在动荡黑暗的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的理想常常难以如愿,特别是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易代之际更是如此。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在阮籍的《咏怀诗》中常常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否定,如“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其五十三)、“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其三)、“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知”(其十五)等。在阮籍看来,人生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也不值得留恋。与建安文学相比,阮籍的诗从对外在功业的追求转向了对生命意义的理性思考,这也是《咏怀诗》的一个基本主题。
对生命意义和生死问题的思考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体现得更加全面和充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形影神》组诗。在《形影神》组诗中,陶渊明通过形影神之间的对话,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在“神辨自然”的基础上,最后归结为一种委运任化的思想,“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也就是陈寅恪概括的“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新自然说”[6](P.205)。不过,对于及时行乐和立善求名的态度,陶渊明也没有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在肯定其合理性一面的同时,又指出其中的不足(前者过于消极,后者又很虚幻)。
陶渊明在思想上有很多矛盾,例如在生死问题上他也时常感到焦虑。陶渊明说:“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在《自祭文》中又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既然人生在世如此艰难,死后又不可知,为什么不能及时行乐呢?所以陶渊明在《游斜川》一诗中说:“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在对待立善求名的问题上,陶渊明的态度也有些矛盾,他称赞颜回的人格精神,“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但对颜回的清贫,又感到遗憾,“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饮酒》其十一)。陶渊明有时感叹人生的虚幻,“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但并没有彻底否定人生,认为还是应该有所作为,至少要做到自食其力,“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总的说来,陶渊明对生命问题看得比较清醒透彻,既不完全否定,也不过分执著,让一切都顺应自然。这是陶渊明人生体验的觉悟和超越,也是六朝诗学精神成熟的标志。
此外,人生体验与诗学精神的关系还表现在对自然美的发现上。自然美是指大自然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形态和神韵之美,同时也包含着人的感受与评价。也就是说,自然美的发现,不仅与对象本身有关,而且也与主体自身的态度有关。黑格尔虽然轻视自然美,认为它远远低于艺术美,但他关于自然美的论述仍然值得重视。黑格尔说:“自然美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7](P.160)一方面,自然界的万象纷呈本身“显出一种愉快的动人的外在和谐,引人入胜”;另一方面,“自然美还由于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而得到一种特性。例如寂静的月夜、平静的山谷,其中有小溪蜿蜒地流着,一望无边波涛汹涌的海洋的雄伟气象,以及星空的肃穆而庄严的气象就是属于这一类。这里的意蕴并不属于对象本身,而是在于所唤醒的心情”[6](P.170)。可见,山水景物只有与人的心灵产生沟通,才能称得上发现。所以清人叶燮说:“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集唐诗序》)归根结底,自然美的发现,与人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由于魏晋以来人的精神得到了自由和解放,“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的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7](P.216)。
自然美的发现与魏晋玄学和佛教的影响有关。玄学和佛教都重视自然。如王弼说:“万物以自然为性。”(《老子》二十九章注)这里的“自然”就是“道”,是一个哲学概念。但“道”又是无所不在的,自然山水正是“道”的最好体现,人们可以从中体悟自然的真谛,不仅如此,山水也最适合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精神在那里能够获得充分的自由,所以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畅神”说,强调主体应以一种空明虚静的心态观照自然(“贤者澄怀味象”),以此来体悟佛理,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在宗炳看来,山水不仅“质有而趣灵”,而且还能够“以形媚道”,实际上是把自然山水看做有机的生命体(这里的“媚”字有“亲近”的意思)。与传统的物感说相比,“畅神”说突出了物我两忘、自由和谐的精神交流,这就使宗炳的“畅神”说更具有审美意义。于是,自然被人格化了,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像知己一样,在情感上进行交流沟通。正如刘勰所云:“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
魏晋士人对自然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诗歌中,并成为六朝诗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如王羲之的《兰亭诗》:“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尽管诗中还有比较明显的体悟玄理的内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但它“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7](P.217)。而陶渊明的田园诗,诸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等等,不仅流露出对大自然的欣喜和向往,而且表现了他悠然自得的情趣和旷达超脱的胸襟。萧统在谈到读陶渊明诗文的体会时说:“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陶渊明集序》)
到了晋宋之际,“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不仅使诗歌在“模山范水”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而且也使魏晋士人以体悟玄理为目的的山水品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情感交流。谢灵运在《游名山志》中把他对山水的热爱看做是“性分之所适”。这种爱好甚至超越了对名利的追求,使他能够忘我地投入自然的怀抱,把新鲜活泼的心灵体验与生机勃勃的自然美景融为一体。因此,谢灵运笔下的景物往往是人格化的,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林壑敛冥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等等。所以,徐复观说:“由魏晋所开辟的自然文学,乃是人的感情的对象化。于是,诗由‘感’的艺术,而同时成为‘见’的艺术。诗中感情向自然的深入,即是人生向自然的深入。由此而可以把抑郁在生命内部的感情,扩展向纯洁地自然中去。”[8](P.418)
三、人格理想与六朝诗学精神
从本质上说,诗学精神与创作主体的人格理想、审美追求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诗学精神的最高境界与艺术精神又是相通的。徐复观指出:“艺术是人生重要修养手段之一,而艺术最高境界的达到,却又有待于人格自身的不断完成。”[8](PP.25~26)显然,徐复观对艺术精神的理解是强调主体的人格修养。我们读屈原的作品,感受最深刻的是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为坚持理想,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人格精神,这也是屈原诗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两汉时期,儒学独尊,通经入仕是士人惟一的选择,利禄所在,趋之若鹜。“经明行修”的目的是为大一统政权服务,皇权的专制和大一统的思想极大地压抑了士人的个性,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土人与帝王的关系正如东方朔所云,“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答客难》)在这种情况下,士人难以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东汉末年,随着儒学的衰落和道家思想的兴起,士人的独立人格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旧的规范和秩序已经崩溃,“于是要求彻底摆脱外在的标准、规范和束缚,以获取把握所谓真正的自我,便成了魏晋以来的一种自觉意识”[9](P.193)。所以,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7](P.208)
魏晋时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人生观,主要有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还有以《列子·杨朱》为代表的纵欲论等。在那个道德崩溃、风气颓靡的社会中,这种人生观虽然有反抗传统的一面,但却缺少救世精神,只能追求个体精神的满足与心灵的和谐,如嵇康的《养生论》强调“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体气和平”。庄子的思想虽然在这一时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绝对的超脱和逍遥是做不到的。事实上,阮籍的逍遥论(如《大人先生传》、《达庄论》),主要是对庄子思想的发挥,是指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很难成为一种现实的人生态度。而且旧的秩序虽然崩塌,但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不可能从人们的思想中彻底根除,如阮籍任性不羁,行为放诞,“礼法之士疾之若仇”,却“外坦荡而内淳至”(《晋书·阮籍传》)。近人黄节说:“嗣宗实一纯粹之儒家也。内怀悲天悯人之心,而遭时不可为之世,于是乃混迹老庄,以玄虚恬淡,深自韬晦,盖所谓有托而逃焉者也,非嗣宗之初心也。”(萧涤非《读诗三札记》引黄节语)又如嵇康,虽然公开“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至于后来被司马昭以不孝的罪名杀害,但实际上,嵇康并非真正反对名教。正如鲁迅所说:“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人格上的分裂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如“质性自然”的陶渊明,虽然在经过仕与隐的反复后终于归隐田园,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彻底化解仕隐出处的矛盾。陶渊明在诗中曾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看起来,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营谋衣食以求自安,通过躬耕的劳动生活来肯定生命的意义。但是,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明确反对他的弟子樊迟学稼学圃。孔子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是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认为君子应该“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陶渊明当然清楚这一点。陶渊明有诗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可见,陶渊明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出于无奈。
魏晋士人的思想矛盾是汉末以来名教危机的重要体现,也是魏晋玄学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玄学的产生是为人格的重塑与统一探求理论上的依据,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人生观念和人格理想。汤用彤指出:“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3](P.196)所以,李泽厚把构建理想的人格本体看做是魏晋玄学的中心问题。李泽厚说:“人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9](P.193)张海明说:“玄学产生的过程,正是人格问题的讨论由显而微、由具体而抽象的过程。事实上,人格问题的讨论不仅直接导向了魏晋玄学,而且还孕育了魏晋玄学的现实主题,诸如理想的圣人人格为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等,都和人格问题的讨论有着直接的渊源。”[10](P.21)
总之,玄学确立了一种重神贵无;崇尚自然的观念,并通过士人的人格精神影响到六朝的文学和艺术,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理想,“这就是将美从狭隘的道德境界上升到宇宙本体上,注重表现和描绘精神之美”[11](P.20)。玄学与艺术通过理想人格这一中介使两者得到沟通,前者是哲学的诗化,后者是诗化的哲学。玄言诗在艺术上虽然并不成功,在晋宋之际为山水诗所取代,但它所张扬的那种超越世俗的、审美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境界对山水诗的影响是深远的,形成了一种“寄至味于淡泊”、“似淡而实美”的风格。“从晋宋到唐代,典型的山水诗都能显示出诗人超脱、从容、宁静、闲雅的风度。这种品味高雅的士大夫气,便是中国山水诗的神韵所在。”[12]从玄言诗到山水诗,标志着六朝诗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在新的审美理想的影响下不断提升,成为诗学精神的重要体现。
[收稿日期]2010-0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