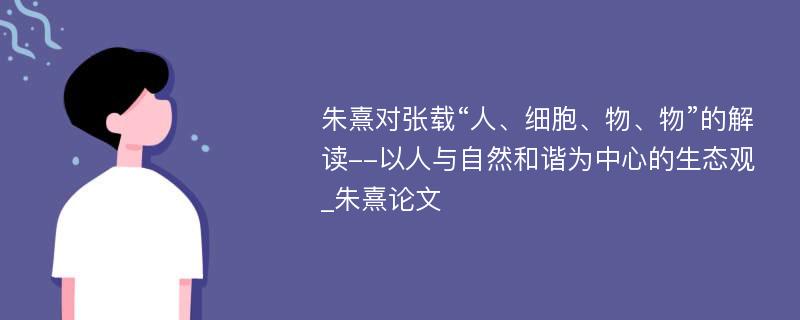
朱熹对张载“民胞物与”的诠释———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胞物与论文,朱熹论文,以人论文,自然和谐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2)03-0115-05
“民胞物与”,即宋代张载提出的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般被理解为“民为同胞,物为同辈。犹言泛爱一切人与物”(《辞源》),而且,当今不少学者认同这样的理解,并以为其中所包含的保护自然的思想具有生态意义。但是,这样的理解,很容易与墨家的“兼爱”混为一谈。的确,儒家很早就具有保护自然的思想,张载的“民胞物与”也具有保护自然的思想内涵。然而,二程将它与“理一分殊”相联系,而与墨子“兼爱”相对立。朱熹吸取二程的“理一分殊”概念,对“民胞物与”作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张载的“民胞物与”,既讲人与物皆为同辈,又讲物与人各有差异,所以,对于自然物,不仅应当予以保护,更应该按照其不同的特性,使其各得其所。为此,朱熹在如何保护自然方面提出了不少见解。他强调尊重自然万物的特殊性,以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谐与共同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一、早期儒家的生态观与张载的“民胞物与”
儒家自孔子开始就有保护自然物的思想。据《论语·述而》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又据《礼记·祭义》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孔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另据《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载,齐人高柴“开蛰不杀,方长不折”,孔子曰:“开蛰不杀则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则仁也。”然而,在孔子那里,人与物受到重视的程度是不同的。据《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应当说,孔子并不是不重视马,而是认为,人比马更为重要。
战国时期,孟子也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据《孟子·尽心上》载,孟子明确提出“仁民而爱物”。后来张载讲“民胞物与”,与这一思想多少有些相似。但需要指出的是,孟子讲“仁民而爱物”旨在强调“爱有差等”。《孟子·尽心上》载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认为“爱物”之“爱”,不同于“仁民”之“仁”,更不同于“亲亲”之“亲”。对此,东汉赵岐注曰:“先亲其亲戚,然后仁民,仁民然后爱物,用恩之次者也。”宋孙奭疏曰:“孟子言,君子于凡物也,但当爱育之,而弗当以仁加之也,若牺牲不得不杀也;于民也,当仁爱之,而弗当亲之也。以爱有差等也。是则先亲其亲,而后仁爱其民;先仁爱其民,然后爱育其物耳。是又见君子用恩有其伦序也。”①孟子讲“爱有差等”,旨在与墨家的“兼爱”区别开来,从而体现出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差异。
另据《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王道之始也。”这里要求按照不同时节开发和利用自然物,显然也包含着保护自然物的思想。孟子的这一思想实际上为后来的荀子以及《礼记·月令》所继承。
《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圣王之用也。”《荀子》对《孟子》要求按照不同时节开发利用自然物中的“时”作了规定:或是“草木荣华滋硕之时”、“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即动、植物的生长时期,或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季节农时。事实上,动、植物的生长时期与季节农时是一致的。
《礼记·月令》按照一年中季节的变化顺序,对各个季节、月份的天象、物候作了描述,并且还据此对各种农事活动作了安排。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更多地强调按照季节农时开发利用自然物。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将农业生产与保护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思想,是从人的需要出发,以实现人对于自然物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
与孟子不同,庄子主张“道法自然”,要求还原自然状态。《庄子·应帝王》载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至乐》也载故事: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对此,庄子说:“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鲦,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
关于保护自然,可以有多种方式。从人的需要出发开发利用自然,并且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而采取某些保护自然的措施,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是根据人对“保护”的理解,把这种“保护”外在地强加于自然,这都是以人类为中心。不可否认,孟子、荀子以及《礼记·月令》要求按照不同时节开发和利用自然物,虽然与盲目的开发利用不同,包含了保护自然的内涵,但由于其目的在于实现“不可胜食”、“不可胜用”,因而较为接近以人类为中心。庄子要求还原自然状态,则与孟子的以人类为中心完全相反;但是,并没有解决人类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物的问题。
宋代张载讲“气”,以为天地万物统一于“太虚之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胞物与”。张载《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②应当说,“民胞物与”提出人与物皆为同辈,包含了保护自然的思想,实际上为孟子的“仁民而爱物”找到了理论依据。至于怎样保护自然,是像孟子那样,从人的需要出发,还是像庄子那样还原自然状态,张载的“民胞物与”并没有给予回答。
应当说,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不乏有保护自然的思想。“民胞物与”,就其强调要保护自然而言,与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一样,是有其生态意义的,但是,由于没有回答怎样保护自然,其生态意义又是十分有限的。正如当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是由于人们不知道应当保护自然,而是由于人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实现对于自然的保护。
二、“民胞物与”与“理一分殊”
张载的“民胞物与”,受到二程以及后来朱熹的高度重视和赞赏,并得到了深入的诠释。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并不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保护自然的思想而给予赞赏,而是在他们看来,张载的“民胞物与”蕴含着对于宋代理学发展极为有价值的“理一分殊”。
宋绍圣三年(1096年),程颐门人杨时寄书程颐曰:“《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③程颐回答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④程颐认为,张载《西铭》讲“理一分殊”,从老吾老、幼吾幼出发而推及他人,而墨子“兼爱”则把爱他人与爱亲人等同起来,讲爱无差等,二者是相对立的;只讲亲疏有别,只讲老吾老、幼吾幼,就会自私自利而不仁,而讲爱无差等,就会亲疏不分而无义;所以,要从老吾老、幼吾幼出发推及他人,才能止住自私自利而达到仁。因此,在程颐看来,张载的“民胞物与”并不是讲“兼爱”,讲“泛爱一切人与物”,而是讲从老吾老、幼吾幼出发而推及他人和物,这就是“理一分殊”。
问题是,从字面上看,张载的“民胞物与”讲的是人与人皆为同胞,人与物皆为同辈,并没有讲从老吾老、幼吾幼出发,更没有明确讲“理一分殊”。杨时也说:“《西铭》之书,以民为同胞,长其长、幼其幼,以鳏寡孤独为兄弟之无告者,所谓明理一也。然其弊无亲亲之杀,非明者默识于言意之表,乌知所谓理一而分殊哉?”⑤后来,杨时论《西铭》时又说“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⑥显然,杨时接受了程颐所谓“《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并认为,张载的“民胞物与”既是讲人与人皆为同胞,人与物皆为同辈,即“理一”,也内涵着像孟子“仁民而爱物”那样的“爱有差等”,即“分殊”。
对于程颐讲“《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朱熹非常赞同,并指出:“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牿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⑦显然,在朱熹看来,张载《西铭》讲“民胞物与”,就是讲“理一分殊”。他还说:“《西铭》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为父,坤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兹藐焉,混然中处’,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⑧
重要的是,朱熹是用“理一分殊”解释张载的“民胞物与”,指出:“乾之为父,坤之为母,所谓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则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为同胞、物为吾与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谓理一者也。然谓之民,则非真以为吾之同胞;谓之物,则非真以为我之同类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谓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与、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圣、曰贤、曰颠连而无告,则于其中间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谓理一者,贯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⑨所以,在朱熹看来,张载的“民胞物与”,既讲人与人皆为同胞,物与人皆为同辈,又讲民与同胞、物与人的不同,讲爱他人与爱亲人、爱物与爱人的不同,这就是“理一分殊”。
如前所述,孟子讲“仁民而爱物”旨在强调“爱有差等”。朱熹则在根据“理一分殊”解释张载的“民胞物与”时,又将“民胞物与”与“仁民而爱物”结合起来。他说:“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通是一气,初无间隔。‘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物虽皆天地所生,而人独得天地之正气,故人为最灵,故民同胞,物则亦我之侪辈。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等差自然如此。”⑩在朱熹看来,张载的“民胞物与”讲人与人皆为同胞,人与物皆为同辈,是“理一”,但又包含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中的“爱有差等”,包含了“分殊”。他还说:“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则为墨氏兼爱;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则为杨氏为我。所以言分殊,而见理一底自在那里;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夹杂。”(11)认为“理一”与“分殊”,二者不可分割。
三、朱熹的诠释及其生态意义
正是根据“理一分殊”,朱熹对张载的“民胞物与”作了深入的诠释,指出:“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其所资以为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为性者,皆天地之帅也。然体有偏正之殊,故其于性也,不无明暗之异。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故曰‘同胞’。则其视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则得夫形气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与我不同类,而不若人之贵。然原其体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尝不同也,故曰‘吾与’。则其视之也,亦如己之侪辈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惟吾与也,故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于外也。”(12)这段论述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人与人皆为同胞,人与物皆为同辈。朱熹认为,人与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天地之气而为其体,天地之理而为之性;就人与物的体和性都来自天地并且都以天地为本而言,人与物皆为同辈。就人而言,人“得其形气之正”,“通乎性命之全”,而属于同类,因而皆为同胞。所以,既要爱人,也要爱物。这就是通常把“民胞物与”解释的“民为同胞,物为同辈。犹言泛爱一切人与物”。需要指出的是,仅作这样的解释,是很不够的。
第二,物与人是有差别的。朱熹认为,物与人,虽然皆为同辈,但在体上有偏正之殊;在性上有明暗之异。就物而言,物“得夫形气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因而与人不属于同类,并且不若人之贵。所以,爱物不同于爱人。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还认为,物与物之间也是各不相同的,据《朱子语类》载,问:“《西铭》‘理一而分殊’,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须是就民物中又知得分殊。”(13)所以,对于不同的物,也要给予不同的对待。正如朱熹门人郑子上所说:“有知无知亦不无小异,盖物虽与人异气,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气所生,与无知之物异,恐圣人于此须亦有差等。如齐王爱牛之事,施于草木恐又不同。”(14)
第三,就保护自然物而言,应当“若其性、遂其宜”,也就是要根据自然物的特殊性,合理地予以对待。所以,人对天地万物的作用,是采取辅助的方式,而不是外在的强加。
从朱熹根据“理一分殊”对张载“民胞物与”的诠释可以看出,他不仅根据“民胞物与”所体现的“理一”,强调人与物皆为同辈,提出要保护自然,而且,根据“民胞物与”所蕴含的“分殊”,强调物与人的差别、爱物与爱人的不同。朱熹还在注《孟子》“仁民而爱物”中引程颐所言:“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民则可,于物则不可。”(15)认为“推己及人”意义上的“仁”,只能用于人,不可用于物。可见,朱熹不仅讲保护自然,而且更为关注如何保护。
朱熹赞赏并引述张栻所说:“圣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是心之发也。然于物也,有祭祀之须,有奉养宾客之用,则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于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若夫子之不绝流、不射宿,皆仁之至义之尽,而天理之公也。……夫穷口腹以暴天物者,则固人欲之私也。而异端之教,遂至禁杀茹蔬,殒身饲兽,而于其天性之亲,人伦之爱,反恝然其无情也,则亦岂得为天理之公哉!”(16)认为保护自然应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要像孔子那样“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既要反对“穷口腹以暴天物”,也要反对“禁杀茹蔬、殒身饲兽”。
朱熹自己也说:“圣贤出来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如昆虫草木,未尝不顺其性,如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当春生时‘不妖夭,不覆巢,不杀胎;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所以能使万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17)这里所谓“抚临万物”,就是对自然的爱护。在朱熹看来,保护自然应当“因其性而导之”,就是要根据自然物的不同物性,顺其性而为,合理地加以开发和利用,“取之以时,用之有节”,从而“使万物各得其所”。而且,朱熹还认为,要能够“因其性而导之”,“使万物各得其所”,首先要“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也就要认识自然之理。这就需要“格物”,“即物而穷其理”,通过研究自然界事物,把握自然之理。他还说:“古人爱物,而伐木亦有时,无一些子不到处,无一物不被其泽。盖缘是格物得尽,所以如此。”(18)这里把“爱物”与“格物”联系起来,以为“爱物”应当从“格物”入手。
由此可见,朱熹对张载“民胞物与”的诠释,不仅从字面上理解为人与物皆为同辈,既要爱人,也要爱物,而且更是从内涵上揭示物与人、爱物与爱人是有差别的,而强调要根据物性,合理地保护自然。由于强调物与人的差别、爱物与爱人的不同,朱熹在如何保护自然方面提出了不少见解。他主张像孔子那样“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对自然“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主张合理的而不是过度的开发和利用自然:他要求对自然“因其性而导之”,“使万物各得其所”,并进而提出要“格物”,认识自然之理。应当说,这些都是围绕着自然物而展开的,体现了对于自然万物特殊性的尊重。同时,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谐与共同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在当今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观备受质疑的背景下,无疑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收稿日期]2011-12-06
注释:
①(汉)赵岐、(宋)孙奭:《孟子注疏》卷十三下《尽心章句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71页。
②(宋)张载:《正蒙·乾称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
③(宋)杨时:《龟山集》卷十六《寄伊川先生》,文渊阁四库全书。
④(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二程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09页。
⑤(宋)杨时:《龟山集》卷十六《答伊川先生》,文渊阁四库全书。
⑥(宋)杨时:《龟山集》卷十一《语录二》,文渊阁四库全书。
⑦(宋)朱熹:《西铭解》,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⑧(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七)卷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23页。
⑨(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与郭冲晦》(二),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38-1639页。
⑩(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七)卷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20页。
(1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七)卷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21页。
(12)(宋)朱熹:《西铭解》,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1-142页。
(13)(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七)卷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24页。
(1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郑子上》(十四),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89-2690页。
(1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16)(宋)朱熹:《四书或问·论语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51页。
(1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一)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6页。
(18)(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一)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4页。
标签:朱熹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张载论文; 孟子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国学论文; 朱子全书论文; 西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