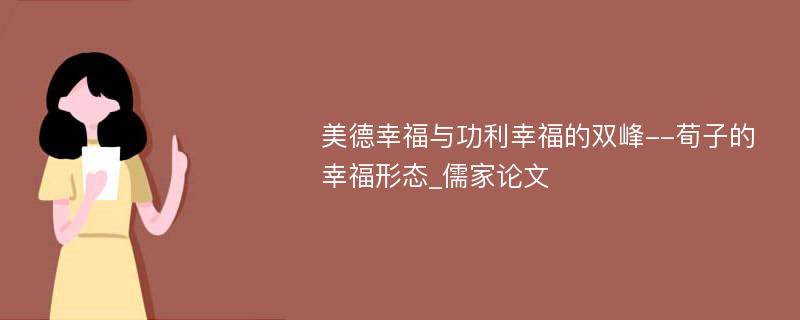
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双峰并峙——荀子的幸福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幸福论文,荀子论文,双峰论文,德性论文,功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6;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2)04-0022-05
荀子的思想,一方面承续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另一方面批判继承、融会贯通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因而显得相当驳杂。荀子思想的这两方面特性深刻反映在其幸福观中。在孔孟那里,儒家的幸福主要地表现为“乐”。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1](《述而》),称赞颜回能够“箪食”“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1](《雍也》),是为“孔颜之乐”;孟子讲“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2](《尽心上》),是为“君子之乐”。而在荀子那里,福、乐、富、荣等众多关于幸福的概念被频繁地使用,“乐”不再是幸福概念集中和纯粹的表达。孔孟的幸福观主要是精神的、德性的、境界的,而荀子的幸福观中,物质的、功利的、欲望的东西获得了理性的确认,这些内容与儒家的德性原则混合在一起,丰富了儒家的幸福观,使先秦儒家幸福观的全貌得到了一次驳杂的呈现。
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满足,是人生幸福首先要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不仅是因为需要的满足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更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及其解决直接决定着人生追求的内容、人生价值的取向和人生幸福的性质。就思想流派而言,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就可能形成不同的派别,比如纵欲派、禁欲派、寡欲派、节欲派或者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德性主义、至善主义等等。先秦诸子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从荀子对诸子的批判来看,人欲问题也应是百家争鸣的重要问题之一:“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3](《非十二子》)
按照一般的说法,荀子认为对待情欲的态度有三种错误的流派:一是纵欲派,以它嚣、魏牟为代表;一是禁欲派,以陈仲、史鰌为代表;一是寡欲派,以墨翟、宋钘为代表[4](P100)。荀子批评纵欲派放纵性情,习惯于任意作为,不符合礼义规范的要求,其行为无异于禽兽。在儒家幸福的视域中,对纵欲派的驳斥实际上意味着纠纯粹功利幸福之偏、解完全利欲幸福之蔽,进而也就隐含着以德性幸福来纠偏和解蔽的意图。荀子批评禁欲派抑制人的性情,行为离奇偏邪,一心把与众不同当作高明,求分异而不能合于大众,重小节而不能分清大义。这就是说,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休等本是人之常情,然而禁欲派却要抑制人的正常需求,否定合理的功利幸福,追求所谓的离世独立。荀子进一步指出,这种离世独立、立异以为高也并不是儒家所崇尚的德性幸福,因为德性幸福必然是“合大众”、“明大分”而不是表面上的“分异人”。
寡欲派以墨翟及其后学宋钘为代表,是荀子重点批判的对象。荀子批评寡欲派崇尚功利、重视节俭却轻视等级差别,完全不懂得人群之差等、君臣之礼义。在荀子看来,墨翟、宋钘为代表的寡欲派也是违背人情的,他们崇尚功利的同时又把人的利欲定位在极低的水平上,实际上也是否定了人的功利幸福。荀子针对宋钘的“人之情,欲寡”提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昧,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之“五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古之人为之不然。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以富厚而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则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赏而以人之所欲者罚邪?乱莫大焉。”[3](《正论》)
荀子由人情之“五綦”驳斥了“寡欲说”,对功利幸福的确认也呼之欲出,这是批判寡欲派所导出的一个方面。进一步而言,荀子对墨家“寡欲说”驳斥同时展示着对儒家德性幸福的诉求,这个方面则是由批判寡欲派轻视等级差别、礼乐文化而导出的。孔子奠定了儒学两个核心概念——仁、礼,孟子由仁而礼侧重内在心性的发掘,荀子则由礼而仁侧重于外在的规范和导引,但在这种差异的背后,“人皆可以为尧舜”(孟)、“涂之人可以为禹”(荀)精神相通,“修身为本”的理念一脉相承。换言之,儒家孟荀之个体德性与礼义文化精神相通、目标一致,而寡欲派轻视等级差别、礼义文化,也就意味着对儒家德性幸福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荀子针对墨子的“非乐”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荀子首先指出喜乐是人的自然感情,进而提出必须对自然情感之乐加以引导使之不发生紊乱,从而能够实现儒家崇尚的道德之乐、心性之乐。从道德个体而言,儒家圣王作乐的目的就在于“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由于“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要达到“以道制欲”,实现“乐而不乱”,就应当发挥音乐的作用:“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这样,在荀子对墨子“非乐”的驳斥中,儒家德性幸福的诉求也就呼之欲出了。
由此可以发现,在对纵欲派、禁欲派、寡欲派的批判中,荀子已经明显地展现出将儒家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统一起来的致思趋向。
“孔颜之乐”奠定了儒家德性幸福的基本形态,此种幸福强调德性的完满、人格的成就、境界的升华,在儒家幸福观中确立了德性至上的原则。孟子把儒家君子作为德性幸福的主体,以伦理型的家庭幸福、道德型的事业幸福以及侧重于内在向度的心性之乐扩展了儒家德性幸福的内容。德性幸福由“孔颜之乐”演变为“君子三乐”,依然贯彻和保持了德性至上的原则。荀子上承孔孟,旁通诸子,其幸福观难免呈现出驳杂的特性。但就德性幸福在其幸福观中的地位而言,荀子与孟子并无二致,同样是承接了德性至上的孔门传统。进一步而言,尽管荀子严厉批评思孟学派,但在德性幸福的原则性问题上,孔、孟、荀实在是一以贯之的。荀子有关德性幸福的论述其实并无多少新鲜之感,其中充斥着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孔孟的“老生常谈”。可以列举三组相关的论述来说明:
第一组,关于德性幸福的自足性,即是说君子、圣人的人生幸福无须外求,即便远离世俗所谓的功名利禄、权势富贵,即便穷苦困顿、“箪食瓢饮”,也能够完满德性、成就理想人格,达到真正的幸福。“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3](《儒效》)“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紃之履而可以养体,屋室、芦庾、葭稾蓐、尚机筵而可以养形。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3](《正名》)这些语句与孔孟的表述,其“神似”和“形似”一目了然:“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啐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2](《尽心上》)。所谓“穷处而荣,独居而乐”不过是“孔颜之乐”的另一种表达,所谓“心平愉”不过是“仁义礼智根于心”的昨日重现。就各自论述的德性幸福之“醇”而言,就论述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荀子关于德性幸福自足性的表述并未将孔孟的思想向前推进,而只是一种延续,且在其中添加了些许功利的杂质。
第二组,关于德性幸福的主观体验,即是说实现德性幸福的主体获得了怎样的心理感觉和心理体验。“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为睹,则以至足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粱而至者,则瞲然视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无赚于鼻,尝之而甘于口,食之而安于体,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3](《荣辱》)。再看孟子相关的表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声也,有同听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2](《公孙丑上》)“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2](《尽心上》)这里可以看到,荀子与孟子在“口味”上真是有着相同的嗜好——“刍豢”,以致于二人在表述仁义道德引起的心理体验时都使用了“刍豢”一词。此外,“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粱而至者……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与“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的句式结构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组,关于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区分,即二者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孰先孰后的问题。“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荣。流淫、汗侵、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藉靡、舌绝,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辱。是荣辱之两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3](《正论》)再看孔孟:“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卫灵公》)“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2](《告子上》)如果说“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提法与“求义荣不求势荣”还稍稍有点出入,那么“义荣”、“势荣”、“义辱”、“势辱”的提法就几乎与“天爵”、“人爵”如出一辙了。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德性幸福的论述,荀子与孔孟不仅是“神似”,而且是“形似”,连语气和口吻都是十分接近的。“荀子对理欲关系的理解,内在地渗入了崇尚‘孔颜之乐’的儒学精神……理性精神的升华显然被置于更为主导的地位。”[5](P107-108)究其原因,乃是先秦时期儒家德性幸福已经由孔孟推至巅峰。荀子虽然集先秦各家之大成,但在德性幸福的建树上却是难有作为,能做和所做的也就是延续德性至上的孔孟传统。
如果说在德性幸福的道路上,荀子的幸福观主要是对孔孟的承续,那么在功利幸福的道路上,荀子更加着眼于社会大众而非少数道德精英,着眼于社会统治秩序而非道德个体修养,着眼于人之“类”而非人之“德”,较为充分地论证了功利幸福的合法性、合理性,使儒家幸福观中相对薄弱的功利幸福得以显著提升和发展。
“孔颜之乐”把“箪食”“瓢饮”“在陋巷”作为幸福观照的内容,实质上就是要求尽可能地降低个体的种种欲望,强调理性和德性对欲望的超越,从而获得所谓的精神之“乐”。孟子也明确宣称:“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2](《尽心下》)且不论孟子是否真正实践了这些,这种宣称终究意味着儒家幸福的价值导向,即意味着对功利幸福的排斥和轻视,而更重德性幸福的追求。荀子不是“醇儒”,在幸福观上言之,其“儒”在于对德性幸福的承续,其“不醇”就在于对功利幸福的提升和发展。也可以说,由于对功利幸福的提升和发展,荀子促成了先秦儒家幸福观在演进中的折变。
首先,荀子思想为功利幸福提供了人性论基础。人性学说在儒家思想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预设、前提或者基础,其意义或许并不在于探究人性事实上是善或者是恶,而是在于其所提供的理论基础。譬如,性善可以为德性幸福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点:由于人心天然具有“四端”,那么当人们接触外界的仁、义、礼、智之事事物物时,人心就会感到愉悦,这就是“理义悦心”[2](《公孙丑上》);当人们反身寻求善心时,人们就获得最大的乐,即“反身而诚,乐莫大焉”[2](《尽心上》)。与孟子性善论之“四端”正相对应,荀子提出了性恶论之“五綦”:“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3](《王霸》)荀子认为,耳目口腹内心之欲是人之常情,不可避免。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共同的天性;无论是禹是桀,“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3](《荣辱》)是相同的人情。在这样的人性预设之上,人之欲获得了人之情、人之性的论证,“合欲”同时具有了“合情”、“合性”的意义,功利幸福由此而获得了“合法”甚至是“合理”的理论基础。
其次,荀子思想为功利幸福提供了政治学论证。就幸福观可能引起的政治意义而言,德性幸福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德性的完满和人格的成就,这在客观上是与寄希望于君王、庶民个体德性的“仁政”内在一致的;而荀子的功利幸福提出人欲是“合情合性”的,在此基础上,荀子进一步论证了功利幸福的符合“天子之礼制”[3](《王霸》),这就是说功利幸福实质上是与所谓的“礼治”内在一致的。功利幸福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满足人们的耳目口腹之欲,其深层内涵是以“奢华”、“排场”彰显封建之礼仪、法度、规范,进而以严格的等级差别维系统治秩序:“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锺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馀;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荀子提出,古者圣王讲究各种器具的花纹颜色,制作鼓管琴瑟等各种乐器,建造各种亭台楼榭,并不是要特意制造荒淫、骄泰、奢侈、华丽,而是要贯彻隆礼尊贤的礼乐等级次序。这对于维持封建政治是必须的。可以看出,功利幸福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合礼”的幸福形态。
再次,荀子思想为功利幸福提供了宇宙论证明。一方面,荀子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3](《正名》),认为人欲合情、人情合性、人性合天,此种致思就为功利幸福提供了“合天”之论证:“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3](《天论》)另一方面,在天人关系上,荀子强调人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进而提出“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等积极有为的观点,就是强调人类应积极主动地从天地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以实现百姓的功利幸福以及国家的强盛。土地生长五谷,只要人们善于生产经营,那么就能“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鳝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3](《富国》),功利幸福因此而具有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可以看出,在荀子这里,侧重于人之利欲的功利幸福不仅“合情”“合性”,而且“合礼”“合天”。如果说功利幸福在孔孟那里是一种为德性幸福所轻视和“有限宽容”的幸福形态,那么荀子则使功利幸福开始成为儒家“合法”甚至是“合理”的幸福形态。
荀子承续了孔孟德性幸福的传统,然而又论证了功利幸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就使得儒家幸福观中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内在紧张进一步激化和凸显。荀子的幸福观无法摆脱二者的内在矛盾,但荀子在论证功利幸福的同时就一直致力于调解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对峙状态,并且最终实现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与融合。这种统一与融合具体又展开于荀子礼学视野中的“养与别”、“性与伪”。
世所公认,“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与孔子崇尚的周礼稍有区别,荀子的“礼”中,固定僵硬的礼节仪式的意味开始下降,而更多地具有了理性主义的色彩。在“礼”的起源上,荀子提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3](《礼论》)荀子认为“礼”起源于人们对于食物等生活资料的分享,进而提出了“礼者,养也”的命题。可以看出,“礼”不仅是一种规范秩序,其中还明确包含有物质功利的内容——“养”,“礼”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利”。与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之“礼”相比,“礼”在这里显然有了不同的意味。荀子又讲:“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在礼学视野中,“既得其养,又好其别”就把礼义视为“养”和“别”的统一。荀子认为,这样的礼义才是儒家礼义的真实内涵,这样的礼义能够使人们实现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之“两得”:“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一之於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3](《礼论》)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3](《礼论》)荀子提出“性”是人原始的自然材质,“伪”是人为,表现为礼法度数的隆盛。在幸福观上言之,“性”意味着人情所欲求的功利幸福,“伪”则是意味着人之德性幸福的追求:“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於伪。”[3](《性恶》)提出“性恶”、区别“性伪”不是荀子思想的最终目的。在区分了性与伪的不同特征之后,荀子进一步提出“性伪合”的响亮主张:“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3](《性恶》)这样,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通过“性伪之合”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有效地缓解了二者之间紧张对峙的局面。
综上所述,对先秦诸子有关幸福观的批判中,荀子实际已经展现出将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相统一的致思趋向。集先秦儒学之大成,荀子承续了“孔颜之乐”所奠定的儒家德性幸福传统,始终坚持了儒家德性至上的原则。但与孔孟主要侧重于精神之“乐”的幸福观有所不同,荀子明显地提升了功利幸福在儒家幸福中的地位,进一步确认了功利幸福的合法性、合理性。这样,儒家幸福观呈现出“双峰并峙”的局面。严格说来,所谓双峰并峙并非意指儒家幸福观中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完全对等。倘若二者地位完全对等,恐怕荀子就不仅不是“醇儒”而是“非儒”了。儒家幸福观中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之间所固有的内在紧张,荀子的幸福观也无法摆脱,但荀子一直致力于调解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对峙状态,最终也实现了二者在一定意义上的统一与融合,从而完成了儒家幸福观由“一枝独秀”到“双峰并峙”的折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