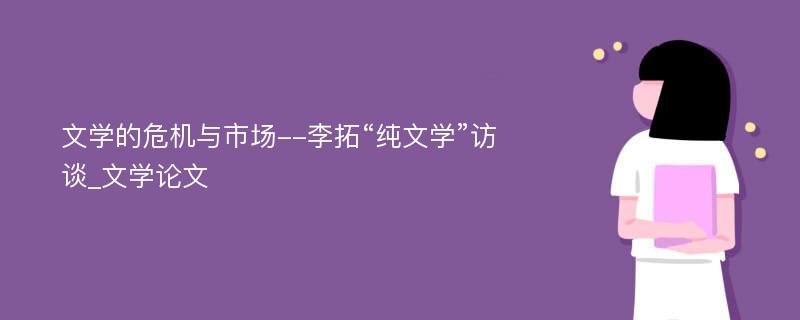
文学的危机与市场——回应李陀“纯文学”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纯文学论文,危机论文,市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陀在《漫说“纯文学”》的访谈中对“纯文学”进行一番解构,指出在纯文学的旗号下,作家批评家无论在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都在从事极其不纯的,有政治意义的文学活动。纯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历史分析。我们现在指的文学,无论在西方和东西,都是很新近的想法。在西方,文学从历史,哲学,宗教和贵族庇护体制(patronage)中独立出来,其历史背景是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日益成熟的十九世纪,类似“纯”文学的概念,伴随美学的概念,脱颖而出,它继承了浪漫主义的重想象和创造性以及变革要求,同时批判日益物化,异化的社会和实用主义。而文学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反而越变越“纯”,正是在政治斗争中无力而返归自身。不能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在远离尘嚣的文学的殿堂里施展才情。
在现代中国,独立于教化的文学概念与西学东渐有联系,在五四和新兴的城市文化市场中,纯文学的想法也有苗头,也有其理论家。由于忙于革命和救亡,文学少有机会独立,直到八十年代,如李陀说的,才打出纯的旗号。但那时的“纯”仍是以“不纯”作基础,是政治策略,是争夺说话权,是颠覆批判,是干预,是想象四个现代化,走向蔚蓝。李陀的分析中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真正以为文学可以纯之又纯的人只是划地为牢,走进窄胡同,出息不大。在八十年代陷入现代派的形式主义,在九十年代走向专业化,个人化,商品化。
纯文学的幻想,在李陀的分析中,可以接下去阐发出两种来源。在八十年代,“纯”来自古典浪漫时代的永恒的真善美理想,这与西方浪漫主义相呼应。发展到现代派先锋派,对形式的追求,就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纯美游戏,虽然有其政治无意识。九十年代的“纯”一是专业化,走写作“自专道路”的纯,另一种是远离商品大潮庇身于文学净土的向往。这使人相起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中的叔叔。对叔叔,生死攸关的人际关系或现实的悲剧,都可以化解为纯粹的文学概念。从文学外围“不纯”历史变动的角度看,纯文学的呼吁恰恰是文学危机的征兆。
但是,李陀对“纯文学”的解构中仍保留对纯文学背后隐藏的某些观念的留恋。在分析汉语写纯中,他似乎暗示汉语书写有一种自成一体的品格,一种未竞的工程,会不断完善,提高其“文学性”,从而提供一种规范的统一的审美品质和体验。在讨论借鉴传统小说修辞和手法,借鉴西方文学传统时,也有这种暗示。他强调作家应以“文学的途径”介入社会,与读者联系,似乎假定有一种文学本体的,内在的逻辑,内在的审美性。在文学课堂上当然可以讨论文学的内在逻辑,本体之类的定义问题,可一旦回到写作活动与社会历史过程的难解难分的关系,“文学本身”的问题也就自行消解了。文学纯与不纯的问题终究是某种历史形成的文体和变动的历史不断的至位关系的问题。因此,不仅中国主化遗产,西方传统可利用借鉴使文学(不妨称作“书写”)吸引更多读者,产生更活泼的形式。恰如李陀建议的,连纪实电影和录象也可成为样板,使文学成为纪实写作,更切进现实。我们有理由假设,如果八十年代的文学家是小说家,诗人的话,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的主体,就将包括散文家,专栏作家,通俗小说家,媒体节目主持人,网络设计人,独立电影制作人,作透人,心理咨询专家(弗洛依德就称他的病史记录为短篇小说,其“朵拉”病例被收入在95年美国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集中),等等。这意味着我们很多搞文学的人都得改行,其实,扪心自问,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弄文学的人在研究写作上不是都改过几次“行”了吗?
如果彻底坚持文学的批判、质疑、介入社会历史过程的功用,所谓“纯文学”就成了变动不居、驳杂不纯的活动。也许正是由于对某种难以明晰的“纯”的留恋,李陀在讨论中强调严肃文学和商品文化的对立面,用抵抗,批判这样的字眼来让文学参与现实进程,与大众对话。严肃文学和商品文学的对立和分歧是明显的,但严肃文学和商品文化的联姻,共存互利,就比较难于想象。严肃文学有终极关怀,有启蒙理想,批判的功能,有参与社会历史进程的锐气。着眼于娱乐消费的文字则重“个体”“私人”的愉悦放松,感官快乐。前者对历史进程的把握是整体的宏观的,仍然有大叙述的意思。后者则对历史感到无能为力,也不想去肩负什么历史责任。茶余饭后,卡拉OK购物商场就是历史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换言之,经济和发展就是大势所趋,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文学艺术不过是经济生活装饰点缀,读者是历史的旁观者,读文学就是在商品潮流的岸边小憩放松一下。而消闲的最终目的是养精畜锐,更好地工作挣钱。
用很严肃的话来说,严肃文学和商品文学的对立在于两种对立的历史意识。一个认为历史是人们去创造,至少是可以用人的主观能动去一次又一次重新叙述的,历史充满了机会和另样的可能。另一个则觉得历史可以自我叙述,自动发展,五彩路已铺垫,往前奔就是了,还有什么比追求汽车洋房,物资繁盛,个人幸福更天经地义的?
从目前商品文化发展的势头看,显然商品市场的大潮不是可以用什么原来的宏大叙述来力挽狂澜的。要文学参与现实,干预社会,所指的现实正是这种商品市场的社会。问题在于,文学书写与社会,与消费大众的位置该是怎样。用道德来评判历史,虽然有必要,但其效力如何?对立,抵抗,逃脱,指责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这就提出了讨价还价,妥协,甚至让步的问题。下海,文人经商,写电视剧,商业写作都是力图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李陀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通俗小说的价值,指出商品化的文学也有其可取之处。这里就产生了另一种可能。作家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通过商品的虚幻回到社会和历史中去。顽强抵抗似乎缺乏策略。这就需要对商品文化,文化市场进行重新思考。这几年来人们对商品市场的负面见的较多,但商品市场的大树是否就一定生出“苦果”还有待讨论。商品市场对人和社会不都是只有负面作用,商品确实有“解放”的潜力,有使社会发展,个人完善的可能。商品经济不一定非得走向美国后现代那种全面物化的企业公司文化(corporate culture),即使在中国已经形成负面效果了,也要设法变坏事为好事,化被动为主动。而且,商品文化已是既成事实,有了自我演变的辩证法,对它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反对抵抗。九十年代不少作家就有勇于钻进商品肚子的气魄和才能。王安忆可作一例,她的写作常有化陈腐为神奇的效果。
对个人化写作的问题,也应考虑到社会体制上的原因,直接指责和否定,说它脱离现实,不涉及重大政治思想社会问题,有过急之嫌。其实,个人化写作恰恰是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发展最敏感的症候。在全面商品化,技术化,法制化的情况下,个人与群体,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的整体已经面目不清,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弄清。想弄清整体的实际和矛盾,一般要有改变世界,使历史转向的企图。现在,市场已宣布历史已终结。人都是单独的,是经济单位,是消费者,劳力商品,受命的经理,总之,是过日子的工具。经济问题成了最大的操作性的问题,成了不容分说,势在必然的自然现象。人都趋于单向。但如果中国人还没有变成市场生产和消费的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话,就仍会有精神和感情上的需要或追求。这追求是无法投射到现存的操作性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只有反归自身,在自己身上找创造,想象的源头。个人化写作并没意识到这点,但恰恰是这无意识,这种写作精确地透视了个人对社会问题的无能。当然从文学应介入社会,有批判力来说,个人写作是应和市场。它已经赢得大量的读者,是意料中事,但如果它表达了一种不甘寂寞,一种不满,一种小规模的有所作为的话,它也不是没有启蒙和认知的作用。
李陀讨论了西方现代主义和中产阶级的暧昧关系。我认为,要借鉴现代主义,应了解它对中产阶级文化的反叛一面,重视它变革现实的企图。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是大工业中产阶级,其主导文化在文学上的形式是现实主义,世界观是实用主义,是对工业文明,既成事实,物资繁荣进化的迷信。现代主义的反的就是这一套。现代主义的出现是艺术家文人对资本主义全面物化,异化的反动,渊源是浪漫主义的冲动。在这点上,现代主义具有批判性,具有社会关怀。在俄国和东欧,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相联手,力图把文学艺术下放到日常生活中,成为改造世界的乌托帮想象和实践。西方的超现实主义,一直到法国的68年学生运动,也有这种革命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文艺为工农服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激进的现代主义的口号,反的是西方中产阶级文化将知识等级化,科层化,把艺术束之高阁,摆设在博物馆和课堂上。我们理解的现代主义,过于偏重个人和形式的问题,也就是重视现代主义对社会历史无能为力的末路时期,即它的高级“成熟”时期。西方学院重视现代主义,有其革命浪漫,社会关怀的一面,但主要的方向仍是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回避改变现实的问题,应和社会的全面市场化,理性化,专业化。因此,我们应借鉴现代主义中干预现实的那一面。后现代看起来与现实连得很紧,但总体上是应和的,缺乏批判的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