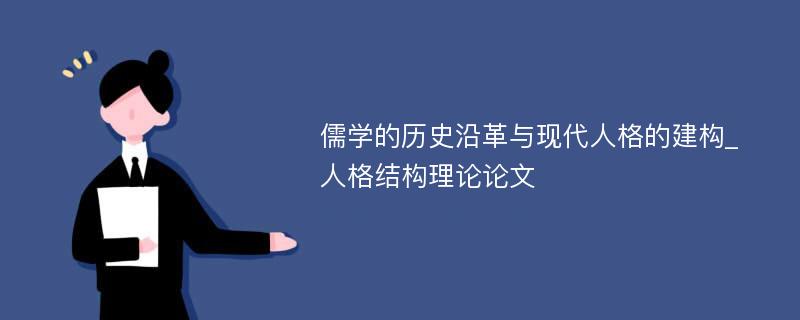
儒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人格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人格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内蕴丰富,气象万千,但从某种特质意义上说,可称为是道德人格一元的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类文化,都可以在这种一元的格局面前与古老的华夏民族、古老的中国文化区别开来。以道德人格为指归的儒学,流贯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之中,常被人称之为静态的、超稳定的文化,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这脉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内涵与历史特征,便会较为清晰地看到儒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发生的明显的自身演变,看到这种演变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及其人格精神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而看到眼前我们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还有多么曲折而漫长。
一、周代文化精神与儒家学说
我国奴隶制度的最后朝代——周朝,是华夏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历史阶段。从现存的《尚书》、《易经》等典籍记载来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崇礼敬德、渴慕理想人格的文化精神,在这个时期已经初步形成。它集中表现为文王的穆穆文制、武王的践功伐纣和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我国道德伦理思想的总结提高、与对国家典章礼乐制度的修整规定。《尚书》中的《周书》,主要记载了周公的言论和思想,还有别人对于他言论的发挥,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周代文化的基本道德内涵:1.“以德配天”,把道德视为治国的根本;2.“王其疾敬德”,君王首先作出道德表率,为臣民层层效法;3.“制作礼乐”,将统治者德政、德教的内容通过礼乐制度规范下来。《诗经》这部集乐歌与民风一体的周代诗歌总集,可以说从更广阔的范围生动地反映了周代文化的独特精神风貌,显示了当时人们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教训规劝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道德与人格自然地趋向于统一,有了道德,也就有了人格,有了令人敬仰的人格力量与魅力,周公在《无逸》篇中举列的几位先王的品行如恭勤国事、勤俭自节、广施慈悯、孝悌亲厚等,在《诗经》中已成为人们反复歌咏的操作标准,成为人们追求仰慕的人格楷模。同样地,失去了道德品行,也就丧失了人格尊严,甚至失去了起码做人的资格,而为众人所不齿。《鄘风·相鼠》是一篇鞭鞑无德无礼之徒的民歌,“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种情感抒发正是周代社会道德人格文化较为发达、并对社会成员产生全身心的涵盖与渗透的结果。
只是,奴隶制的繁荣并未能永久维持,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一个分化动荡的社会开始了。孔子是鲁国人,春秋时鲁国是保存周礼最丰富的国家。历史的变迁,使他最早感受到的是文化问题,即礼坏乐崩、人心不古。他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得出结论:原因在于人自身,是人心麻痹了、堕落了、失去了节制,才使人的行为与礼制之间产生了疏离和脱节;而人自身,是有能力反省自己、提高自己、超越自己的。因此,孔子自信地踏上了一条解决问题的独特道路:不是修改文制去适应人,而是要从人心入手,恢复和培养人的精神,重建人的创造能力,最终构成统一规范的社会道德秩序。这样,我国最早的一个理论学派——儒学便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从总体上说,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重视人的作用,注意人的内心修养;二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仁”是一个总摄许多品德的综合概念,仁在孔子那里是爱君、爱亲、惠亲的统称,它不仅是一种道德行为,而且也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道德情感,体现了一种发诸善端而趋于日臻完美的人格境界。那么,人如何去拥有这种全德,到达“仁”的彼岸呢?孔子的答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教之”,一是“克己复礼为仁”。教之,就是要把理想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人们,使他们知德明礼,有行为准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把教之的内涵由心之外推及至心之内,通过人自觉的反省、努力、学习,克服麻痹和堕落而到达行为高尚的仁人目标。
孟轲在此基点上继承了孔子的内省式思考,并进一步深化扩展,建立起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孟子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反省之路:养心、养气。“养心”就是存诸内心、求放心的修养功夫;养气之说,更有些形而上学的意味,但却有着明确的“义”、“道”内容。孟子的养心养气说体现了人们对自我潜能的一种认识和把握,同时也加强了道德与人格二者内在的统一,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唱出了一首首“浩然正气”之歌,就是到达了高超的道德修养境界、人格意志境界。由孔子、孟子等创立的儒家学说,体现了滥觞于我国奴隶制社会的道德人格文化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着人们对“人”这个社会主体所作的关注与反省到达了一个较高的理性层次。可以看出,重视人的主动精神、重视人的道德实践意志,恢复和建立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是贯串于先秦儒学的一个基本支点。
二、汉儒学说及其历史影响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各抒己见,未有高低之分,各诸侯国对各家学说的认可程度亦有不同。但这种局面到汉朝时为之一变,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孔子便被偶像化、圣人化了,儒家学说也被绝对化、权威化了。汉儒对儒学的推崇和经学加神学式的改造,使先秦儒家学说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演变与定位。
西汉的董仲舒被标榜为“为儒者宗”,而实际上他所阐释与宣扬的儒家理论,已是揉进了燕齐方术与墨家“义自天出”的天志、天命思想,改造了战国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特色的阴阳五行说,建立了以“天”为中心,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以神秘主义、蒙昧主义为理论特色的封建道德(伦理)体系。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对儒家学说最响亮的概括集成,也是他留给世人的最通俗、最完备的道德行为准则。三纲,在《白虎通义》中明确地阐释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是董仲舒在孟子“四心”说的基础上,与“五行”相比附,提出的五种行为准则:仁、义、礼、智、信。表面上看,此说与先秦儒学尤其孟子的体系颇有相似,然却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先秦儒学的确也讲秩序,讲君臣等级,但他们的着眼点更在于讲道德所赋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统一内容,讲各个层次无一例外所承载的道德义务,讲各方面通过履行各自的责任而形成的相互的关系。并且尤其强调在上者的道德垂范作用,在上者的道德状况对在下者所产生的影响。这与周公以王德领民风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以,孔子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论说,孟子有“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论辩。而“三纲五常”则不同,“三纲”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确定为不可更改的阴从于阳的从属性关系。“五常”同样是以这种绝对化的从属关系作为道德根本的。董仲舒阐述“礼”为:“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奉本》)由此可见,无论三纲,无论五常,其核心只有一个,确立法定的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序列,由此强调等级之分不可逾越;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再是相互的、相对的,而是依附的、绝对的,只有着卑者、下者对尊者、上者的服从敬顺,不见了上者、尊者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这样,贯串于先秦儒学中平等的道德实践精神和统一的道德规范观念就此消逝了。
在确定了“三纲”的等级轴心之后,董仲舒似乎觉得还不够威严和令人信服,便制造了天神的绝对权威,并在人性问题上提出了“性三品”说,形成了人“受命于天”、“先天有别”的神学说教。这样,汉儒树立起“天”的主宰力量,将人们对于道德的培养和遵从,引入对“天”的敬畏与盲从之中,完全否定了作为维系道德力量的人的自主能动作用。同时,先秦社会所萌现的朴素的公平意识、平等观念,洋溢在先秦儒学中“圣人与凡人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响亮呼唤和“民贵君轻”的民主精神,也被彻底摒弃。这种极不平等的纲常制度和理论说教虽然遭到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但是,它却作为一种为统治者所得心应手的道德模式而延续、巩固下来,成为两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且逐步演化为规定中国今后文化发展的一个轴心。这就导致了一个恶劣的困境与结局:道德的统一性被破坏了,等级地位向道德提出了挑战,虚伪性、欺骗性由此而生。它不仅造就了堂而皇之的堕落、表里不一的伪饰,而且还使先秦社会凝结起来的道德人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文化精神出现了断裂、唯上、屈从、盲目、毫无主动意志等都成了人的“美德”,道德不再体现人格的力量与尊严,反而凸现出人格的萎缩与丧失。这无疑是一个民族性格的悲剧开始。
三、宋明理学及其社会作用
随着汉王朝的覆灭,被引向谶纬迷信和烦琐考证的汉儒学日渐失去人心,代之而起的是东汉传入我国的佛学和魏晋兴起的玄学。到了唐代,统治者虽采取“三教并容”的政策,但佛学长风日甚,儒学衰败不兴,直到中唐韩愈、李翱力排佛教、弘扬儒说、重申“三纲五常”,才开启了宋明儒学发展的新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儒学发展、演化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朱熹是这个时期宋明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精通儒学,出入佛老(玄学),继承与发展了宋初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理论观点,吸收了佛学“一多相摄”、“月印万川”等所包含的理一分殊的思想,对三纲五常作了精密而系统的哲学论证。从此以后,朱熹的思想成为官方指定的儒学正统思想,他所编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历代王朝科举考试和文化人必读的教科书,朱熹本人也受到600余年的大力推崇。
然而,纵观朱熹的理学理论,其体系虽然严整,其论辩虽然精致,但在根本上,可以一言以蔽之,只是在董仲舒强调等级威严的路子上愈走愈远,将禁锢人们身心的绳索愈收愈紧而已,只不过在佛老哲学深奥体系的压力下,煞费苦心地为其理论增加了诸多哲学思辩的色彩。
唐宋儒士们的高明之处,在于意识到了理论论证的必要,把封建道德与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宇宙观密切联系起来,将其提升为独立于自然界和社会关系之上的“天理”,使“天理”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成为派生宇宙万物的精神实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天理是无所不在的,人们必须服从它,即使不想服从也做不到。这样,封建道德原则就被夸大成为宇宙的最高原则,而且附之烦琐的哲学论证,建立起了一个庞大完整的道德学说体系,为封建纲常制度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所谓“天理”,其实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熹《文集》),落实在行为规范上,父子之间就是一个“孝”,君臣之间就是一个“忠”,儿子、臣下要绝对服从父亲、君主,“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朱子语类》卷十三)如果说,汉儒在确立三纲还着重强调的是明确关系,从地位上规定等级名分,而宋明理学则推进了一步,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上大大强化了这一纲常的贯彻实施。由此,“忠孝大节”成为封建社会衡量人们道德的主要标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操守观念,也愈加演示为社会性的习俗。到了明代,封建道德更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什么孝子挖脑取肝事父母,节妇断臂悬梁守贞操等等乌烟瘴气的宣传充斥社会,实为后来进步的思想家所指斥的:礼教杀人,罄竹难书!
宋明理学崇尚“天理”,而与“天理”相对立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人欲”。“人欲”是“天理”的大敌,“人欲”的存在,直接构成了对“天理”的威胁。因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集注》卷五)朱熹甚至把儒家学说归结为一点:“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的确,孔孟儒学中的重义轻利倾向,开了我国道德史上义利之辩的先河。然而那种倾向还是与先秦历代先王种种勤俭无逸的美德、与当时国家纷争、礼崩乐坏的社会思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尚建立在事物整体性的联系之上,讲的是相对的侧重之分。汉朝时,董仲舒发展了孔孟“节欲”思想,提出了“成性”“防欲”论,即尚承认“欲”的一般合理性,而将其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防止其贪,防止超度。到了宋儒,理学家们则是在“防欲”的基础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把“人欲”视为一切罪恶的源泉,把人的全部生命权利一笔勾销,对“欲”不仅是节制、限制而且是要彻底围剿、连根拔除。宋朝以降,“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训诫便威严地响彻在人们耳旁,既成为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严厉枷锁,也成为统治者所欣赏的最高道德修养境界,遂而造成了几百年对中华民族身心与个性的严重残害。可以设想,当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到了半点容不下“人欲”、而只有所谓“天理”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悲哀可想而知!由此,儒学终于在特定的土壤下完成了自身的演变——从以人为主体的自我开发走到了对人全面专制与禁锢的历史反面。
四、建构现代人格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反观儒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对人的塑造,不难看到这样一个悖论:道德规范愈昌达,自我人格愈萎缩,社会愈流于虚伪、不道德。专制的文化对人以及人格的根本毒害,在于砍削个性以迎合社会,制造了社会与人、人与人的根本对立与分裂。在强大的社会的、家族的、官僚的、舆论的、名分的等等势力面前,个人的自我意识被层层扼杀、层层销毁,人们终将被异化为一具具无思想能力、无行为意识的躯壳,而导致了个体人格萎缩和社会活力匮乏的双向负性循环。
今天,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使古老的中国真正启开了封闭已久的大门,启动了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脚步,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愈加向纵深挺进,人们已经感受到传统文化以及所塑造的传统人格定势,正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生发着强烈的阻抑作用。有识之士站在时代高度和未来发展背景上,致力于民族文化素质研究和现代文化重建,显示了人们对历史沉疴的正视和对现代社会的理性认识。社会的现代化终究的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健全发展、人格的健全发展,一切发展将失去最终的可能和意义,社会进步也将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的现代人格特质是与现代化的目标相对应的,它与传统人格的根本区别应该是,能深刻地感知生活、自觉地顺应生活、主动地创造生活。有关学者将这些特质概括为:1.认知层面的多元选择,包括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价值取向;具有立体思维视角,在无规可循的境况中,具有较强的价值分析和抉择能力;尊重并欣赏具有不同特点的人。2.情感方式活跃、开朗、进取,适应功能良好,如何感受就如何表达,善于将负性情绪如焦虑、压力、忧郁等化合提升为人格动力。3.个性化与理性高度结合,重视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操之在我,不需要依据权威获取安全感;尊重他人的尊重与价值,重视同辈人的人际关系。(见魏磊《中国人的人格》)
虽然,现代人格及其建构问题,是一个内涵复杂、因素纷繁的大课题,不同国家对此执着的研究也因主客观因素不同而各呈风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愈来愈趋向于对人的各种权利的尊重、对人的个体意志的开发和创造能力的弘扬,有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新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91页)因此,在我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迈进之际,尤其需要自觉地摒弃传统人格中的名分人格、依附人格、多重人格(主奴人格)、圣人人格等模式,而着力向新型的本真人格、独立人格、统一人格(平等人格)、健全人格等结构转化,主动地去顺应和推动社会变革,营造现代社会的良好生活环境。
所谓本真人格、独立人格,即强调人的本来个性和自主性,强调人的自我意志和独立品格,它与传统的名分人格、依附人格形成强烈的对照。传统的名分、依附人格,典型地体现了封建等级社会对人性的抑制和禁锢,“名分”下的人似乎不体现一个具体的有个性的人,只是一个官位的、级别的偶象,是这个级别对那个级别的管辖或附庸,是繁缛礼节下的机械表演。尤其在官本位的社会,这种人格结构的政治语义在于,人的价值等同于“名分”的价值,人不在于做什么、有什么能力,只在于是个什么级别名分;人的能力不在于操之在我,自主地去实现,只在于是否得到另一级别的赏识恩宠。这种重名不重实、人为名累的依附性人格取向,导致了个性原创力和自主能力的极度枯萎,只会为社会制造僵化呆板的负面效应,实在为现代社会所不取。
冷峻地解剖我们自己的人格,将会发现,在其灵魂深处总埋有与传统人格难以切断的根,那就是一种“双重人格”基因。不管它以什么方式表现,或主人、或奴才,或倚强凌弱、或以弱媚强,或高傲自恃、或怯懦自卑等,都不离其正负转化的怪圈,这就是被鲁迅先生斥之为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尤以“主奴人格”表现得淋离尽致。在封建专制的国度,公平、平等的概念从未达到它理应具备的内涵,人们生活在层层权威奴役驱使的畏惧之中。然而,国人的劣根就在于相对于主子他是奴才、相对于奴才他是更刁刻的主子,受到了欺辱又去欺辱别人,碰到了强手便只有忍气吞声、麻木不仁了。这种主奴人格极容易造成社会性的姑息养奸、为虎作伥的风气,不反省和翦除这种劣根,现代社会的公平意识、平等观念、竞争、保护、抗争等思维指向是难以在我们这个环境生发光大的。因此,社会的变革呼唤着统一人格的真正实现。
改革开放的时代,正在造就一种促进参与、呼唤献身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时代精神辉映下,“健全人格”应该是更快、更多地活跃在当今社会中的新型人格模式。健全人格是认知、情绪、价值、信仰、想象以及生化反应等诸要素整合良好的产物,它着眼于科学的身心系统的平衡和调适,着眼于对自我各种能力的尝试和把握,它不仅仅追求某种实现的结果,而更着意整个实现的过程,它不仅仅苛求成功的喜悦和完美无缺,而更乐意咀嚼全身心投入之后的平静和无憾。与传统的“圣人人格”相比,健全人格的意义在于,它并非高大无缺、煌煌盛美,并非高不可及、令人仰叹,也不必刻意雕琢、为世人楷模。作为个人的人,他可能有种种缺陷和失误,有种种欲望和苦闷,但是他却是自我的、独立的、真诚的,他在现实中学会努力地付出,学会努力地调整自己,学会建立符合历史发展的价值系统,这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现代人格特质,也是我们人人应该经过不断体认、重组和更新去达到的人格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