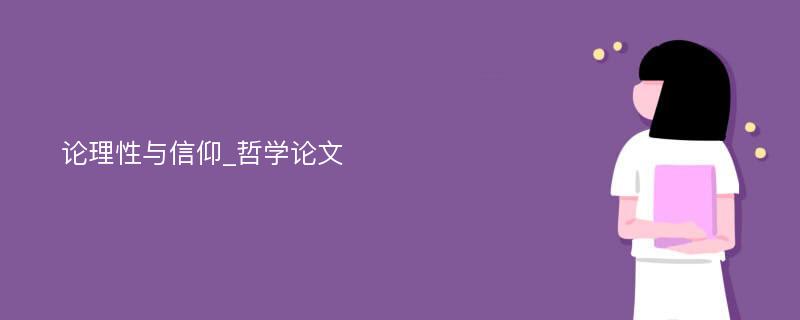
汉斯#183;昆论理性与信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理论文,汉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神学界,很少有人能像汉斯·昆(Hans Kung,1928~)那样扮演好两种矛盾的角色——既是一个学术勇气过人的改革派思想家,又是一位信仰意志顽强的护教论者。这就决定了汉斯·昆的思想特色,即由当代文化氛围来重新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意义。而他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的认识,既能充分反映出上述思想特色,同时也是他致力于“革新”与“护教”的一个关键环节。
1.历史难题
理性与信仰是一个历史难题。它使人们至今仍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困境:如果能证实关于上帝的信仰,那时是否还需要信仰呢?反之,如果无法证实,那又如何理解信仰呢?为说明这种逻辑困境,汉斯·昆分析了如下两种主要解释观念:
(1)“辩证神学”:上帝的不可证实性。上帝是主动的, 通过圣经启示而向人显现,使人有可能获得认识。若无作为恩典的启示,有罪的人根本无法认识上帝。因此,只有上帝才能证实上帝,而对人来说上帝则是不可证实的。这种解释观念是以路德的神学思想为背景的,其当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巴特、布尔特曼,以及福音神学的追随者们。
(2)“自然神学”:上帝的可证实性。 只有首先借助理性认识上帝,才能树立信仰。理性对信仰的证实来自于现实世界,因为理性对现存世界的反省可清楚地证明:上帝是万事万物的原因和目的。这是天主教新经院学派所坚持的自然神学立场,其思想来源可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
以上两种解释观念都有难以回避的问题。拿第一种观念来说,难道信仰问题是不可探讨的吗?难道“信仰上帝”仅仅是一个无法给以经验证实的论断吗?难道信仰上帝或启示便不得抛弃理性、牺牲理解吗?同样,第二种观念也面临一系列诘难。首先,能用证据来证实上帝吗?能像处理专门的科技问题那样来对待信仰问题,或用纯理性的逻辑推理来证实上帝存在吗?其次,能用上述方法来证实的上帝还可能是“上帝”吗?最后,人的理性有这么大的能力吗?康德对“纯粹理性”所作的限制不是已被广泛认可了吗?
2.改造康德
辩证神学和自然神学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都陷入了困境。有无可能走出困境呢?汉斯·昆的回答是肯定的,其思路在于重新反省康德哲学,以探求一条能平衡前述两种极端观念的中间路线。
康德哲学留下的启发在于:拒绝让纯粹理性的矛盾或二律背反进入人的现实存在范围,这就在信仰证实问题上超越了“纯理性”,消除了强制性的论证形式,但同时又保留了信仰的内容。然而,就康德哲学的问题来说,决不能先验地假定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冷酷无情的道德义务、道德法则或绝对命令。相反,证实信仰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作为整体的人”,是这种意义上的人对现实的具体感受。由上述出发点展开的论证被汉斯·昆看作是在康德哲学基础上的进一步尝试。这种新尝试主要包括以下论证环节:
(1)关于终极问题的假设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起证实作用的现实本身最终就不会得不到证实,上帝是全部现实的首要依据。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起依凭作用的现实本身最终就不会得不到依凭。上帝是全部现实的首要依凭。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演变中的世界最终就不会没有目的。上帝就是全部现实的首要目标。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就不会存在悬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现实最终可能是空虚的这种怀疑。上帝就是全部现实的存在本身。〔1〕
(2)从假设到现实
从前述假设并不能合理地推论出“上帝存在”,因为就理性而言,一方面有神论可肯定上帝,另一方面无神论则可否定上帝。然而,“否定上帝”与“肯定上帝”都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决断。面对完全不确定的现实,尤其是对现实有无首要的依据、依凭和意义这类终极问题,既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那就有自由决断的余地,但这种决断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即不是“否定上帝”便是“肯定上帝”。这两种决断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前者意味着“对现实的没得到终极证实的基本信赖态度”,后者则意味着“对现实的没得到终极证实的基本信赖态度”。
因此,在信仰证实问题上并不存在“外在的理性”,只能形成“固有的理性”。这个论点想要说明的是,信仰能在多大程度或什么意义上得到理性的证实。信仰之选择是由一些根本问题引起的,像如何理解人和世界,如何理解现实的不确定性,如何认识现实之终极根据、依凭和目标等等。对于这些根本问题,当然可以采取怀疑论或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可以肯定,假如一个人不准备“承认上帝”及其信仰的实际结果,那他永远不会获得关于上帝的合理知识。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完全面对现实,大胆献身于终极之根据、依凭和目标,现实才会以其最终的深刻性展示出来;这时尽管还会存在种种不确定性或怀疑,可信仰者却能从根本上达到并保持一种确定性或信赖,即体验到信仰上帝的合理性,使之得到理性的证实。
所谓“外在的理性”与“固有的理性”大致就是依据以上分析提出来的。前一个概念又被汉斯·昆称为“关于上帝的第一理性知识”。它之所以不存在,就是因为信仰的对象或“上帝的存在”本来就不可能先在理性上强行加以证实,然后才能承认或才有信仰。而与之相对的“固有的理性”,是指能证实信仰的那种理性本来就和“信赖上帝的大胆行为”不可分,即属于一种“实践的认识”。
(3).神学范式
据汉斯·昆考察,为解决“理性与信仰”这道历史难题,中世纪以来的神学主要提出了三种思维范式。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范式”,该范式始于奥古斯丁,形成于托马斯·阿奎那,其经典表达形式就是《神学大全》。在这部经典文献里,哲学与神学达到了空前的综合,不但将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明确定位于罗马天主教,而且使之完全奠基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性”。按照这种思维范式,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见于下图:
信仰恩典 教会 神学 基督教领域
(神秘事物)(教皇)
-----------------------------
理性自然 国家 哲学 人类领域
(证据) (国王)
汉斯·昆解释说,在托马斯那里明确划分了知识与存在的两种秩序,即“自然的基础”和“超自然的上层建筑”;这样也就形成了两种知识力量——“自然的理性”和“来自恩典的信仰”,两个知识层次——“自然的真理”和“启示的真理”,两类“科学”——哲学和神学。所以,上图展示的是一个双层体系。这两个层次虽然明显不同,但决不互相对立,处于下层的各项因素均是以上层的对应部分为目标的。
下一个值得重视的是“近代启蒙神学范式”。它是在17到18世纪形成的,不但深受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且直接以近代的政治学说、自然科学尤其是哲学为理论基础。因此,这种范式突出的是“理性”,是神学思维的“现代性”(modernity)。 汉斯·昆指出,这种以“现代性”为特征的神学思维是作为“宗教改革时期新教范式”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因为其总体倾向就是把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自然与恩典、世界与教会等统统对立起来。不过需要解释:这里的“哲学”是指一种转向了人的哲学,“自然”主要是指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而“世界”则是指近代以来日渐世俗化了的人类社会。上述范式也可借图解来表示:
(肯定性的)(否定性的)
理性-----信仰
自然-----恩典
世界-----教会
哲学-----神学
人的因素---基督教的因素
对重新反省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来说,巴特的“危机神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重重危机,诸如经济的、文化的、精神的,特别是政治的,巴特想要否定的就是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派神学。因此,从早期的危机神学到后来的辩证神学,巴特一直在推动着神学思维范式的转变,即从主观经验转向《圣经》,从历史研究转向上帝的启示,从神学概念转向上帝之道,从“一般的宗教”转向基督教信仰,从个人的宗教需要转向作为“完全之他者”的上帝。
由此可理解,巴特之所以拒斥各种自然神学,其依据就在于作为“完全之他者”的上帝及其神性。他既反对像施莱尔马赫以来的新教神学那样,用“虔诚的个人”顶替上帝和启示;也决不像传统的经院哲学那样,通过调解上帝与人的关系来平衡种种相互作用,比如人性与上帝、自然与恩典、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等等。在这一点上,以巴特为代表的辩证神学重扬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批判意向,即主张“观察人的视角”并非某种和谐的“自然一超自然体系”,而是人性与神性的尖锐冲突。正因如此,巴特神学用一种新教的“二分法”取代了“托马斯式的综合”。这种“二分法”如同下图:
(肯定性的)(否定性的)
信仰--------理性
恩典--------自然
教会--------世界
神学--------哲学
基督教-------人
巴特等人的危机神学,又一次拉开了神学范式之转变的序幕,即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的”。但在汉斯·昆看来,要真正建构一种普世性的后现代神学范式,尚需深入反思这样一组根本问题:神学的起点何在,其认识论基础又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设定我们今天的经验世界具有矛盾性、偶然性以及多样性,神学岂不必须对“知识之基础”加以重新思考吗?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针对新经院哲学和中世纪神学范式提出来的,而且也涉及到笛卡尔哲学和整个近、现代神学范式的局限性。如果重蹈笛卡尔的思路,仅仅由“方法论上的怀疑”去追究“理智的、精神的确定性”,难道这不是一条羊肠小道吗?假如有人进行彻底的怀疑,难道他不早就该怀疑这种狭义的确定性了吗?因而,难道当代神学不应当寻求某个更深刻的出发点,不仅使“理性思维之真理”而且使“理性本身的合理性”,不仅使“上帝和世界的实在性”而且使“我们自身生存的实在性”都得以重新探讨吗?总之,一旦意识到上述问题,我们还能按笛卡尔式的理智思路来考察“基本之确定性”吗?
那么,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又何在呢?汉斯·昆首先指出,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所有的思维与行为里,他们总是出于实践的目的而预设理性之合理性的,并据此而对充满矛盾的世界和人性抱有信心。这表明:我们的怀疑与思维、直觉与推理总是由“一种先在的信赖行为”(a prior act of trust)掌管着的。而能否理所当然地认可这样一种“先验的信赖”,此乃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难题。也就是说,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也不论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均不得不作出或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对此,可作如下几点反省:
首先,设若实在之本质是完全不确定的,我们每个人在根本上面临的便是一种或肯定或否定的抉择。这种抉择显然会决定着一个人对作为整体的实在的基本态度,像如何对待自我、他人、社会和世界等等。
其次,假如一个人对生活、理性和整个实在不抱有信赖态度,那么,他就会在原则上或事实上否定具有不确定性的自我和世界,从而把自己与实在隔离开来。这属于虚无主义的选择。
反之,如果一个人从根本上对生活、理性和整个实在抱有信赖态度,他就会向实在开放,即在原则上或事实上肯定具有不确定性的自我和世界。这属于“基本信赖”之选择。
最后,上述基本信赖态度所揭示的就是“一种原初的合理性”(an original rationality)、“一种内在的有理性”(an inner reaso-nableness)。就我们这个如此破碎的世界而言,上述意义上的“基本信赖”虽可作为一种恩赐而被经验到,但同时又是一项长久的任务,一种负有理性责任的勇敢行为,而这种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超理性之勇敢”(a supra—rational daring)。
汉斯·昆认定,以上分析可为后现代的普世神学提供一种具有“批判之合理性”的根本方法,以克服传统思维范式在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上的诸多失误,因为按此方法可明确以下几条基本界线:
“(1)与权威中的中世纪一新经院哲学思想相反, 这条思路可表明:信仰并非高于理性。
——因为即使按假设把理性与证据划归‘自然的’层面,与生存息息相关者仍是某种绝对明显的(而非‘简单’明白的)基本之信赖(或不信赖),即以信赖态度接受‘恩典’,还是用虚无主义态度加以拒斥。
——即使‘上帝存在’这一事实被接受,其理由也并非像‘自然神学’声称的那样,严格地来自纯理性的证明或证据,而是出自一种信赖——其自身以实在为根基。
(2)与新教神学家巴特的二分法相反, 必须强调:信仰不是理性的对立面。
在日常的思维、职业和科学,以及哲学和宗教里,理性之层面发生的一切,并非与信仰不相干,或事先就和信仰相对立,而是由这样一种辩证法决定着的——肯定与否定、基本之信赖与基本之不信赖、证实与反驳,每个人,不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均可在这种辩证法里发现自己。即使连‘信仰上帝’也不像巴特神学主张的那样,即这种信念的唯一可能性仅仅系于《圣经》里的启示性陈述;毋宁说,非基督徒也有可能凭借某种信赖而相信上帝,即此类信赖本身由于以实在为根基而变成一种对上帝的信赖、一种对上帝的相信(对上帝的启示与恩典的感恩)。
(3)与近代启蒙神学的二分法相反, 我们可设法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理性不是信仰的对立面。
——因为即使理性的合理活动,也是以‘信赖理性’为先决条件的,而这一点是不能用纯理性方式作解释的。
——‘信仰上帝’并非某种非理性、盲目的、鲁莽的跳跃,而是一种信赖,这在理性看来是负责任的,同时又是以实在本身为根基的。”〔2〕
注释:
〔1〕汉斯·昆:《论基督徒》(上),杨德友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4页。
〔2〕汉斯·昆:《为了第三个千年的神学——一种普世观》(Theology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An Beumenical View,WilliamCollins Sons and Co..Ltd.and Doubleday,1988),第202~2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