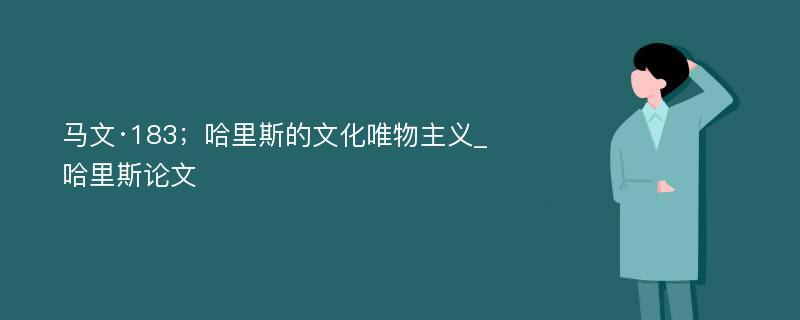
马文#183;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哈里论文,文化论文,马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1927—)1953年在哥伦比亚获得博士学位,师从查尔斯·韦格利(Charles Wagley)。1953—1980年,哈里斯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63—1966年,哈里斯曾任该系主任。1980年,他来到佛罗里达大学,并一直担任该校人类学研究生研究教授。哈里斯“过去是美国人类学学会一般人类学分会主席及1991年度杰出讲演者(Distinguished Lecturer)。”(注:Robert Borofsky(editor):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McGraw-Hill,Inc.1994.第75页。Materialism And The Study Of Culture,1995.UniversityPress of Florida,第35页。)
在哥伦比亚读书时,哈里斯就“对主张多实地调查,少闭门造车的研究方法极感兴趣”(注:哈里斯:《文化的起源》:黄晴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85页。)。自那时起,他曾在巴西、莫桑比克、 印度、厄瓜多尔和纽约等地从事田野工作。他是17本著作的编著者,其中The Arise of Anthropology Theory(1968)一书是哈里斯的成名作。在该书及《文化唯物主义》一书中,他批判了几乎所有人类学派的理论,力图确立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策略(research strategy )或范式。他认为范式是一容易引起分歧的概念,故主张以研究策略取代之。他对其研究策略所加的最新定语是:新实证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
一、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策略
虽然哈里斯对他的理论策略的论述已有中译本,但最近几年他至少对他原来的论述作了形式上的调整,使之更有条理,更系统。
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指“社会限定的与特定社会群体或人口相联系的种种活动和思想……文化诸要素由特殊的诸个体的众多可变的思想和行为建构(更明确地说,抽象)而来。”(注: Harris,Marvin:Cultural Materialism Is Alive and Well and Won't Go Away UntilSomething Better Comes Along,载于Robert Brorofsky(edlitor):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McGraw-Hill,Inc.1994,第63页。)哈里斯反对那些忽视人类学的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人类学者把文化视作纯粹的精神和主位(emic)现象,同样反对把文化定义为个体的思想和活动。
哈里斯认为,范式或研究策略规定了管制研究活动的诸原则。这些原则分为两类:1、获得、检验、证实知识的规则,即认识论原则。2、产生和评价理论的规则,即理论原则。
(一)文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
文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与所有声称拥有科学知识的学科是一致的。因此哈里斯把“科学”概括为文化唯物主义的一个认识论原则。他说,科学知识由共同的、可重复的操作(即观察和逻辑转换)获得。科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产生解释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具有以下特征:预测性;可检验性(或可否证性);简洁;范围广阔;在一个内恰的和扩展着的理论集合里是可整合的或积累性的。科学理论总是被看作尝试性的接近,而不是“事实”。哈里斯认为这种科学观来源于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因此可称之为“新实证主义”。有些人声称,由于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和混沌理论,自然科学也已抛弃了客观性和决定论。关于客观性,哈里斯回答说:“让反科学的人类学学者站起来,告诉一群病人,不存在客观有效的艾滋病、白血病治疗方法,永远也不会有;或者告诉一群物理学家,不可能客观地决定核聚变是否发生;告诉国家健康协会科学欺骗委员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panelson scientific fraud)不要担心,因为所有科学资料都同样制作, 都同样是主观的和文化上建构起来的。文化唯物主义偏爱由科学的认识论原则产生的知识,其原因并不在于科学保证免于主观偏见、误差、谬误、谎言和欺骗的绝对真理,而在于科学是最好的减少主观偏见、误差、谬误、谎言和欺骗的体系。”
关于决定论,哈里斯回答说:“决定论——现象由特定事件或原则因果地决定——的死亡被大大地夸大了。19世纪社会科学关于绝对法则的陈述很早以前就被这个认识——科学并不产生确定性和法则,而只是或然性和概括——所限定。混沌理论并不导致对于决定论体系的放弃,而是把或然主义的决定论移向现象王国(例如流体动力学紊乱)——迄今为止,这个现象王国似乎完全不可预测。 ”(注:Harris, Marvin:Cultural Materialism Is Alive and Well and Won't Go AwayUntil Something Better Comes Along,载于Robert
Brorofsky(editor):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McGraw-Hill,Inc.1994,第64—65页。)哈里斯总是强调或然性(的决定论), 以反驳他人对决定论的攻击。
哈里斯对“科学”的强调让人联系起他对自己的学术渊源的叙述:逻辑实证主义、斯金纳……在哲学史上,前者以拒斥形而上学强调科学(的统一)而闻名,甚至主张以物理学语言来统一各学科,它在社会学界的代表是纽拉克(Otto Neurath);后者被称作相对于华生的行为主义的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心理学界强调靠近自然科学的最激进代表之一。哈里斯对决定论——因果关系的强调,至少可以与他的治世精神联系起来。一个强烈希望使世界更为美好的理想主义者难道不同时希望发现现象为什么存在,怎样并为什么发展吗?( 注: Tim O'Meara 的Caus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一文认为,为了一门文化科学而进行的斗争(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已经失败,因为它以一种有缺陷的因果叙述、因果法则和因果解释(肇始于休谟,终结于波普和亨佩尔)为基础。哈里斯强调因果关系,“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是《文化唯物主义》的副标题,因此可以认为,这篇文章以哈里斯为靶子来攻击人类学界的某种思潮。 哈里斯予以了有力的反击(
参见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38,Number,3,June 1997)。
哈里斯说上述原则是和其他科学学科共享的,他的第二个认识论原则,即对主位物和客位物(emics and etics)的区分, 则为人类社会文化体系研究所特有。主位物是被研究者对自己的描述和分析;客位物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和分析,只应该使用科学的方法来得到客位物。具体地说,这个原则涉及到:(1 )精神事件(思想)和行为(身体的行动和行动的环境效果)的分离。(2)思想、 行为的主位观点和客位观点的区分。区分精神事件和行为事件的理由在于,“用来获得关于精神事件的知识的操作(观察性程序)与用来获得关于行为事件的知识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参与者传达他们头脑中发生的事情;至于后者,观察者并不依赖于行动者辨别他们身体的运动及身体运动的环境效果。”在主位事件和客位事件之间作进一步区分的理由在于,“对精神事件和行为事件的区分并不能完全明确用于识别精神或行为事件的诸范畴(资料语言)的认识论地位”。由以上区分可以得到四种类型的知识:“思想的主位物、行为的主位物、行为的客位物、思想的客位物。”(注:Harris,Marvin:Cultural Materialism Is Alive and Well and Won't Go Away Until Something
Better Comes Along,载于Robert Brorofsky(editor):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McGraw-Hill,Inc.1994,第66—67页。)
哈里斯至少告诉我们,在田野工作中,要保持一种严肃的怀疑精神,因为被研究者的描述和分析经常有意无意地歪曲了真相。他经常提到,印度人声称把牛看作自己的母亲,并且决不会故意杀死一头牛(主位的),但客位研究却否认了这一点。其次,一项严谨的田野研究成果至少应对四种知识类型作出区分。考虑到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特点(即经常要借助于主位物。有几个田野工作者只是默默地观察,而不倾听被研究者的描述和分析?)及现实研究中的弊病;(即过分依赖主位物,把它作为真相的源泉。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哈里斯的这一认识论原则是很有意义的。
(二)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
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依赖于以下假定:对于人类诸个体的生存和福利来说,某些种类的行为和精神反应比其他种类更为直接重要。并且,能够测量这些反应促进一个个体的生存和福利的效率。这些种类的反应从经验上取自研究人类遗传的需要、驱动力、厌恶和行为倾向的生物和心理科学:性、饥、渴、睡眠、语言习得;感情抚育的需要;营养和新陈代谢过程;对于精神和身体疾病的脆弱性;对于由冷、热、海拔、湿度、缺乏空气及其他环境危险所带来的压力的脆弱性。
人类的生物需要、驱动力、厌恶和行为倾向都是在社会文化体系里得到满足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即人口—技术—经济—环境结合的客位的行为方面(他又称之为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或客位行为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调节和促进这种满足。它是社会文化体系的因果中心。基础结构是一个界面,一面是以不可改变的物理、化学、生物和心理限制为形式存在的自然,另一面是作为人类使健康和福利最优化的基本方式的文化。正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不可变更性给予基础结构以策略优先权。除了基础结构以外,每一社会文化体系还包括其他两个亚系统:结构(structure)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 它们都具有各自的精神/行为和主位/客位方面。结构指家庭的和政治的亚系统,上层建筑指价值、美学、规则、信仰、符号、仪式、宗教、哲学和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形式的知识。
哈里斯认为,马克思的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原则的雏形。但他同时认为在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具有认识论上的模糊性。哈里斯根据自己的认识论原则对马克思的话进行了修正,得到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即基础结构首要性原则是(1 )满足生物需要的成本/效益的最优化或然地决定着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的变化。(2 )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的变化或然地决定着社会文化体系其他部分的变化。哈里斯指出,这一原则要求,人类学研究者要对社会文化差异和相似作出解释,就要首先考虑把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成分作为自变量,把结构和上层建筑成分作为因变量。如果这样做不能达到有效的解释,才应该从结构或上层建筑成分中寻找自变量。
关于社会文化体系内的因果性,哈里斯借用了B.F.斯金纳“根据后果的选择”(selection by consequences)这一概念。他指出, 对文化的某些部分的选择或淘汰由改进性行为的基础结构后果(成本和效益)所或然地决定。结合他的基本理论原则,他在这里的意思是,在一定基础结构条件下,一般会出现成本——效益的最优化。可以用各种指标衡量具有最优化后果的行为的成本和效益,例如:发病和死亡率、有差异的性达到(sex access)、金钱上的成本和效益、能量输入和输出、营养输入和输出。
哈里斯同时承认基础结构和结构或上层建筑之间的反馈。他指出:“问题不在于是思想重要还是行动重要,而在于在对社会文化体系的解释上两者是否同样重要……体系是不对称的。基础结构变量对于体系的进化更具有决定性……(但是),结构和上层建筑也积极地促进上层建筑的连续和变迁。但它们是在一套既定的人口——技术——经济——环境条件下发挥这种作用的。 ”(注: Harris, Marvin: CulturalMaterialism Is Alive and Well and Won't Go AwayUntilSomething
Better Comes Along,载于Robert Brorofsky(editor):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McGraw-Hill,Inc.1994,第67—71页。)
哈里斯依据“生物和心理科学”对人性作出的假定再次体现了他对科学的强调。与之相反,不强调把通过严格的实验、观察手段获得的人性假定作为理论基石的人类学学者,似乎往往强调人性的理性/非理性,自私/非自私,善/恶。由于哈里斯的基础结构指的是一套人口、技术、经济、环境因素,有人以“人口——技术——经济——环境”决定论来概括其理论基本特点,甚至认为“与斯图尔德的技术——经济——环境决定论相比,哈里斯(只不过)增加了人口再生产的因素。”(注:黄淑娉、 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343页。 )有些人认为他的基础结构概念包含了太多的经验内容,有大而不当之嫌。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科学的理论应该能够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不断得到修正,他的理论原则的经验或唯物主义性质使得自身符合这个标准。相对于学界满天飞的不可验证的“意义”,哈里斯明确地指示了另一个方向。布洛克(Morice Bloch)批评了哈里斯,认为“抛开了政治,背离了辩证法(哈里斯反对辩证法,认为辩证法不能证伪因而违背了科学原则。他戏称黑格尔“并不是马克思认为自己不得不站到其肩上的巨人,而是一只依靠在马克思背上的猴子。”(注: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66页。)他甚至曾经认为,如果达尔文的著作早出版15年, 马克思将以达尔文进化论为理论基石,而不是黑格尔辩证法。(
注:参见 OnHarris'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Current AnthropologyVol.11 Nol February 1970。))对意识缺乏正确的认识,并且拒不承认马克思的进化论体系……哈里斯的理论根本就谈不上具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注: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冯利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第153页。)实际上, 哈里斯对上层建筑反馈作用的强调表明他并非“对意识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我们倒可以反问一句,只要继承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这一基本点和对经济因素的重视,即使“抛开了政治……”,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的理论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呢?另外,是否赞成一个理论或赞成的程度如何,涉及到各种因素。例如,是否精读过一些(或许多)哈里斯的作品?一些评述文章常常使笔者怀疑这一点。
二、个案研究:好吃的(“good to eat”)
哈里斯提出了一套关于前国家社会的起源,性别歧视,阶级、等级制度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各种主要的国家一级的制度的起源的理论,并指出它们位于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主体中心。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大。遵循哈里斯关于如何深入研究他的作品的建议,这里仅介绍他对食物方式的研究。
哈里斯指出,人类学上存在文化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唯物主义三种研究饮食方式的方法。唯心主义方法以列维·斯特劳斯及玛丽·道格拉斯为代表。前者认为:“自然物种被选择,不是因为它们是‘好吃的’(good to eat),而是因为它们是‘好想的’(good to think)。”这种方法“已经时髦起来,它把研究的优先权让给食物的意义及其精神、意识形态和符号功能。”“对于道格拉斯来说,人类学家研究饮食方式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它们包含的神秘信息的解码。研究古以色列人的猪禁忌,不必研究自然史、考古学、生态学、生产猪的经济学、猪肉的营养价值。猪的所有重要特性都包含在由《旧约全书》前五卷所体现的古以色列的精神肖像中”;“折衷主义表面上站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立场之间,实际上却强烈地倾向于对具体的饮食方式作出个案的和唯心主义的解释。”(注:Harris,Marvin:Foodways:Historical Overviewand Theoretical Prolegomenon,载于Harris,Marvin,et.al.:Food and Evolution—towards a Theory of Human Food Habits,第58—59页。)
与他的理论原则相一致,哈里斯指出,文化唯物主义方法建立在以下假定的基础上:“生理—心理、环境、人口、技术、政治—经济因素对可生产和消费的食物施加强大的影响。”他提出了建立一种“最优化选择模型”的可能性。这种模型假定:某些物种比别的物种更有用;这样,为了使生产的成本/效益最优化和营养最优化,某些物种(将)被忽略。衡量最优化的变量是物种的丰富性、季节性、获得它们的时间和能量成本、营养价值、味感,等等。当然,这涉及到短期和长期最优化。哈里斯指出,即使食用某些物种在短期的成本/效益上更有利,但长期的最优化可能导致对它们的禁食。(注:Harris,Marvin: Foodways:Historical Overview and Theoretical Prolegomenon,载于Harris,Marvin,et.al.:Food and Evolu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Human Food Habits,第74—77页。)
需要注意的是,哈里斯仅仅提出了建立这种模型的可能性。作为模型的经验基础的多是原始的或较落后的地区或国家的文化——饮食方式。这些地区或国家似乎更多地受到“基础结构”因素的制约。或许对现代社会——文化的考察使他更多地注意到政治经济因素(“结构”)的重要性,而这种表述又与他的基础结构首要性原则至少在字面上相抵触(参见本文结语)。相关经验事实的繁多及在此方面理论研究的匮乏使得他谨慎地把他的有关论文称作“历史总体观和理论引论”(historical overview and theoretical prolegomenon)。
(一)神圣的牛
印度禁止屠杀牛和消费牛肉,这是最著名的非理性饮食方式。“印度牛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据估计,1/4—1/2的牛是‘无用的’,在田野里、高速公路、城市大街上游荡……印度教是印度的主要宗教,牛崇拜和牛保护是印度教义的核心……甘地说过,‘印度教的核心事实是牛保护……牛保护是上帝给予世界的礼物……只要有印度教徒保护牛,印度教就能存在。’”(注:Harris,Marvin:Good to Eat—Riddles of Food and Cultures,Simon and Schuster,1985,第48页。)公元前1800到公元前800年间,吠陀人(Vedas)统治着印度的北部。《吠陀》就是印度教的早期文本。吠陀人既不禁食牛肉也不保护牛。婆罗门的宗教责任就是屠杀牛。举行庆祝仪式时,吠陀的士兵和教士慷慨地把牛肉分给追随者,以作为对他们的忠诚的物质报答,并显示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在婆罗门教士的统治下,只允许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屠杀动物,但这一点并不能限制人们的食肉量。诸神吃掉了动物的精神部分,崇拜者则开心地吃掉了肉体部分。《吠陀》对于牺牲的描述表明,当时牺牲的牛比其他动物都多,牛肉是吠陀人最常见的食用肉。随着人口的增加,森林的萎缩,草场转化为耕地,半畜牧的生活方式让位给农耕和养牛。(奶牛业把饲料转化为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效率远远高于牛肉业)。随人口密度的增加,牛和人类竞争食物,牛肉逐渐变得代价太大,以至于平民无法在举行盛大仪式时和教士共享牛肉。哈里斯强调,正是牛拉犁的使用开始了人口增加和减少食肉量的周期。但是在不邀请平民共享牛肉很久以后,婆罗门和刹帝利还继续屠杀牛、吃牛肉。到了大约公元前600年, 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战争、干旱、饥馑给他们造成巨大灾难。一些新宗教领袖发现平民日益反对动物牺牲。佛教及其他几个主张不杀生的宗教出现了。婆罗门修正了对《吠陀》的解释,采纳了不杀生的原则。他们说,神不吃肉,《吠陀》里的牺牲仅是隐喻的和象征的行动。婆罗门声称自己是牛的保护者而不是毁灭者。保护牛更加符合印度农业生产的需要。佛教和印度教为争得印度人的支持进行了九个世纪的斗争,最后印度教获胜。哈里斯认为,印度农业体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了吃肉而屠杀活着比死了在能量和营养上更有用的动物,而禁食牛肉的宗教规定则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宗教正是在一定基础结构基础上实现最优化的要求下产生、兴盛的。
但这里的问题是,不允许杀牛但允许吃死牛不是更合理,对人们的营养摄入更有利,更有助于印度农业的发展吗?当然,这又涉及到宗教起源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宗教在调整人们的行为使之适应于特定条件的同时必然采取一种矫枉过正的形式吗?存在的其他问题还有,“在其他早期建国的中心地区(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牛肉并未成禁忌”。哈里斯的解释是,印度农业更加依靠气候(热带季风气候)而不是灌溉,因而需要耐旱的牛来度过冬季……(注:哈里斯:《文化的起源》,黄晴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43—147页。)他的解释是粗线条的。
哈里斯同时指出,虽然印度教禁止屠杀牛,但印度教农民还是故意饿死大部分他们认为无用的牛。在现代印度,印度教农民还把无用的牛出售给穆斯林商人。哈里斯和两个印度学者的研究还表明,“印度牛的年龄、性别、种比率被系统地调整以适应人口、技术、经济和环境条件。”(注:参见A.Vaidyanathan,K.N.Nair, and Marvin
Harris:Bovine
Sex
and
Species
Ratios
in
India,载于CurrentAnthropology Vol.23,No.4,August 1982。)
(二)小东西——白蚁、蚂蚱、蝉、蟋蟀、臭虫、蟑螂……(注:Harris,Marvin:Good to Eat—Riddles of Food and Cultures,Simon and Schuster,1985,第154—174页。)
问现代欧洲人或美国人为什么不吃昆虫,他们会回答:“呀!昆虫好讨厌,都是细菌。”我们不吃昆虫的原因并不是它们脏,令人讨厌;相反,我们不吃昆虫,所以它们才是脏的和令人讨厌的。事实上,人类的祖先是吃昆虫的。猿类和猴类也吃大量的昆虫。例如猴子吃虱子,吃果肉里的小虫。 人类的绝大多数文化都至少把某些昆虫看作好吃的(good to eat),西方文化只是一个例外。欧洲人原先也吃昆虫。 亚里士多德就吃蝉,他说蝉在蜕壳之前味道最好。古罗马人特别喜欢吃一种栖居在树皮里的小虫。中世纪以来,欧洲人也吃昆虫。19世纪80年代,巴黎的一家珍奇饭店甚至举行了一次精致的昆虫宴会。1878年法国议会针对消灭昆虫展开辩论。一个参议员出版了用臭虫(maybug)做汤的食谱。巴黎昆虫协会副主席为了阐明他的关于昆虫控制的“吸收”理论的演讲,非常开心地吞下了一把臭虫。
哈里斯接着指出,从营养的角度看,昆虫肉几乎和红肉、家禽一样。例如100克非洲白蚁包含610卡路里、38克蛋白质、46克脂肪。中等脂肪含量的100克汉堡包含有245卡路里、21克蛋白质、17克脂肪,100 克蛾蛹则含有375卡路里、46克蛋白质、10克脂肪。 至于昆虫携带一些病菌——这是千真万确的,但通过烹煮的办法就可以解决了。
哈里斯认为,要回答现代欧美人为什么不吃昆虫的问题,就必须检验吃昆虫或其他小东西的比较成本和效益。他引入了生态学家的最优化觅食理论。这个理论预测,狩猎者和采集者将只寻觅和收获相对于“处置时间”(handling time)(追寻、杀死、收集、运载、 准备烹调、 烹调所花费的时间)能得到最多卡路里回报的物种;或者说只要每一新项目增加(或者不减少)觅食活动的总效率,觅食者会把新项目添加到他的食物里。这样,哈里斯说,欧美有充足的牛肉、羊肉、家禽肉和鱼肉,连马肉都被排斥,谁还会需要昆虫呢?当然,这里的问题似乎是:卡路里如此重要吗?它竟然可以充当衡量最优化的标准?为什么不是蛋白质或维生素或某些营养物质的加权值,或其他标准?哈里斯也承认,关于“小东西”,他不能为这个理论的预测提供很多定量数据,这个理论大致在定性的意义上适用于欧洲排斥吃昆虫的现象。笔者揣测,可以从哈里斯对“科学”的强调来理解他对此理论的偏爱——这个理论为数学化和预测开辟了道路,并可以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修正。
哈里斯注重历史的分析(在“圣牛”及其他个案上都是如此。这一点颇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味道。)他的话外之音是,如果欧美人从历史上到现在一直吃昆虫,就不会觉得它们脏和令人讨厌了。从非历史的静态观点看,欧美人及某些东方人讨厌昆虫,似乎是昆虫对他们的伤害和社会、文化对这种可能的伤害灌输、传播的结果,哈里斯的分析令人想起他的基础结构首要性原则——他偏重与以历史的基础结构分析来解释个案,在这个例子里就是要矫正“good to think ”之偏颇或谬误、浅薄。
三、结语
哈里斯的著述博大精深。对于落后民族、地区经验资料的过分依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特点——使得哈里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强调基础结构因素。落后民族或地区更多、更直接地受到基础结构因素的制约,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组织、管理社会活动的政治因素(结构)在干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加大。其他的基本问题是:哈里斯的认识论强调科学,但除了科学知识的几个基本标准外,他似乎并没有指明人类学知识达到这些标准的最终的具体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除了区分主位和客位以外,还需要其他什么方法?需要大量各种层面的经验研究,以检验、发展文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和作为其理论原则内核的“人口——技术——经济——环境”首要性原则,使之具体化、结构化,臻于完善。
最后要指出,近几年来,后现代在中国学界风行一时,福柯、德里达等人炙手可热;人类学的学者、学生相对较少,对西方人类学的大规模引进或许刚刚开始,而哈里斯的著述不啻是不可忽略的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