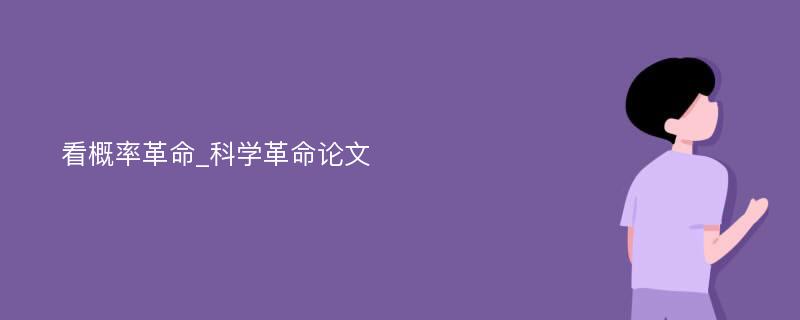
审视概率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概率”这个术语常常具有理论与经验的两重含义,在理论方面主要指概率论以及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统计理论的研究;在经验方面指概率统计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各个领域的实践。19世纪以来,概率和统计被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的各个知识领域,由此导致这些领域的知识更新和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变。1914年法国数学家艾米尔·波雷耳在题为《概率》一书中把这种变化称为一场“人们没有意识到的科学革命”。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更明确地把概率统计所引起的变化称为一场“概率革命”。
概率统计思想带来的各方面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把这种变化称为革命却在西方国家引起了一场热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19世纪以来是否可以说发生了概率革命以及怎样理解概率革命。这一讨论反映了一般科学哲学对于数学哲学的影响。参与其中的学者大多依据两种不同的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来诠释概率革命。第一个理论是托马斯·库恩(Kuhn)的科学革命,库恩于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先对科学革命提出了最初的理解。另一个是伯纳德·科恩(Cohn)的革命,他于1985年出版的《科学中的革命》中对哥白尼以来的种种科学革命做出历史分析,并进一步提出科学革命的四阶段说以及判断科学革命的四条标准。库恩的革命与科恩的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他们关于革命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科学革命”,一个是“科学中的革命”,这两个概念并不是文体风格的变化,而是在为研究科学的历史时所提供的两种不同观念的审视方法。两种理论都为概率革命的理解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本文将分别对此作一简略介绍和评说。我们会看到仅从科学革命的角度来探讨概率革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给出作者对于概率革命的主要特征的理解。
1 科恩关于概率革命的观点
在诸多关于概率革命的讨论中,科恩本人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他在《科学中的革命》中提出判断科学革命的四条标准[1]:第一条是见证人的证言,见证人包括当时的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工作者、文学家等甚至受过教育的一般人。第二条是后来叙述该学科发生了革命的历史文献。第三条是历史学家、特别是科学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评判。第四条是当代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科学家的普遍意见。当科恩尝试用这四条标准来判断19世纪以来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发展时却遇到了一个问题:即找不到一个完全符合四条革命标准的事件——不管是对当时的观察者,还是参加者,都没有发现有关于概率统计的革命宣言能与拉瓦锡的同时代人对于化学革命的评论相对比,或者与丰特奈尔等对牛顿革命的评论,达尔文及其追随者关于进化论影响的评论等典型的革命事件相对比。也没有在概率论和统计史学家的评述中发现关于革命的舆论,因此前三个关于革命的标准并不适合于“概率革命”。那么这是不是说19世纪以来并不存在一场由概率思想引起的革命了呢?科恩说不[1]。还有第四条标准可应用于概率统计革命,即当今科学家们的一般评论:20世纪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甚至数学家等几乎无一不认识到概率的思想和方法给他们所研究的学科带来的变化已经形成了与过去的思想和传统的明显决裂,没有比用革命更好的词汇来描述这种变化的特征。科恩在其《科学中的革命》中不止一次提到由于概率的引入而为科学带来的变化。
其次,科恩一再强调理解“概率革命”不适合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而是更应当侧重探讨概率思想在具体科学领域中应用意义上的革命。正如他所说“定量的统计推理的引进导致了自然科学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中的思维和方法的根本性的一系列变化。这场革命最引人注目地展现在A.凯特勒的‘道德统计学’的工作中。此外作为概率统计引入的结果之一还有医药和公共健康领域的思维方法和基础的转化。这不是在概率论学科之中的传统的革命意义上的‘概率革命’,而是指由于把概率的思想和方法引入社会的思想和分析,以及医学和公共健康领域而引起的一场革命[2]”。
最后,科恩认为要回答某一事件是否是一场革命,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方法就是对公众反对这种新思想的强烈程度加以分析。因为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大都与旧的思想是相冲突,甚至是不相容的。这一点在19世纪概率统计的方法广泛应用于自然和社会科学时表现的尤为明显。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对J.伯努利、孔多塞等人把概率论和统计学运用到社会学中的行动大加抨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反对概率论及其运用的有效性,当他在《逻辑体系》中说“分析概率论的滥用是数学的真正耻辱”时就表明了他自己的立场。许多科学家、哲学家或者是直接反对概率论和统计学在科学上的运用,或者是对它们的运用表示强烈的怀疑。现代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克劳得·贝尔纳是一位典型代表。贝尔纳在《临床医学绪论》中明确提出统计学的运用会“带来空想科学,而不能产生有活力的实验科学,即那些能根据一定的法则控制现象的科学。”
所以,尽管科恩认为不能从他所定义的一般科学革命的意义上理解“概率革命”,但是他最后还是提出了一个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结论——概率革命是存在的。19世纪由于概率思想和统计方法的应用,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出现的变化显示出革命性的力量,这一点是任何人也不能够否定的。科恩进一步从他的革命科学的四阶段理论出发,认为在19世纪末统计力学发展以前,那种革命仅是纸面上的革命,直到20世纪初期,以物理学和生物学为开端,概率的思想的引进几乎引起了所有科学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才开始了一场像牛顿的物理学革命、拉瓦锡的化学革命这种意义上的革命。
2 用库恩观点审视概率革命
当科恩从应用的角度分析概率革命的同时,许多人却尝试用库恩的理论来解释概率和统计学革命。在库恩诸多的科学革命的观点中,他在“科学革命是什么”和“测量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的作用”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最多被人们用来讨论概率革命。
1988年库恩在“科学革命是什么”一文[3]中提出的观点是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反常——危机——革命”模式的发展和补充。在这篇文章中,库恩提出了科学革命的三个特征,这些特征不是确定科学革命的精确标准,但它们却是库恩判断某些事件为革命的非常重要的线索。第一个特征是“一系列事件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转变。”在描述了他最终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经历之后,他写到“细碎片断的知识突然地归门别类,并且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将认为是革命性变化的第一个一般的特征……尽管革命留下了大量的碎片需要整理,但核心的变化却不能经历逐步的过程,而是一步完成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他曾把这个变化比作心理学式的格式塔转化。第二个特征是他早期论述过的范式的转化及其不可通约性的替换。在这篇文章中库恩这样表述:“革命的特征就是对科学描述和分类的综合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与分类的标准有关,而且也是对对象及其在原来类中的位置的分配方式的再调整,因为这种再调整经常涉及到相互交叉定义的类,所以这种改造必须是全盘的。”第三个特征是“模式、语义或者类推的重要变化——一种在什么与什么是相似的,和什么与什么是不同的这种意义上的变化”。
根据上述特征,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可以在概率论及其应用中找到许多可以作为革命的候选事件,例如1844年,凯特勒在读高低地区5738名士兵胸围的直径的总结时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生物种类的某种特点的分布恰恰好像聚集于一个客观存在的平均值的误差分布一样。这个发现给人们带来一种惊讶的刺激:广泛的人类现象突然被想像为有规律的东西——作为隶属于概率的计算。尽管许多类似的事件或许未必完全符合三个条件,但是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上述特征。
在另一篇题为“测量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的作用”的文章中,库恩又提出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概念[4]:“在1800和1850年之间,在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的研究特点有一个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在以物理学而闻名的一系列领域内。这个变化就是培根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化,也即是我称之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强调指出数学化仅仅是第二次科学革命所展示的重要特点之一,还有其它的一些方面的重大变化,如19世纪前半叶出现的科学事业规模的大幅度扩展、科学组织规范的重大变化、科学教育的完全重新改造等。这些变化几乎与数学化同样重要的方式影响到全部科学。因此,为了解释19世纪数学化的新科学有别于其他时期的科学还需要某些其它因素。
哈肯(Ian.Hacking)进一步发展了库恩的观点。他发现第一次科学革命和第二次科学革命等这样的大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们植根和流行于一个转变了的文化实践和机构的广大范围中。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拇指法则”(rule of thumb)[5]:每一场大革命必须伴随着新一类机构的产生,这种机构能够集中体现由革命所创造的新的方向。例如,伴随着17世纪的科学革命立即出现了伦敦皇家学会,并且许多国家的科学院相继成立,如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等。伴随着库恩所称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机构的成立,1831年,英国科学促进会(简称为BAAS)成立。和原来的皇家学会相比,BAAS是一个更开放、更诚实、运作更有序的机构,它充分向广大会员开放,通过联合地方组织,在不同的城市每年召开会议以“促进科学的发展”。继BAAS以后,类似的组织在其他国家也相继成立,最终通过这些组织的活动整个国家变成科学运动的一部分。
哈肯发现他的拇指法则可以很好地应用于概率论和统计学。首先是在1830年左右许多统计学会建立起来。第一个建立的是1832年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中附设的统计学部。后来在国际统计活动家凯特勒的促使下,于1835年又成立了有名的伦敦统计学会,此后英国又在曼切斯特、利物浦、里兹等地先后建立了这类统计学会。而且在一般的科学协会内部也纷纷设置统计分会。其他国家也纷纷模仿英国建立自己的统计学会。1851年在伦敦成立了第一个国际统计组织——国际统计协会,1853年由比利时政府邀请于布鲁塞尔召开第一次会议,此后会议每隔二、三年在欧洲的各大都市轮流召开。从此统计便成了世界性的共同事业。其次是国家统计局的建立。在19世纪以前有许多收集数据的国家办公室,它们主要关心的是税收和征召新兵的数量等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保密的,只属于国王或大臣的私人所有。然而,19世纪出现的国家统计局通过出版年鉴的方式使大部分数据公开化。所以从统计学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来说,各个国家统计局的建立是比统计协会更重要的事件。
哈肯认为一场大革命必需与社会本质的变革相联系,而国家的某些重大机构的出现则是社会发生变革的一种象征。尽管一个新的机构并不能造成一场革命,但是,它可以作为评判科学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拇指法则可以作为我们衡量概率的革命性的一个强有力的条件。
3 概率革命的重要的特征——人类思维观念的转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对于概率革命的理解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于“科学革命”的理解,而科学革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定义和表征,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的丰富涵义为概率革命的探讨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丰富的内涵。然而,这些解释均未对这场科学运动做出完备的历史理解和描述,更不足以揭示这场革命的本质特征,即它所导致的人类思维观念的转变。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概率论尤其是以概率论为基础的统计学的发展和应用异常迅速,这种发展最终导致了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认识人类自身的观念的彻底改变。这种改变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自然观的改变。在19世纪初,人们还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由严格的因果原理所控制的世界,这种观点也称为决定论。然而到了1936年随着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产生,人们认为世界不再是确定性的,但世界也不是完全杂乱无章,无任何规律可谈,而是充满了有规律可循的偶然性,这种规律就是概率的原理;其次是人们认识观念的变化:人们所经验的大部分知识包括自然、社会和心理领域等都可以用概率的模型表示出来的观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最后,这种认识观念也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只有当一个行为所产生后果的概率计算出来时,人们才认为这个行动是理性的,信念伴随着概率。可是,风险分析和决策论成为公众判断实际行动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现代人的信念体系中,几乎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以某种方式受着概率统计思想的影响。
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它并非是由某一个人的工作所引起,也不像大多数政治革命那样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一场剧变,以下几个主要的转折点可以给我们展示这个转变过程的一个简略而清晰的轮廓。
首先,拉普拉斯的分析概率论拉开了概率革命的序幕。1812年他的《分析概率论》的出版把概率论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为它首先把数学分析系统地运用于概率论,由此导致了概率论发生了质的飞跃。拉普拉斯以前的概率论只能处理诸如赌博中的有限事件的组合问题,自从数学分析引入之后,概率论就可以处理无限个事件发生的问题或者连续的问题,由此才能建立起比较严格的大数定理、中心极限定理、正态分布理论等法则。而这些法则的发现使得概率论走出赌桌旁,为应用于比赌博的输赢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可能,并使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统计学的产生成为可能。
第二个转折点是社会统计工作的展开。自从1789年法国革命以后,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先后建立起的新兴资产阶级政府讲究“务实的新步伐”,各国政府迫切需要有关工农业生产、交通邮电、国际贸易、金融保险等方面的统计资料,以反映国情和国力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迫切需要各种有关人口、消费、犯罪、罢工等方面的统计资料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动情况。在1820-1840年间,印刷的数据大量涌现,怎样收集、整理利用、解释、分析数字成为统计学家的任务。所以统计学所形成的冲击首先不在自然科学领域,而是即将成为社会科学的领域。当时有一句话是“自然科学要实验,社会科学要统计”,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如果不借助于统计,没有数字说话,就被认为是不完整的科学。如英国于1832年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中附设的统计学部干脆规定:统计学只限于研究人类社会中可以用数字表现的事实。为此,他们只取有关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数量资料,运用数学方法予以研究,力求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数量化。这种对数字的崇拜尽管有些狂热,但是它首次使得人类能够从数学的角度审视自身行为,并把它们置于概率论模型下进行研究。
第三,对数据的规则性的信任也是人类思维观念转化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个转化以凯特勒的工作为标志。凯特勒所处的时代正是经典的自然科学领域结出辉煌硕果的时期,许多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常常把自然科学中的方法全盘照抄。凯特勒把拉普拉斯的概率论拿来解释社会现象。凯特勒从研究当时法国、比利时、英国的司法机关的汇编出发,并在1829年和1831年分别发表了两篇研究报告,引起了社会的轰动[6]。在报告中他指出,每年犯罪的次数大体不变,不仅如此,各种类型的犯罪也有惊人的重复性。凯特勒还分析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其他表现,如结婚、自杀等,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由此得出“统计数据是有规律的”结论,凯特勒本人以及他的同时代人为这些惊人的分析所震动。从此人们认识到看起来纷繁杂乱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是按某种规律运行的,不过人类社会所遵从的规律是概率的规律,任何偶然都是可以“驯服”的。
第四个转折点是统计法则的独立。如果说凯特勒工作的目标还是寻找隐藏在随机现象中的确定性的因果结构,那么从1875年左右则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以高尔顿的工作为标志。高尔顿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身高、智力等方面杰出的父母却少有杰出的后代,这种现象可以用“向平庸回归”的原理来解释[7]。这种原理可以被看作生物特点服从正态分布这一事实的一个逻辑的结果。若简单地把正态分布归结为隐藏的因果结构与这种解释是不相适的,高尔顿的统计原理是独立于具体事实的,是数学知识的一部分,然而它们并不具备以往数学知识的绝对性、确定性和因果性。高尔顿打破了数学的应用范围仅限于因果关系范围的自然现象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也动摇了机械决定论的统治地位。
最后一个导致人类思维观念决定性改变的是非决定论的出现。早在1859年麦克斯韦尔就已断定:首要的自然定律是统计学原理。他将这种思想应用于气体运动学的研究,他提出热力学定律可能只是一条概率性的原理,而不是一条绝对性的真理,并且气体的运动速度可看成是遵从一定统计规律的随机变量。借助于这一定律即可以求出以不同速度运动的分子所占的比率或相对频率。1872年玻耳兹曼改进了麦克斯韦尔的推导方程,并使之在数学上更为严密,因此传统上就将上述定律称之为分子速度的麦克斯韦尔——玻耳兹曼分布。然而上述工作是一种纯粹理论性的创造,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05年爱因斯坦等人为布朗运动找到了统计学原理的解释,这种解释后来又为法国的彼林用实验方法所证实,于是理论的统计力学终于变为“现实的”。这些研究工作终于使人们相信概率规律可以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后来发展起来的量子论对决定论形成更大的冲击。根据量子理论人们只能观测到概率,未来的概率是可以测定的,但是观测知识本质上是非决定的。从此人们关于自然的观念包括对自然的认识和研究自然的方法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总之,从概率的思想走出机会性游戏的范围,到随机的驯服,到决定论的衰落,再到非决定论的兴起这一系列的转变构成了人类的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超越所有烦琐的哲学讨论,从普通公众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自然界和社会认识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化应当毫无疑问构成一场人类思想发展历史中的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之一,这正是概率革命所蕴涵的最重要的特征之所在。
收稿日期:2002-02-07
标签:科学革命论文; 统计学论文; 概率论论文; 社会统计学论文; 概率计算论文; 科学革命的结构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数学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