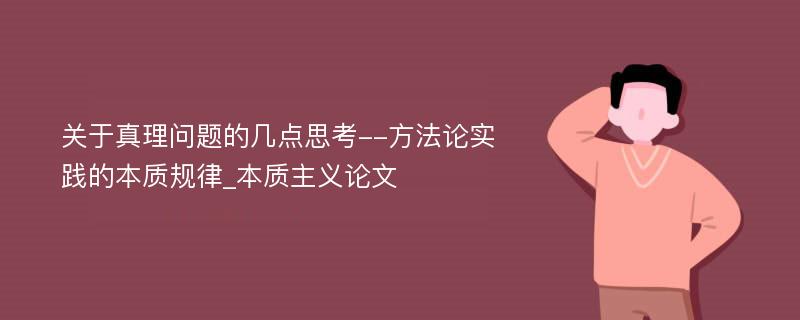
真理问题的若干思考——方法论 实践 本质 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真理论文,本质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经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等一系列论著,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先导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两大讨论和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无不和真理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真理论对解决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重大理论、重大实践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成为制定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决定无产阶级事业成败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
但遗憾的是,随着事业的发展、环境的变迁,特别是在执政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及其方法论,以致普遍出现了政治上的“左”倾,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因而不仅造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思想上的僵化、混乱,也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三方面:一是往往遗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迁就于世俗和势力,真理成了政治的附属物,理论失去了它的革命精神,沦为阐述各种政治行为合理性的御用工具,“权力真理”取代了事实真理。二是随着政权的获得,无产阶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渐渐被执政党中的许多人遗忘、抛弃了。从而日益远离群众、远离实践、远离真理。三是缺乏民主和法制,压制、打击正确的意见、主张。马寅初因“人口论”,孙冶方因“价值论”,杨献珍因“合二而一论”,彭德怀因“万言书”遭到的批判、迫害,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问题,都给真理的形成、发展、传播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追根溯源,也有三方面: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都受封建、半封建势力的严重影响,缺乏民主、法制传统。毛泽东建国初曾清醒地确认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错误的社会根源。他说:“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①]但他自己并没能避免这一错误,后来还是搞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二是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及其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酿成排斥真理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的温床。三是在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又把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神圣化的情况下,领袖、党、广大群众陶醉或满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只要照抄马列的原则,照搬苏联的经验就可完成,社会主义时期似乎不必再做更多的真理的发展和探索工作了。
这一切,都使对真理的追求屡遭磨难,导致了对真理的严重歪曲、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害和对无产阶级执政党及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不应有的窒息和禁锢。
在中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提出和实施,对真理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开始有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当前,真理问题若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必须破除各种疑虑,大胆闯出各个迷宫。本文为此拟就真理的若干问题,做些粗浅的思考。
一、真理的方法论问题
多年来,对真理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往往拘泥于几本教科书、几本原著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上,过多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论断和公式。结果出现了两个倾向:其一是概念化、教条化;其二是无视主体在认识、塑造、运用真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如“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是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等等。似乎事物、对象、真理是早已被设置好的,只待我们接触了、透视了,就把握了其中的真谛。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它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②]
可以说,真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判定、确认人对客观世界所具有的认识、改造的能力及其大小问题。真理是人所独有的,是最能显示人在思维中能动地把握外部世界这一本质特征的。如柏拉图所说:“真理原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因此,古往今来的哲学家、著作家们都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看不到或漠视这种能动性,是宿命论或机械论。当然,夸大、偏执这种能动性则会陷入精神万能论或唯意志论。
因此,必须从主客体的矛盾运动,即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③]的实践活动中去把握真理的问题。研究人或人类是怎样从对外部世界“盲目的必然性”一步步进入“为我的必然性”的,怎样使自然的世界一步步成为属人的世界,又怎样使属人的世界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地发展起来。其间,日益增多的真理和真理性的认识不仅指导着人们的实践,为人民生存发展的需要服务,而且又受这个需要的驱动,使更多的真理和真理性的认识被发现、被采撷、被运用,从而形成了人类对客观事物“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如此类推,以致无穷”[④]的认识。
还应该看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⑤]。因此,我们还必须从认识的物质技术基础来研究、考察真理的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实验和工业”[⑥]不仅是发现、发展真理所必须的物质手段,也是验证真理的必不可少的准绳。
最后,还必须从社会运动的高度把握主体认识真理的实际进程。既要考察一定时代的主体的思维能力和水平,也要看到社会制度、体制环境、习惯势力对主体的历史制约性,而不能把主体抽象成远离实践和社会的个体,搞纯概念的学理式的演绎活动。
二、实践中把握真理
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实践对真理的基础性作用的论述很多,这里只谈几点。
第一,真理的实践源泉。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最大的失误是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根本性的错误在于离开了生活、生产和人民的基本需要去理解实践,并把它作为制定执政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这样的做法只能越来越远离真理。前苏东国家经济政治的崩溃,我国20年的“左”倾错误,固然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和集权体制有关。但如果从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从人民的生存发展去认识、解决问题,就不会犯思想路线上、体制上的严重错误,就不会生出许多错误的决策。尊重生产、生活,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创造精神,就是尊重真理。这既是十几年来我国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文教体制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台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成功的原因所在。
所以,在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⑦]的著名论述时,应该想到,在社会生活中,生产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本原的意义。而真理的源泉问题也应主要围绕生产力、人民群众去探索、去寻源。
第二,真理的实践标准。有四个问题:一是实践标准的唯一性怎么看。应该说,只能从本原的意义上,从是非一时难以公断的意义上和事物发展的过程性要求来理解。否则,凡事都实践验证,则悖于常理,陷入繁琐哲学了。二是生产力标准。应该说,是实践标准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但又不能把它庸俗化。在经济生活中和事关全面性的问题时,必须运用和注意这一标准。而在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等领域就应按各自的运作规律有各自的标准。否则,会导致这一标准的泛化、庸俗化,甚至出现金钱真理、钞票真理的问题。总之,实践标准应是以生产力标准为基础的多样性的统一,是社会分工和人类生活需求多样化的现实体现。三是实践标准的辩证性或列宁所说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其实质是在时空、手段、需求和需求手段等实践要素的变化中,事物、对象对人们变化中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如在生产活动中,经过质量检测或技术检查,产品达到了要求并在投入使用中达到了设计标准,即可说该产品的设计和工艺是和生产的结果吻合的。说明已有了该产品的材料、技术工艺等方面的真理和真理性的认识。但是,随着条件的改变,或是用户要求的变化,或是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产品的质量、花色品种有了新的提高或改变,原有的“真理和真理性的认识”就可能是过时的或错误的。这是时间、手段、需求变化的情况。还有同时同地同一事物和行为对不同对象出现了矛盾标准,如吸烟之于税收和人体健康,如何权衡利弊?至于同一事物异时异地又是在不同需求对象情况下,就更难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了。然而,当条件和人的需求已经给定的时候,实践即可以证明认识和对象的吻合的确定性或绝对性了。四是实践标准的量的规定性。理论上说,因为真理是“总和”、“全体”和“过程”,因而个人的或少数人的实践不能验证、实现真理。“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⑧]从真理问题的无限存在和无限发展看,确应靠“人的全部实践”[⑨]。但从具体的真理讲,只需要用可以代表人类活动的一定数量的实践,进而达到了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并满足了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需要,即可以认为完成了对具体真理的检验。
三、真理的本质
一般都把真理的客观性,即真理具有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看做真理的本质。但如果真理的本质就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那末,显然就排斥了主体,排斥了人类历史和人的实践。就会得出,最好的真理就是没有人类参与的自然界,这也是费尔巴哈人本哲学的真理观。然而,这样也就没有了真理和真理问题的存在。
真理只能是人对外部世界认识和改造的产物,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晶。因而,它必然有人的意志的烙印,甚至就是人的意志的体现。因此,只能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来认识真理的本质问题。而这一相互作用就是实践。整个实践过程都贯穿和体现着人的意志。“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⑩]人的实践的第一步就是根据需要去选择对象或真理的内容并予以改造。原初的对象只有自然属性,经过选择利用其自然性状加工创造,使之有了社会意义,成为自然、社会属性兼有的物。野牛被驯化为家牛,是根据不同的需要依其原有的自然特点被培育成耕牛、肉牛、乳牛、药用牛等。其中,有的成为所有制关系的内容,有的成为劳动资料;有的成为消费资料;而上帝并没有做这样的安排。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创造力的提高,客体、对象或真理的内容大多已不是原始状态的自然物了,自然界中彼此并无联系也不可能自然地综合起来的各种事物越来越多地被有机地加工成人工客体。它们既是认识的成果,也作为认识的对象,成为真理的基本内容。最后,作为真理的表现形式,更是被人脑改造加工的结果,既可以体系、学说的形式出现,也可由公式、公理表达。甚至同一真理也可有不同的形式。对世界的普遍联系,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都在反映。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奥地利薛定谔的波动方程,德国海森堡、丹麦玻尔的矩阵方程,都是成立的。
值得一提的是,如前所述自然物一旦选择、加工改造后就有了社会属性,因而就有了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价值)。当它再作为认识的对象时,它的价值性同时就成为真理的内容和属性。这一点,尤其体现了人的意志要求。这种价值性,可以说,在人对某自然物有了一定的认识并选择了的时候,就潜在地存在着。一旦被加工或开发之后,就变成了现实的属性。
所以,列宁在论证实践中人所面对和作用的物时说:“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做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11)显而易见,任何具体的真理,其本质都应是对象、事物被认识并予以利用的那个属性。如列宁所说,一般情况下的玻璃杯是喝水的饮具,而压纸张时则做镇器,有雕刻或图画的可做艺术品(12)等等。
综上所述,真理的本质或定义就应是,人对其在实践中所选择或运用了的事物的属性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及正确反映。这个定义既反映了客体的本来性质,也体现了人的能动作用,是主客体现实的矛盾统一关系的体现。同时,它也克服了把客观事物及其规律都纳入到真理的定义和内容的大而不当的毛病。最后,对一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相对真理作了积极的肯定。只要是深刻认识,有真理的成分和内容,就不应因后来发现了其中的谬误而丢掉它。这样,就避免了对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正确反映的形而上学理解。正确到何种程度?是基本的、完全的,还是部分的?离开实践的抽象化的定义,只能被理解为是:完全正确。结果,就会回到恩格斯所批判的永恒真理的问题而再引发一场争论。
四、真理的基本规律
真理的规律,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研究。如我国哲学界,有从真理的认识过程,有从真理的表现形式,有从真理的发展,有从真理动力等多方面研究。但作为基本的规律,应从认识的主体、客体各自的普遍特征或其矛盾本性及主客体矛盾关系在思维中的同一得以完成的现实过程来考察。因为前者是真理规律产生的物质的、思想的基础,后者是真理得以形成的现实的普遍必然性。
主客体的矛盾本性。从客体看,任何存在、事物、对象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正如列宁肯定的黑格尔的思想:“一切事物自身中都是矛盾的,并且是在那样的意义上,即和其他命题比起来更能表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13)而从主体面对的现实对象看,“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14)从主体看,作为意识主体其思维也具有着至上和不至上的内在矛盾性。因而就存在着对存在、事物、对象认识的有限性、片面性和无限性、全面性的矛盾。
主客体在认识活动中的矛盾关系的实质就是主体如何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在思维中全面地深刻地把握客体,这是由主体各自的矛盾本性及二者相互作用的现实发展进程决定的。一方面,客体的“总和”与“关系”都不是既成的。“总和”的各个方面、各个属性、各种关系是在具体的时空中生成、发展、变化的,是经过一系列中介,沿着个别——特殊——普遍的路线完成的。另一方面,认识主体在同时作为实践主体时,因分工的限制和具体主体存在的有限性,对客体的认识也只有依局部——全部或个别——特殊——普遍的路线进行。而人的思维的不至上性则和对“个别”、“局部”等的认识相吻合,思维的至上性,抽象思维不断发展的能力和这种能力的一步步实现则和“总和”、“全面”的认识相一致。这样,客体方面、主体方面各自的矛盾性就在实践中得到了统一,并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手段的完善而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客体的“总和”、“本质”的认识。
这个进程实际上就是主体不断地对客体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抽象思维过程,就是对客体的各个方面、各个现象、各个特性的一次又一次否定,由此建立起通往真理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虽有曲折、倒退,但总趋势是在前进的上升的路线。自然科学的认识法则是如此。如恩格斯所说:“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15)社会科学的法则是如此,如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感性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理性的具体的方法。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形成和提出,实际上也是在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和重要决策的否定之否定的反思中完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的形成是如此。十四大明确提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是如此。它既是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体制模式相互否定的结果,又在吸收各自的长处的基础上扬弃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属性论的形而上学,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
广而言之,认识遵循的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感性认识的规律,实践——理论——实践的规律,辩证逻辑的分析综合律(分析否定了整体,综合又否定了部分)、抽象具体律(抽象否定了现象、具体否定了个别的抽象)以及作为真理动力的真理和谬误斗争的规律都是以否定之否定为主线,在一系列由否定环节构筑的轨道上运行的。
黑格尔总结真理的基本规律,缺点是把它演绎成了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列宁肯定说:“人的认识……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他特别赞赏黑格尔把作为真理认识史的哲学史喻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由一系列辩证否定环节组成的圆圈:“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16)列宁的论述,显然表明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基础性的主导作用。
真理的社会制约性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随着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全面贯彻,以往对真理追求的那种社会性磨难和对真理的歪曲的逆境已不复存在。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关系的形成,随着全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一定会用比过去更小的代价跨过一个个盲目的必然性的沟壑,获得更深刻更丰富因而更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关于对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日益增多的宝贵真知。
注释:
[①]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3页。
[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③][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221页。
[④][⑧][⑩](13)(14)(16)列宁《哲学笔记》,林利等译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243、237、151、218、404及271页。
[⑤](15)前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176页。
[⑦]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⑨](11)(1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2—4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