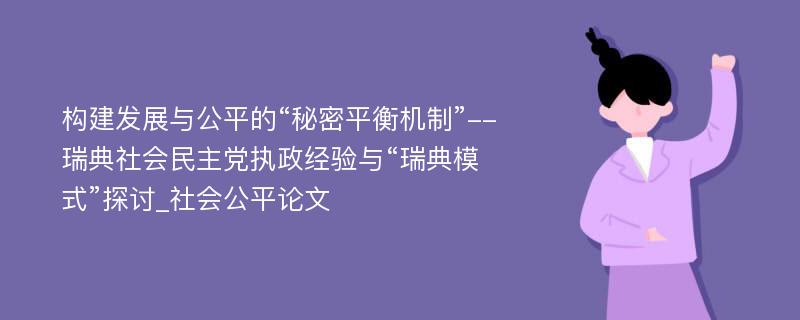
构建发展与公平之间的“秘密平衡机制”——瑞典社民党执政经验及“瑞典模式”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瑞典论文,公平论文,机制论文,秘密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来,理论界对外国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探讨,已成为执政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瑞典社会民主党独特的执政经历,举世闻名的执政成就(创造了“瑞典模式”)以及蕴藏于其中的颇有借鉴意义的执政经验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
一、瑞典社民党独特的执政经历
一提起瑞典和瑞典社民党,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第三条道路”、“福利国家”、“瑞典模式”、“北欧社会主义”这几个词,这几个词语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正是我们在这里要涉及的。瑞典社民党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走上执政舞台至今,累计执政时间已达60多年。瑞典社民党在其长期执政经历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瑞典社民党是通过议会选举道路得到执政地位的,是以建设民主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左翼政党。或许人们对瑞典社民党的判断和看法不尽一致,但以下几点背景有助于说明问题:一是瑞典社民党直接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1889年瑞典社民党成立时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直接采用了第二国际成立时恩格斯指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章。瑞典社民党创建者、第一任主席布兰廷(Hjalmar Bramting)也是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二是瑞典社民党的领导人和党的理论家们,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注:参见任军锋:《政党公民社会国家—以瑞典政党模式为中心》,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并根据瑞典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变化以及他们长期执政而积累的治党治国的经验,不断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如阿尔宾·汉森的福利社会主义理论,阿德勒·卡尔松的职能社会主义理论,奥洛夫·帕尔梅的基金社会主义理论等。上述理论设计在实践中已转化为瑞典式社会主义的施政纲领。
第二,瑞典社民党是在普选制条件下取得了长期执政地位,这种情况在当代世界政党执政史上是不多见的。1932年,社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该党第二任主席汉森出任政府首相,从而走上执政舞台。从1932年到1976年,社民党连选连任,连续执政长达44年之久。其间有29年是社民党独立执政,其余年份是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在历届议会选举中社民党的得票率从未低于40%,有两次甚至超过50%。著名的福利国家制度主要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但在1976年的大选中,社民党失去执政地位,成为在野党达6年时间,直到1982年通过与其他政党组建政党联盟才又重新在大选中获胜,重新走上执政地位,连续执政8年。1991年至1994再次下野;1994年在选举中再次获胜,执政至今,长达11年。回首这段历史,从1932年首次执政至今的73年间,瑞典社民党累计执政长达63年,在野时间9年,两度失去执政地位,又两次重新夺回执政大权,两起两落,可谓在普选制的大风大浪中操帆掌舵,经风雨见世面。对此,我们想探究的是:在这个执政63年、在野9年、两起两落的历史表象背后,瑞典社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的秘诀是什么?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把握吗?
二、瑞典社民党长期执政的体制基础
瑞典社民党在其长期执政期间,一手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瑞典模式”。广为世人称道的“瑞典模式”有两个最显著、最基本的体制特征,或者说,“瑞典模式”是由两套互相补充、互相依赖、互相约束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
其一,完整而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社民党在其44年执政期间,制定和推出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和法规,如居民建房补贴金制度,失业保险金制度(1934年);全民基本养老金制(1935年);农业工人劳动时间法(1936年);生育妇女和婴儿援助法(1937年);全民性带薪两周休假制(1938年);改善住宅纲要(1945年);儿童补助金制度(1948年);6年一贯制免费义务教育(1950年);劳资双方中央一级工资谈判制(1951年);全民附加养老金制(1958—1962年);9年免费义务教育(1962年);就业保障法(1974 年); 员工参与决定法(1977年)等等,不一而足。瑞典的国家福利制度做到了两个全覆盖:一是国家福利覆盖全体公民,无论贫富、贵贱,无论居住在大城市还是住在偏远渔村,人人都能得到无区别的、平等的、高品质的生活福利保障;二是国家福利覆盖每一个人由婴儿到老年的人生全过程,包括儿童成长、教育、就业、子女抚养、医疗、住房、工资、休假和退休,也就是人们常说到的“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的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这样一套高密度的社会福利体系,国家需要拿出一大笔钱;而这笔钱则来自于高税收。
其二,长期实行高税收政策。瑞典政府实行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制,低收入者,税率低,应交的税也少;高收入者,其税率累计计算,收入越高,税率越高,应交的税也越高,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1991年社民党政府将个人所得税率由最高时的70%降为不超过50%,加上政府在收入政策上注意照顾低收入者,在社会公共福利制度方面对低收入者倾斜,使得瑞典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据测算,一般职工与大企业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经税收和福利两次拉平后由10∶1降到大约4∶1,政府高级领导人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税前约为5倍,税后约为2—3倍。(注:参见吴江:《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 因此,瑞典社会的贫富差距被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小的。现任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先生介绍说:“在瑞典,与高福利制度相应的是高税收政策。靠高税收来提供高福利。瑞典人认为,高品质的生活,要使人人享受,大家平等,而不是少数人的享受。收入高者多纳税,用税收来调节人们的收入差异。因此,瑞典人的收入高低差距仅有几倍,贫富悬殊很小。总之,以上介绍就是通常所说的‘瑞典模式’。它按照社会福利普遍享有原则,使所有公民享有社会提供的基本福利,福利面前人人平等。”(注:转引自刘东平:《我非常荣幸,正逢在任中国—访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先生》,载《今日中国》2004年第9期。)
“瑞典模式”既是瑞典社民党的执政政绩,也是她赖以长期执政的体制基础。由于实行高福利政策,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财富的增长能够惠及全体人民;由于实行高税收政策,使得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社会差距得以相对拉平。因此,瑞典社民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甚至遭到严重挫折,但相对其他政党仍然能够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在近百年的瑞典政治舞台上一直保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在现代瑞典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和领导作用。在最近一次的大选(2002年)中赢得了39.9%的选票,比上一次大选(1998年)增加了3.4个百分点;而她的主要竞争对手温和联合党所获选票却从原来的22.7%下降了7.6个百分点。尽管瑞典国内,还有国际上对以高福利、高税收为特征的“瑞典模式”提出了种种批评和指责,认为它导致了国民过分依赖社会福利,生产效率下降,经济发展受阻,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社会精英迁居它国,等等。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双高”体制的设计和实施存在种种缺陷,但它从根本上照顾了一国之中人口占多数的中低收入工薪阶层的利益。因此,尽管人们还有各种不满和牢骚,社民党仍然能够赢得继续执政的资格。这就是我们在观察“瑞典模式”与瑞典社民党长期执政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核心问题。
三、瑞典社民党长期执政的秘诀:维系发展与公平之间的微妙平衡
瑞典社民党在60多年的长期执政期间,取得了两大成就。
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就。瑞典从20世纪初欧洲较落后、较贫穷的农业国家(有“欧洲的穷汉”之称),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跃变为20世纪末全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2000年人均GDP24277美元,多年稳居世界前5位,高于工业化国家23569美元的平均水平,更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3783美元的平均水平。20世纪50—60年代,社民党政府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而平稳的增长(46—50年为4.5%,50年代平均为3.4%,60年代平均为4.5%)(注:参见杨迟:《瑞典模式的演变及当今瑞典社民党的政治定位》,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11期。)。目前在工业化国家500家最大的企业中,瑞典占14家。在拥有最多大型工业企业的国家排名中,瑞典名列第六,拥有如爱立信、ABB、沃尔沃、利乐、宜家、伊来克斯、SKF等世界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在世界上同等大小规模的国家中,瑞典是唯一拥有航天工业和核电工业的国家。
二是维系社会公平的成就。由于社民党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人人平等和共同富裕)作为党的执政纲领,在社会发展政策上坚持向低收入者、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构建了一套较完整的全体社会成员人人平等享有的社会福利体系,使瑞典社会在百多年时间里稳定和谐。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2人类发展指数》显示,人类发展指数瑞典为0.941,全世界排名第二(第一为北欧邻国挪威0.942),高于工业化国家0.905的平均水平,大大高于0.722的世界平均水平;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瑞典为0.250(北欧邻国挪威为0.258,芬兰为0.256),属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一句话,在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方面,瑞典走在了世界前列。
社民党取得的这两大成就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平衡互补关系,对于执政党来说缺一不可。推动经济发展是执政的首要任务,没有经济增长,没有国家财富总量的增加,就不可能逐步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执政就失去了意义。即使执政,也会下野。维系社会公平是执政的法理基础。特别是在瑞典实行普选制条件下,没有适度的社会公平、普遍平等,一国之内贫富悬殊过大的话,即使经济年年有增长,但增长的大部分落入富人的腰包,多数公民也不会投你的票;得不到足够的选票,自然就失去了执政的法理依据。对此,雍博瑞先生认为:“瑞典的成功经验,是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注:转引自刘东平:《我非常荣幸,正逢在任中国—访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先生》,载《今日中国》2004年第9期。)(注:转引自刘东平:《我非常荣幸,正逢在任中国—访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先生》,载《今日中国》2004年第9期。)
对于瑞典的经验,我国领导层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重视。2004年6月,瑞典社民党政府外长莱拉·弗瓦尔慈来中国访问,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他时特别谈到1988年访问瑞典时的印象。温总理说那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看一看瑞典的秘密平衡机制,即怎样在公平与福利之间保持完美平衡⑥。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领导层对世界各国的成功执政经验、有效的治国之道的敏锐的洞察。联想到近年来中央接连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可见谋略之久、眼光之远。
寻求并维系发展与公平之间的微妙平衡(或完美平衡)是瑞典社民党在其几起几落的长期执政时间中摸索并积累起来的治国经验。所谓的“秘密平衡机制”,据我研究,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高福利与高税收之间的平衡。高福利是靠高税收来支撑的。高福利过度,必然带来高税收过度,政府的社会支出过快上升。1985年瑞典税收占GDP的比重达50.4%,而当时的欧洲工业化国家平均为38.8%;瑞典的社会支出占GDP的33.2%,高居欧洲主要工业国家前列。同时,高福利过度,使部分人想方设法减少工作时间,小病大治,提前退休等,导致生产效率下降,这就是人们所讲的“瑞典病”。1982年,社民党政府重新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推行社会保障支出紧缩政策。如削减健康保险津贴,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66周岁,降低失业保险津贴标准等,同时相应地降低个人所得税率由70%降到不超过50%。即在降低社会福利的同时,增加个人的实际收入,以求平衡。
二是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由于社民党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执政纲领,一方面实行市场经济,保护和发展私人企业,私有制经济占主体;另一方面,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程度又很大,通过高税收,政府掌握了国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并通过庞大的公共部门进行二次分配,转移支出,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有很强的控制作用和调节作用。“其再分配政策中更多地加入了社会主义因素”(注:克拉斯·波里顿:《瑞典和瑞典人》,瑞典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出版。)。二者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市场经济天然地要求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而瑞典模式本身又要求足够大的政府干预才能维持。20世纪70年代,社民党执政遇到了严重困难,当时,全球性石油危机也影响到瑞典的经济发展,社民党政府试图再次借助国家预算来维持生产和就业规模,反而使瑞典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1976年社民党失去了连续44年的执政地位,在随后下野的6年中对其政策进行了反思。1981年社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题为《瑞典之未来》的决议。1982年大选获胜重新上台执政后,作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如减少国家预算干预,允许外国银行在瑞典设立分行,允许外国人在瑞典自由购买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将原八大国家企事业管理局改制为股份制公司等。从而达到财富生产领域的高度市场化与财富分配领域的高度计划化二者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平衡。
这两套互补平衡机制保证了财富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均衡,使得全体国民能够普遍地分享不断做大的“蛋糕”(社会财富)。因此我们看到,瑞典不仅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且还是社会公平实现程度相对最高的国度。瑞典虽是北欧一小国,它的成就和经验,对于现阶段中国的发展,确有其特殊的借鉴价值。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经济持续高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9%—10%,在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积累下来一些社会问题,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薄弱、收入差距过快拉大等。我们既要不断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要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两个建设”不可或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两个保证”,既保证经济持续长久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又保证增长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也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的基本的执政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