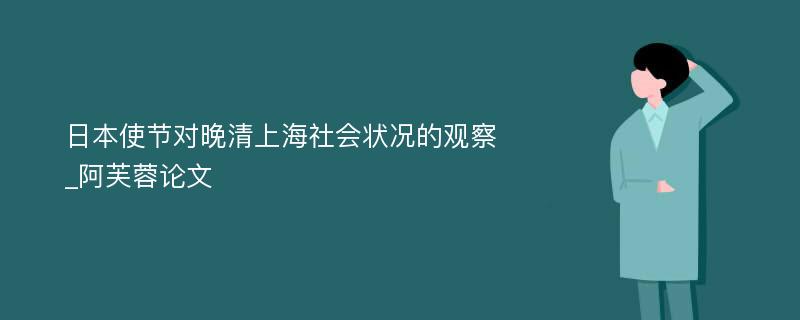
日本使团对清末上海社情的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团论文,清末论文,日本论文,上海论文,社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78(2001)02-0001-07
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即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1862年幕府第一次派遣使团乘“千岁丸”访问上海,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社情、风俗、规章制度、市场商情及日中贸易、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形势、西方列强入侵状况及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反应作了具体考察,从外国观察者角度,提供了关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诸侧面的生动画卷。
一、难民潮涌
1862年(同治元年)上海的一大社会景观,便是滚滚而至的难民潮。日本使节团诸人穿行上海城垣内外,漫步黄浦江滨,耳目所及,详悉难民情状。
1843年开埠前,上海县人口50万,其中县城及近郊人口约20万,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不能与南京(1852年90万人口)、杭州(鸦片战争前夕60万人口)相比,较之苏州(鸦片战争前夕50万人口)也等而下之。开埠后,对外贸易和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吸引周边人口进入上海。1853年3月(咸丰三年二月),太平军攻克江宁(南京),旋改称天京,以为首都,又分兵镇江、扬州。清将向荣(1792-1856)率部驻扎江宁南郊明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琦善(1790-1854)、陈金绶(?-1856)率部驻扎扬州城外,是为“江北大营”,形成与太平军对垒形势。自此,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下游展开拉锯战。长达十年的兵火,使素称富庶的江苏、浙江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冯桂芬称,苏州松江一带,“纵横千里之内,人烟寥落,邑里榛芜”(《显志堂稿》卷3)。据户部清册,1840-1850年(道光二十至三十年)江苏人口在4,200万至4,400万之间,居全国第一位或第二位,居第二位时也仅比第一位的四川少20万人;而光绪初年则锐减至2,000万,在全国排名降至第九位[1](P362-374)。太平战事及北方的捻军战事不仅导致人口锐减,还造成人口大流动——因上海作为开埠港市,西洋人在此建立“国中之国”——租界,保有相对安定,江、浙及赣、皖、鲁一带官绅商贾为避兵燹,竞相逃往上海,托荫于洋人控制的租界,而城乡民众也涌进上海租界内外以求生存。这样,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便面临来势汹涌的难民潮。
1853年9月(咸丰三年八月),小刀会首领刘丽川(1820-1855)率众乘丁祭日渗入上海县城,杀死县令袁祖德(?-1853),拘捕苏松太道吴健彰(1815-1870),占领县城。英美两国驻上海领事利用小刀会内部矛盾,将吴健彰营救出来,助其在租界重建政权。小刀会抗击清军及法国干涉军,坚守上海县城直至1855年。此间,大批城内居民迁徙租界。1854年,租界内华人达二万多[2](P49)。自此增势不减。1860年3月(咸丰十年二月),太平军东征,上海郊县、苏南各县、浙东诸县,以至安徽、江西、山东难民辗转来沪,上海租界华人剧增,不同资料说法不一,有十余万说[3](P15),有三十万说[4](P61),这些新增人口主要是难民。久居上海的文士王韬记述,咸丰十年街面“肩摩踵接”,已经人满为患(《蘅华馆日记》,咸丰十年一月二日)。
1861年12月29日,太平天国李秀成部攻克杭州,随即分兵五路进攻上海县、松江府。一波更为巨大的难民潮涌向上海。《北华捷报》1862年1月至2月,连续几期报道难民滔滔的情形。工部局华文处译述的“报告书”称,1862年租界人口达到50万[4](P61),法国驻上海代理领事爱棠的调查则显示,当时有百万左右难民进入上海(参见《上海法租界史》,第261页)。而《北华捷报》(1862年2月21日、1863年3月12日)编辑的统计数字更惊人:1862年上海市区人口骤增至300万,其中250万是难民。王韬称该年上海“人多如海”(《弢园尺牍》卷3)。乘“千岁丸”访沪的日本藩士称上海“人烟炽盛,士女杂沓”[5](P170)。旅居上海的名士冯桂芬则形容难民们“鸠形鹄面”,困窘万状(《显志堂稿》卷3)。上海道台吴煦同治元年不断收到下属的禀报,称上海近郊“庵庙各宅坟山屋,难民拥挤不堪”(《吴煦档案选编》第二辑,第286页。以下简称《选编》),“连日难民来者甚众”(《选编》第247页),“现定洋商出钱,由官派员在城内教场搭草棚数百间,安插附近难民”(《选编》第247-248页)。洋人为维持租界秩序,对难民严加控制,甚至以开枪相威胁。英国署理上海领事麦华陀(Medhurst,Jr·WalterHenry,1823-1885)发布公告称,租界内难民“设有滋扰情事,外国兵丁定即开枪攻击”(《选编》第209-210页)。
饥饿、露宿、洋兵威压,加之“天行疾疫,何其盛且广”(《选编》第368页),使难民陷于绝境,1862年一年内死亡者不下百万。
“千岁丸”造访上海正值该年盛夏,藩士们从诸多侧面看到了一幅幅难民图。
名仓予何人一天“出薛家浜,过江边,见有逃难携妻子住于船中者,其舟不知有几千百艘”[5](P107)。又在一个阴雨天,名仓散步到黄浦江边——
见黄江之水涯小舟栉比,大抵系避难之人。[5](P121)
峰洁也发现,江面小舟浮住着大批难民[5](P31)。
纳富介次郎对难民的生活状况有较详细记述:
那时的上海凡为躲避贼乱的难民,均无固定的住处,有的站在路旁,有的把船作为栖身之地,雨淋露晒,困于饥渴,为计算每日的生计,拼命挣扎,真是可怜至极。
据说难民大多来自苏州,约有十余万人。而官府无能救助他们,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于饥饿。[6](P25-26)
纳富还在长江及黄浦江江面见到多具漂浮的尸体。
峰洁则注意到,除租界涌入大量难民外,上海县城内也挤满难民。他听说,城内原先“户数一万二千余轩,人口三万六千余人”,而“贼乱以来,避难而来者颇多,城内人数分明大增”[5](P27)。峰洁还具体考察了因难民潮导致的上海大饥荒问题——
上海因四方难民群集故,米价日日沸腾(米百斤须钱九贯文,相当于日本钱二十七贯文)……今天我船雇来几个人,都似饿鬼,皮包骨,没有一个肢体肥胖的[5](P31)。
名仓予何人具体考察了上海米价腾升的情况:
余至米铺,寻常米价大抵铜钱八十文至九十五文,而现今定价十倍云[5](P208)。
米价的飞涨,自然造成难民的食粮无着。峰洁一日面对黄浦江面寄居小舟的难民,与回乡县令马铨交谈——
问曰:今此江中之人,皆何处人乎?
铨曰:此系苏州难民矣。
洁曰:大概有几人?
铨曰:难细言,约十万余人。
洁曰:此十万人,所食米盐此买于上海市乎?
曰:然矣。
曰:费价日当腾涌矣。
曰:一石米价常日三四千钱,今则九千钱矣。
洁曰:钱尽将如何?
曰:无可如何。
洁曰:官府亦无可如何乎?
曰:官府难办。[5](P31-32)
纳富价次郎也述及上海饥荒状况:
在上海,当地人和逃难来的十余万难民一起消耗粮食很多,好在上海水路运输方便,运来的粮食不会穷尽。可是米价天天暴涨,难民们买不起,成了叫化子也没有人给,最后只能饿死。由此我想,其他地区也为躲贼乱,而那个地方粮食少,运输又不方便的话,即使储有黄金,迫于饥渴,饿死的人会比上海还要多。清朝当今的衰败实在可叹。[6](P27)
峰洁为饥荒问题,与中国士人顾麟作具体探讨——
问曰:所见满江难民约不下十万,不出数十日而食将尽矣,将如之何?
麟答曰:此间海口甚便,有牛庄籼,西洋商载来。又有江北仙女庙产籼米甚多,商人陆续筹办,欠米之可以无虑。
洁曰:幸有此一事,稍放心矣。
麟曰:闻贵国米颇佳,何不贩到此乎?
曰:此大禁也,若一开之,滑商相争贩出矣,则国中米价腾涌,小户贫民将饿死矣。[5](P32)
峰、顾对话,有几点具备经济史价值。其一,上海因水路交通方便,可从周边产稻区源源运来粮米;其二,洋商已介入粮食贩运;其三,日本米质好,已为上海人所知,但日本的国策是大米不出口,以防日本国内米价升腾,引起饥荒[7](P19)。
峰洁对上海难民的痛苦深怀同情,又向中国士人管庆楳询问清朝政府的救治之策——
问曰:申江中多少难民,今此梅雨中,蓬漏舟湿,实千苦万艰,若留于此经三月之外,则人皆将病。且上海市上籼米腾涌,将以何生活?且官府有意于救之而不能乎?抑实无救之意乎?
庆楳曰:难民到此,官府设有难民厂,酌给米石,其有不虑进厂者,听其自谋生计。今江中所泊之船,皆是别处逃来自谋生计,不愿入厂者也。[5](P32)
当时上海城内外,饥民遍野,树皮草根也被剖掘殆尽,怎么可能有难民不愿意进官府开办的粥厂取食呢?管庆楳的言论显然是一种替官府遮丑的开脱之词,峰洁并不相信,故批曰“此语可疑”。
难民面对饥饿、瘟疫、兵锋等威胁,当然设法自救,有的人便想逃亡国外。纳富介次郎接待过试图出走日本的中国士人——
上海本是俗地,搞文学艺术的人并不多,有时到我们旅馆来显露风雅的都是难民。其中有一秀才,他唉叹清朝的衰败,景仰我国,对我说,现在有不少难民去了贵国的长崎,古时也有这样的事,知贵国本是仁义之邦,而且与我国唇齿相依。若诸位可怜我辈,救我们出苦难深渊,召为民,便能长期得到恩泽,得以安居。[6](P26)
中国人移居日本,古来即有,近如明末清初陈元赟、朱舜水便是移民日本的著名者,且对日本文化有大贡献。求见纳富的士人所称“古时也有这样的事”,约指上述。纳富颇同情这些人,以为接纳为日本国民,以量材使用,“他们就不会因战乱而饿死,也有益于国家[6](P26)。这当然只是作为下层武士的纳富个人的善意,当时江户幕府的国策是不允许中国人移居日本的。
二、鸦片泛滥
“鸦片”是英文Opium的音译,亦译作“阿片”。由罂粟果内乳汁经干燥而成,主要成分为吗啡,有镇痛、止泻等作用,吸食易中毒、成瘾[8]。唐代即有阿拉伯商人将罂粟输入作药用,17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从南洋传入中国。清朝雍正间开始禁吸鸦片,1796年(嘉庆元年)严禁鸦片输入,鸦片贸易成为非法走私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73年和1797年先后取得鸦片专卖和制造特权,并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1838年(道光十八年)输往中国鸦片4570箱,烟毒漫延南北,并引起白银外流,银价飞涨。中国对外贸易由先前的出超变为大规模入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没有鸦片条款,实际是默许鸦片免税输入,形成公开走私局面。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于1858年(咸丰八年)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准许外商在通商口销售鸦片,以“洋药”名目缴税,两江总督何桂清亦于当年倡言弛禁之利(《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
作为通商五口之一的上海,是鸦片贸易的重要口岸。英国驻上海第二任领事阿礼国(1809-1897),在就任第二年(1847年)呈递的一份报告中,把鸦片走私纳入上海贸易之中。当时鸦片走私不是在租界内进行,而是在停泊于吴淞口的趸船上进行的[3]。在上海进出口贸易额中,鸦片所占比重超过一半,1847年达63%,1849年更高达71%。鸦片贸易在1858年以后,因有条约保障而规模更大,诚如王韬在谈及上海贸易的感想时,沉痛指出:“其片芥(指鸦片——引者)一物累箱捆载而来者,皆毒痈中原吸膏敲髓也,民生凋敝财力耗蠹此其一端。”(《瀛壖杂志》)
上海既是鸦片贸易中心,也是巨大的鸦片消费市场,时称“上海烟馆,甲于天下”(葛元煦《沪游杂记》)。“租界中大小烟馆,数以千计”(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官民吸食鸦片相当普遍。1862年夏季访沪的日本使节团对当地烟毒泛滥的情状有真切观察。这也触发了藩士们考察鸦片战争史的兴趣。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消息,由《鸦片传闻书》播散于日本。其资料来源是“清商、兰客”(清朝商人和荷兰客商)。《传闻书》逐年逐月记述始自300年前中国输入鸦片,以及清政府一再禁止鸦片贩卖,林则徐到广东上任,厉行禁烟,其后发生战争和外交交涉、议和签约等情节。后来又有《夷匪犯境录》等记述鸦片战争始末的汉籍传入日本,并出现日本人写作的《鸦片始末》等书。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消息对幕末日本震动甚大,实启其开国先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消息,再次促使开国之初的幕府加紧开放步伐,而具有“尊王攘夷”倾向的下层武士则对西力东渐导致的民族危机忧患更深。访沪的藩士注意于鸦片战争史的考察,便与此种情怀相关,其中以高杉晋作最为突出,他曾多方探查有关鸦片战争的资料。
高杉记录的一段与中国人的笔语如下——
高杉:英夷鸦片以来战争之事,书为史册者有否?
中国士人:无。阿片通中国,始于乾隆,盛于道光,鸿胪寺黄爵滋奏禁此物,英夷遂滋事。道光二十二年提督陈忠愍公化成死之后,遂解禁。
高杉:贵邦近世之人,钦慕陈化成、林则徐等之为人者多否?
中国士人:二公名望,非特本地钦慕,四夷多想望风采,实为吾朝名臣。
高杉:弟亦尝慕其为人。(《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卷之贰》)
高杉求索鸦片战争史册,探询林则徐、陈化成等禁烟、抗击英国侵略的中国民族英雄的事迹,并表露自己对林、陈二位的钦敬。高杉一次逛书店,店主问:现有《佩文韵府》贰部,请问,要否?高杉答曰:
《佩文韵府》等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陈化成谥“忠愍”——引者)、林文忠公(林则徐谥“文忠”——引者)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同上)
有较深汉学功底的高杉当然懂得,作为分韵编排的辞书《佩文韵府》有很高学术价值,但他此时最急迫求索的,是挽救民族危机的谋略,林则徐、陈化成的思想言行自然为他所渴慕,清朝应对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也为其所关注。此类图书,高杉不计价格,一概购买。
中国在近代前夜即遭遇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推行的鸦片贸易的袭扰,鸦片是英国人主持的“英国——印度——中国”间“三角贸易”的三大商品之一(另外二种为棉织品和茶叶)。确保罪恶的鸦片贸易,成为当年英国的国策,这便是其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动因。而日本则较为幸运,打开日本门户的美国,固然也有商人参与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其规模仅次于英商,如1817年(嘉庆元年)输入中国鸦片共4,500箱,美商占1,900箱,但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美国第一次与亚洲国家签订的《美国·逻罗条约》(1833年3月20日)便写明禁运鸦片。美国与清朝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也有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1853年率舰队逼迫日本开港的柏利,亦宣布禁运鸦片。秉承这种外交传统的美国代表哈里斯(TownsendHarris,1804-1878)在与日本幕府谈判时,便把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写入《日美和亲条约》[9](P105-109)。继美国之后与日本签订条约的英、法等国也只得沿袭美日间的这种禁运鸦片的先例。因此,日本开国之际避开了鸦片之祸。故后来伊藤博文说:“与一国立善约,则他国遵之”[10](P18)。日本人既然未蒙鸦片之祸,1862年访沪的藩士们当然特别震惊于中国的烟毒泛滥,同时又天真地认为,只要有人出来呼吁禁止,即可阻挡鸦片流行。日比野辉宽在与中国官员华翼纶交谈时,即劝华氏出来挽救局面——
欢成:鸦片、邪教之有害于国家,不鲜少,今也公行,然而往往看饥饿之人,兄何不献白而救之?
华翼纶: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之一叹
华翼纶身为县令,又曾率兵多次出战太平军,在与日本藩士交往时,颇有豪迈气概,但言及救治鸦片之害,他却自叹无能为力,足见此害之广、之深,决非一般性呼吁和举措所可挽救。
纳富介次郎关于上海烟毒弥漫的记述最详,并涉及到鸦片禁而不止的原因——
清国近几年有很多人吸鸦片烟,官府最终也无法制止。现在在上海以吴煦为首的官吏也都吸鸦片。因此,虽说对百姓施行严禁,但无人遵守。[6](P31)
上海官绅民众吸食鸦片者甚众,道台吴煦等政府要员吞云吐雾,就连痛论鸦片之害的沪上名士王韬,本人也是瘾君子。上海的官绅出入烟馆,又在家中自备豪华烟具,平民缺钱,甚至讨取烟馆洗刷烟具的残水饮用,以解烟瘾。据光绪年间教会医生的一项统计,上海各类人吸鸦片的比例为:苦力50%,工人30%,商人40%,官绅无统计,而南京官绅吸食者为50%,上海亦应相近[11](P605)。近半数的上海成年男子吸鸦片,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态!纳富向当地人打听,鸦片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答复是:“鸦片烟味儿极美”,虽明知有毒,甚至危及生命,但“心气不爽,或做事感到疲倦时,吸口鸦片会顿觉精神振奋。因此,人们最终还是废止不了鸦片。”[6](P31)
纳富记载,“千岁丸”离开上海港前,曾雇请一位领水员,费用80银元,是很高的报酬。这个领水员是当地人,会讲英语,却衣衫破旧、面黄肌瘦。纳富写道:
在黄浦出发前,中牟田仓之助问他:“你每月有几次这种活”回答说:“有时两、三次,有时四、五次。”中牟田又问:“你有父母妻儿吗?”回答说:“没有”。又问:“那么,你是喜欢赌博或沉溺于女色了?否则,你挣那么多钱,怎么衣着如此不整,而且身体又那么瘦弱?”他答道:“我不好别的,只嗜好吸鸦片。挣的钱虽多,但还不够吸鸦片的呢。”[6](P32)
藩士们都不相信鸦片有那样大的吸引力,竟使一个人倾家荡产。但紧接着藩士们亲眼看到的情景,终于使他们明白了鸦片烟的特殊威力——
过了一会,此人来到我们住处,从一个精美的盒子里取出烟具,平卧着抽起来,约半刻钟,大家都凑过来看稀奇。其烟充满了屋子,其味难闻。因此就制止他吸烟,可他根本听不进去,眸神荡漾,如醉如睡。过了一会儿,恐有事故,仓之助大喝一声,把手放到刀把上,脸上露出怒色。见此,那人吃了一惊,匆忙收起烟具走了。
日比野辉宽的《赘肬录》1862年8月1日(七月六日)也有关于中国领水员(文称“水路主人”)吸食鸦片的描述,情节与纳富记的略同。日比野发抒感慨道:
余窃闻水路主人一月获利二百余金,然而却贫苦到这种地步,鸦片费用大到如此,使人贫苦,甚至朝吃夕死也在所不惜。嗟乎!陷害生民于迷惑、沉溺之中,莫如其甚也
纳富还耳闻若干烟毒泛滥的情形——
我曾听清人说过,官军之所以屡次打败仗,原因是军中都吸鸦片,大敌临头,还躺在床上吸鸦片。吸鸦片是定时性的。一到时间,即使在战场上也得吸,否则就受不了。我听了尚半信半疑,但看到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才认识到所闻不假。可怜的是这烟又戒不掉。[6](P32-33)
名仓予何人与中国士人王互甫讨论烟毒泛滥问题,王互甫叹息没有解毒良药,名仓戏曰:
除此烟毒需良方,今求取其药甚难,却有,其药名“则徐丸”、“化成汤”。[5](P198)
王互甫闻言大笑。可见,日本藩士寄望于林则徐、陈化成这样的民族英雄再世,禁除烟毒。
日本藩士在上海逗留时间不长,但所见烟毒泛滥情形已经触目惊心。与他们同期在沪的杭州人葛元煦,后来在所著《沪游杂记》(1876)中专载《洋烟害》一目,形容一个吸鸦片者,“但见愁容如枯木,勉强支架在人间”。并引《竹枝词》说:“洋烟之害,害人若投渊”。19世纪70年代访华的日本汉学家竹添光鸿(1842-1917),也十分注意鸦片泛滥的情形,他作诗讽罂粟花——
翠袖轻飞不受尘,娇红艳紫殿残春;
前身应是倾城女,香色娱人又杀人。[12](P221)
此诗揭示了在罂粟花轻柔香艳外表背后的杀人本质。另一位日本汉学家冈千仞(1832-1913)于19世纪80年代访华,也痛论烟毒“缩人命,耗国力”[13](P76),将“烟毒”与“贪毒”、“六经毒”并称中国“三毒”,认为“非一洗烟毒与六经毒,中土之事,不可下手”[13](P84)。这些论述与纳富介次郎等日本藩士60年代初的见闻相合,印证着林则徐1838年9月(道光十八年八月)的著名奏章:如果对禁烟“泄泄视之”,后果将是——
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19世纪中后叶的中国,正呈现出这样的危局。
三、洋教传播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是西方人传入中国的宗教,近代中国朝野通称“洋教”。基督教入华,可追溯至唐代,时称景教,后中断;元时复入,称也里可温教,后又中断;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入华,万历间,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入北京,天主教在中国各地传播,明亡前夕信徒达38,000人[14](P380),上海是流行地区之一,明代内阁大学士、上海人徐光启(1562-1633)便是著名受洗者。1608年,他请天主教传教士郭居静来上海徐家汇建立祈祷所传教,徐家汇周围多人受洗入教。清初天主教在中国仍有发展,耶稣会士、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任钦天监监正,主持修历,并曾做过顺治皇帝的老师。1663年(康熙二年),江南共有12座大教堂,5万名教友,上海就有2座教堂,4万名教友。雍正间禁教,基督教在中国基本匿迹。道光间签订南京条约后,基督教再度入华,江苏省是传教主要地区之一,19世纪40年代以降,到江苏传教的教会有圣公会(1845)、美国浸信会(1847)、监理会(1848)、美国长老会(1850)、内地会(1854)等,60年代中期江苏的信徒在五万人以上[15]。这些来江苏传教的教会都以上海为重点。
1843年,上海已有教堂35个。40年代以降,上海的主要教会设施如下——
1843年2月,江南教区第一所修道院在上海郊区佘山附近张朴桥开设天主教修道院,1850年6月迁浦东张家楼。
1853年,董家渡主教堂(正式名称方济各·沙勿咯教堂)落成,这是一座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至今保存完好。
1844年,耶稣会修院初设青浦横塘,1847年迁至徐家汇,1860年在肇嘉浜东岸辟建新址。
1845年,传教士文惠廉在上海成立美圣公会。
1861年,洋泾浜天主堂(正式名称圣约瑟教堂)落成,为拉丁式十字平面、单钟塔式立面建筑。
1862年,即日本幕府使节团造访上海之际,洋教已经在这里有相当规模的发展,藩士们在沪上看到一些教堂建筑,读到一些宣教出版物,并接触到教会的中国信徒。天主教16世纪在日本曾广为传播,17世纪初开始被禁止,1613年(庆长十八年)江户幕府发布禁教令后,天主教更被视为非法。连“千岁丸”的航行十四条规则中,有一条便是禁止传播异教,乘员本人也不准信仰异教。武士们则普遍视洋教为邪恶,访沪的藩士们当然也以此种眼光看待洋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人信教深感困惑和不满。纳富介次郎写道:
一天,有两个书生来访,我病卧在床。同屋的朋友们和他俩笔谈,谈话之余,书生问:“贵国信天主耶稣教吗?”回答:“过去该教传到我国,与我朝结仇,因此我国禁止此教。”书生说:“先生们尚未读过《圣经》吧?我们今天带来了,想进呈给你们。”我的朋友拿过来一看,是耶稣的邪教书,大怒,将其书扔掉,大家争论起来,最后把他们推出了门。然而,转天他们再次来访,我们不允许他们进来,他们就站在门外。[6](P27-28)
看来,这两位中国书生已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到日本人这里来传教,竟不顾斥责,吃了闭门羹也不泄气,仍然候在门外。后来,他们又通过日本藩士的朋友马铨将《圣经》偷偷给日本人,其后果是——
我的朋友们更加生气,大声谴责,大家都出去,将那两个书生赶走。在此之前他们也曾过来几次,找到机会就劝我们,要给我们书。这两天终于被赶了出去。大概因为吃了苦头,从此不再来了。唉!清国连读书人都尊奉这个,更何况愚民们呢
据纳富所闻,“洋人在上海首建的耶稣教堂在道光廿年”,这可能是指的张朴桥天主教修道院,作为江南第一座教堂,该修道院建于1843年(道光廿三年)。关于教会吸引信众的办法,纳富记曰:
为了让愚民们加入教会,先发给很多金银,因此有很多穷苦人不管宗教的善恶,如能有助于糊口就信奉。所以,该教终于在天下兴盛起来。又听说洋人在上海建医院,招来很多病人给予治疗。药剂等都说是奉上帝之命发给的,病愈也是上帝的拯救,未必是医生的功劳,以此让人们明白是天主的恩惠。洋人本来就精通医术,是清国的庸医望尘莫及的。愚民们生命得以保住非常高兴,真认为是上帝的拯救,便自觉地尊敬起耶稣了。
纳富所述,大体符合洋教传教方式:以福利救济开路,以办医院、开学校争取信众,正如一位法国军医所说:“由过去的经验所知,在中国创办华人医院为扩展影响力的巧妙工具。”[16](P20)
日比野辉宽则记述了对洋教士和教堂的感受。日本使节团住在法租界内的荷兰商馆点耶洋行附近的宏记旅馆,一日早起,日比野到楼下洗脸,看到“佛人在我旁边站立,口里念念有词,此人容貌怪异。秃头佛衣,面目似鬼。此时张棣香来,我问这是什么人?棣香云:这是佛兰西耶稣教传教士,就住在楼上。余闻之愕然,怒发冲冠,目眥张裂,不由得仰天长叹。”[6](P74)日比野在论及上海耶稣堂之后,作诗感叹曰:
夺国资基在此楼,满堂诸士可知否?
试凭栏槛看黄浦,浊浪排天万里流。[6](P74)
藩士们还对洋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经医药等福利事业蠃得民众的现象十分警惕,认为日本要格外提防。高杉晋作6月20日(五月二十三日,与五代友厚访问英国人缪尔赫茨特,缪氏是耶稣教传教士,中文名慕维廉,施耶稣教于上海士民。高杉指出:
城内教堂,缪尔赫茨特之所关也。缪尔赫茨特之所常居,亦有教堂与病院,谓施医院。总西人教师之施教于外邦,必携医师,有士民病且穷者,乃(治)(此字缺,据前后意补字——引者)其病使入此教,是教师致教于外邦之术也。我邦之士君子不可不有预防也。(《游清五录·上海淹留日录》)
中牟田仓之助更认定,太平军与西洋人因宗教信仰相同,会结合到一起。他说:
英吉利表面上帮助清朝防御长毛贼,实际上给长毛贼供应好器械,这都是通过耶稣教会进行的。……我认为,由于信仰耶稣教,英吉利等将把长毛掌握在手里,终于从清朝手中夺取天下。如果天下夺得,英吉利的策略就达到目的了(中牟田仓之助《上海滞在中杂录》)。
高杉也认为,太平天国起事是洋人洋教蛊惑的结果,而这正是日本要特别警惕的。他说:
夫夷狄夺人之国则先取其心。或以厚利啖之,或以妖教蛊之,黎民听信,一举灭其国,易如摧枯(《东行先生遗文·书翰》,第20页)。
这便是日本藩士们反洋教的出发点。
收稿日期:2001-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