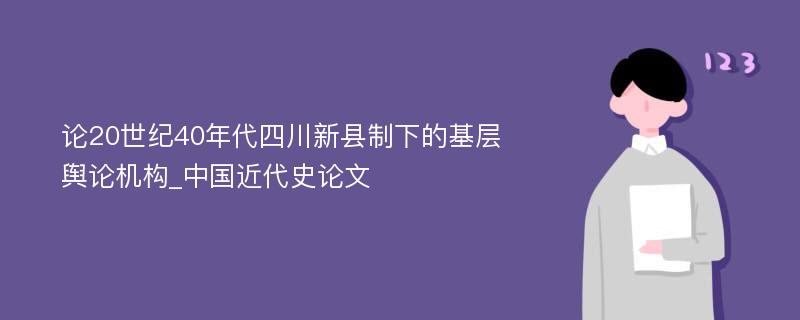
试论20世纪40年代四川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县论文,民意论文,试论论文,基层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3.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5-0089-07
一 “民意机构”的建立
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要建立的基层民意机构包括保民大会、乡镇民代表会、县临时参议会及县参议会,建立民意机构是新县制下地方自治政策的独特内容。尽管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如“必须将官办自治改为民办自治;将土劣自治改为革命自治,而后真正地方自治始有彻底实现的可能”[1],以及纳保甲于自治之中,“民选精神似应维持”[2](504页)等卓见,但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按孙中山先生的地方自治思想制定的一系列自治法规,还是30年代中期按蒋介石的意图所推行的“纳保甲于自治”的政策以及县政改革,但政府都未能明确下令建立基层各级民意机构[3]。直到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10月,行政院颁发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即新县制),才明确要求建立基层各级民意机构,作为地方自治政策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蒋介石国民政府要求建立各级民意机构不只是一种政治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它确实是政府力图贯彻的一项政策。这一点从当时各级政府机构所颁政令中可以得到反映。
新县制颁布后,蒋介石手令四川省“自1940年3月起全省各县一律实施,限期三年完成”[4]。按照该手令并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四川省制定了《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三年计划大纲》,将新县制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其目标是循序渐进地实现地方自治,即借助由上而下(由县而乡镇而保甲)的行政组织来指导建立由下而上(由保甲而乡镇而县)的民意机构[5]。四川省所属的各行政区纷纷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办法。四川省第三行政区,自1940年3月开始实施新县制以后,“各县区均经遵照曾颁各项法令及规定程序,按步推行,未或稍懈,并遵省令指定巴县、江北两县为实施新县制示范县”[6](1页)。要求务必从1941年7月开始筹备保民大会和乡镇民代表大会,在1942年7月前成立县临时参议会。巴县制定了《筹设乡镇以下各级民意机关工作推进时限表》,自1942年6月“通令各区乡镇局积极筹备”到1942年12月“呈报乡镇民代表会首次会议记录”为止,共分为14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对应几天到一个月的实施时限[7]。为了确保该计划的顺利进行,巴县政府还制定了《筹设乡镇以下各级民意机关注意事项》,要求在户长会议到保民大会再到乡镇民代表大会的层层选举,必须在指导员及民政干部的监督之下进行。在选举乡镇民代表时,“各指导员及乡镇长应切实指导各保公民务须选举公正合格人士充任,同时严密防范土劣、哥老会、异党分子把持操纵或形成党派争执”[7]。总之,国民政府确实希望按期建立民意机构,希望通过新县制所设立的各级民意机构来使民众负担平均一点,发挥民众(包括士绅、其他有产者以及一般民众等)的积极性来有效完成摊筹派募、征丁等任务,同时抵制地方各级官僚及恶势力的贪污中饱等行为,充分动员人力、物力、财力以利抗战及消灭异己势力以维护自身统治,应该是可信的。
首先,通过民意机构来规范地方的摊筹派募行为。40年代,地方的摊筹派募现象异常严重,政府对此十分清楚。1943年四川省民政厅调查表明:“全省各县不同的摊派名称,一共是301种……大家都感觉地方的摊筹派募太多,于是谤怨烦兴,乡镇公所成为怨府。”“地方人士是主张消灭摊派,财政当局是主张禁止摊派的。”[8](107-108页)但由于战争以及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费甚巨,正赋收入有限,“自中央以至乡镇,大家都觉得财政困难,于是一层推一层,推到乡镇,便推无可推,只好一切出于摊派,摊派的门一开,有几个不是见钱眼黑,于是不应该派的也摊派,应该少摊派的,无妨多摊派几次”。鉴于以上情况,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民意机构来规范地方的摊筹派募行为。例如《县各级组织纲要》第四十一条第五款[9](7页),以及根据此条款所制定的“各县乡镇征收临时收入办法”[8](111页),乡镇民代表大会享有对临时经费征收的审核权和决议征收数额、征收标准之权利。
其次,借助民意机构的参与来使征丁工作公平些。政府征丁办法为:按丁口多寡进行抽签,被抽中者,如不出丁,则出钱请人代丁。政府即欲发挥民意机构的监督功能,使抽签公平些。
再次,利用民意机构来监督基层行政人员的行为。当时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赋税征收中的贪污中饱行为,即“民贫国穷而富贪官”,“川民负担虽重,罗掘几尽,而政府收入仍属寥寥……一年三征之结果,全年省税,仅19000余万,其中隐匿侵蚀,为数定多”[10]。针对以上情况,一些有识之士要求“有效发挥并提高民意机关职权以协助及监督政府”,政府对此深表认同[11]。
政府对民意机构确曾寄予厚望。不过,由于在民意机构的产生方式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结果事与愿违。
二 以绅意和官意代替民意
国民政府所要建立的民意机构实际上是在各级行政机构的监控下,由所谓的“公正士绅”组成的机构。
40年代初,针对“目下各县情况,但见恶势力之治而不见自治,甚且也不见官治”的情况,国民政府认为“如何使能打倒恶势力之治,势非设立民意机关扶植正人君子,共图自治不可”[12]。这表明政府建立民意机构是为了扶助地方“公正士绅”(正人君子),达到以“正绅治”来辅助官治的目的。一方面,因为他们认为士绅在基层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士绅者,民众之耳目喉舌也,士绅之所是,一邑是之,士绅之所非,一邑非之,且政令之推行,及地方兴革事宜,有赖于士绅协助赞襄倡导举办者甚多”[13];另一方面,因为他们认为一般民众觉悟程度低,难以发挥直接民主。基层社区民众舆论往往以议论、闲谈、埋怨等形式存在,具有相当的散漫性、无实效性。民众对县乡事务及法令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布告、报纸、文告、乡务会议所传递的信息往往仅限于士绅及行政人员,因而能够发表意见的往往只是士绅等少数人[14]。因此,以公正士绅来代表民意,不偏不倚地反映包括一般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打击劣绅,从而调动民众的积极性,稳固自身统治,当是政府建立民意机构的初衷。
由于人数众多的一般民众不可能直接参与到民意机构之中,以公正人士作为代表,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只在于作为代表的士绅是否公正,是否能够维护占人口大多数的一般劳动民众的利益。按常理讲,这样的人只有通过民众的公正选举才可能产生,但当时却并未通过民众公正选举。以四川省训练团第九期考训学员从彭县、长寿、华阳、巴县、隆昌等18个县中所抽取出的45个乡镇的情况来看,作为初级民意机构的保民大会,其举办时间先后不齐且距离民众直接选举较远,民众对其缺乏热情。如资中人民不参加保民大会;乐山云华乡之一保,应到36人,实到1人;彭县丽春乡第四保,实到男子53人,妇女38人,小孩20余人,其中3/5以上不识字,十之七八不合公民资格,十之六七确是户长[15](32页)。乡镇民代表的产生方式各异,除巴县、阆中由保民大会票选外,彭县由保长指定,兼由指导员提出人名,以举手方式表决;南充由保民大会选出人数呈报县府圈定;资中由甲长填选举票,以代替保民大会[15](144页);巴县、长寿两县,“其代表之产生多系豪绅推荐,或直接由乡镇保长提出”[15](147页)。作为县正式参议会过度机构的县临时参议会完全通过从上到下的推举方式产生,省县政府及党部在推举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也代表不了民意。“临参会时代之参议员,概不通过民间,系由政府遴选,出于从上而下,不能代表真正民意,徒具民主的形式”[16](104页)。
笔者并不认为,不是民众选举产生的就一定不是“公正士绅”,也不认为是民众选举的,上任以后,就一直是公正士绅。实际上,当时民意机构普遍存在着“贤者不为,为者不贤”的情况,“然公正士绅,每多不愿问事,其喜揽公事者,常以土劣居多,贪官污吏,与此辈沆瀣一气,办事反觉顺手”[13]。不直接参与地方政务的士绅,平时高谈阔论,品评时政,易博“贤者”美名,然一旦参与地方事务,或迫于生计,或为亲朋谋利,或为有势者胁迫,或为有财者收买,作上级派下的扰民之事,难免会变为“不贤”。
一般来讲,不通过民众的公正选举而欲产生能代表民众利益的所谓“公正士绅”,不通过民众的有效监督而欲使士绅保持长久公正,不免太富于幻想色彩。况且,国民政府实际上并未把维护一般民众的利益作为“民意机构”的首要职能,他们更多地把“民意机构”作为协助政府办理地方行政事务的工具。
按照四川省《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三年计划大纲》,由下到上的民意机构的建立必须在由上到下的行政组织指导下完成。从其实际承担的任务看,也往往是行政先于多于自治。
笔者先以巴县各级民意机构的会议记录及所提议案来进行考察。1942年9月5日《巴县土桥乡第一保录呈保民大会记录》及1942年8月23日《巴县人和镇第二十八保保民大会记录》具有一定代表性。这两次会议的提案多为如何办理上级机构委办事务,维持保的社会秩序,确保保甲机构之运行等,如“遵守时间案”、“保甲人员服装案”、“本保治安如何维持案”[17]、“应如何组设盘查哨案”、“训练国民兵案”、“户口异动应如期呈报案”、“县治民工伙食应从速收清呈缴案”[18],为本保民众争取利益的提案甚少,而且提案倡导者皆为保甲长及士绅。1942年10月23日《四川省巴县马王乡乡民代表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则绝大部分是筹募经费的议案。如“提议田赋征实乡镇民代表应负督催监视以杜流弊而早结束案”、“设立卫生所所需经费药品用具筹募案”、“乡公所职员待遇菲薄拟就地筹款津贴以维生活案”、“为代166师征购稻草烧柴及借用豆料如何分派偿还案”、“1942年积谷可否征募案”[19]。乡镇民代表会成了行政机构筹募经费的工具。
基层会议重行政轻自治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从四川省训练团第九期考训学员所调查的45个乡镇的会议统计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为行政会议,并无自治意义可言。1942年1-9月的会议决议案共478件,摊派杂款就占139件,而垦荒、测量土地、修路、救灾等自治事务才各占两案[15](38-40页)。
应该看到,基层各级民意机构协助完成相应的行政事务,也属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关键在于基层的自治工作应该占据重要位置,民意机构也应该更多地提出维护地方民众利益的提案,并监督其实施。然而40年代四川省在基层所建立的“民意机构”却并无自治意义可言。正如四川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沈鹏所言:“实施地方自治是当前县府及乡镇公所之唯一主要任务,但事实上今日县、乡镇公所无暇可办自治工作,全部时间为行政工作(即上级委办事项)占去,征兵、征工、征粮、募债,均是他们之‘重头戏’,整日整夜终无演尽之时。”[20]对此,他认为“固然战时动员工作重要,但建国之基础工作‘自治’也应予重视”[20]。其实在《县各级组织纲要》中,对于国家事务与自治事务早已作了明确的划分。只不过在实施的过程中,两者“仍属混而不分”,充其量“不过成为官督民办之一种进步的官治,而非真正的民治”[21](80页)。
主要由士绅组成的“民意机构”成了协助办理行政事务的工具,反映出官和绅之间众多利益的一致性,但两者之间除了互相利用外,还暗斗摩擦。比如,“乡镇民代表与乡镇长合作者,则全变为乡镇公所负责派款机关,如长寿是。对乡镇公所认真稽核者,又形成对立局势,如巴县是。而互相利用与暗斗摩擦,实为目前一般现象”[15](147页)。作为“民意机构”的县临时参议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是既有合作又有冲突,“遂宁各机关对临参会认为绅权太大,徒讨麻烦,有碍政令推行”[15](121页)。巴县临参会不能与政府密切配合,“在议会方面,即是扯、揉、看三字,在政府方面,即是推、拖、骗三字”[16](10页)。
政府希望“民意机构”在协助政府完成各项行政事务的同时,也能够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这曾一度激起一些地区的民众对地方自治的热情,巴县等少数地区就曾经出现过“民众热心,礼仪隆重”[22]、“参加踊跃”[23]等情形。但是,大多数地区的一般民众对这种“民意机构”缺乏认识,取漠视态度,“参加选举代表,也任人操纵也”[15](147页)。对于县临时参议会,一般民众更是缺乏了解。如,“乐山牛华溪人民称临参会为盐商会,遂宁县人民误认临参会为财委会,甚有知识稍差之保甲人员,也对临参会漠然不知”,“大多数民众,均漠不关心”[15](11页)。这正是以官意和绅意来代替民意的必然结果。
三 “民意机构”的作用
(一)“民意机构”在选举基层行政及自治人员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县制实行以后,一些地区开始了“民选”的实践,到1943年底“民选”的乡镇干部及职员已经占有一定比例,这是以往推行地方自治未能做到的。不过,完全通过“民选”产生的基层行政及自治人员的比例较小。现以四川省训练团第九期考训学员对18个县45个乡镇调查的情况为例。
表一 乡镇长的来源情况
背景及来路
人数
百分比
乡民选者
5 11%
县委派者13 29%
联保主任改充者
2 4%
士绅哥老推荐者及其他25 56%
(资料来源: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3-65/3号,第9页。)
表二 副乡镇长来源情况
背景及来路
人数 百分比
民选者
3 7%
县委派者20 46%
乡镇长保委者11 26%
士绅哥老推荐由县府任用
9 21%
(资料来源: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3-65/3号,第12页。)
表三 民政股主任来源情况
背景及来路
人数 百分比
乡镇长保委者 21 72%
县府委任者
5 17%
民选者
2 7%
哥老保委者
1 4%
(资料来源: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3-65/3号,第16页。)
表四 警卫股主任来源情况
背景及来路
人数 百分比
乡镇长保委者26 79%
县委任者 4 12%
国民兵团保委者
1 3%
哥老介绍与乡长保委
2 6%
(资料来源: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3-65/3号,第18页。)
以上四表反映出“民选”基层行政及自治人员所占比例较小,甚至普遍不如哥老会的推荐人数,而且就连一般助理干事和事务员也是如此,其“民选”与“哥老保荐者”之比例为1:2[15](32页)。哥老会盛行,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方势力,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发言权有时超过一般民众。
实际上,所谓的“民选”并不是真正的民众直接选举,而是由保民大会、乡镇民代表会、县临时参议会、县参议会等所谓的“民意机构”来间接选举产生。“民意机构”在选举基层行政及自治人员中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不具有决定性,而主要行政人员的意志才具有压倒多数的权威。加上,民意机构自身的产生多为上级官员及地方士绅所支配,民意程度十分有限,即使地方行政及自治人员全通过这种“民意机构”选举产生,也不能确保其能充分代表民意。
(二)“民意机构”在解决摊筹派募、征丁以及吏治腐败等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
抗战期间,一般民众异常贫困,在政治上,他们往往并不奢望当家作主,但却十分希望政府能减轻他们的负担,改善他们的生活。“民意机构”的建立,在一些宣传较好的示范县,如巴县等,最初也使民众看到了一丝希望,因而也曾一度激起他们的一点热情。从当时基层所报的开会情形来看,除福寿乡的户长会议“秩序欠佳”外,其余皆为“参加颇觉奋发,议案周到”。巴县各乡镇民代表会的筹备经过及开会情形,“仪式庄严,有条不紊”,“参加踊跃”,“民众热心,礼仪隆重”等。1943年巴县地方自治工作竞赛,“比上年成绩优异”[24]。尽管基层的报告多少具有一定的浮夸成分,但民众对可能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抱有一定的热情,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种热情能否持续下去,则全依赖于他们是否实际得到了利益。
“民意机构”能够了解民间的一些疾苦,甚至向政府提出一些维护民众利益的建议。如1941年12月,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县政考察团第十四组报告书列出了许多典型议案,如“请绝对废止乡镇保甲长筹款案”。该案指出:1.不宜使派款收款占据(乡镇保甲长)大部分之精力时间;2.乡镇保甲长经手此等事务易作威作福并难免有挪移侵占等贪污之弊;3.人民见乡镇保甲长时时向彼等要钱,对之自易起轻视畏厌之心,乡镇保甲长推行其他公务时也暗受其影响;4.贤良自好之士无不视派款收款为畏途,于是保甲镇长遂成贤者不为,为者不贤之普遍现象,使行政下层机构无法健全。此外,还有救灾、救济公教人员生活、补助行政及教育经费、减征壮丁、增加壮丁食粮、改善壮丁待遇、落实优待壮丁家属等议案,它们大多是要求减轻负担的。其中有议案明确主张将组训民众与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25](第六章,1-5页)。可见,民意机构中也确实不乏有正义感、有见识的公正人士。
“民意机构”提出的建议也曾一度引起行政机构的高度重视,他们也相应发布了一些行政命令,力图解决出现的问题,不过却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办法。县乡保甲在实施大政方针时还出现了扭曲行为,尤其是贪污中饱严重。“上峰收入一千而保甲索取于民者何止二、三千”[25](第六章,1-5页)。政府设置“民意机构”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所谓的“公正士绅”来减少或杜绝中饱行为,然而士绅及其他有产者与一般民众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在要求政府减轻赋税方面,他们与一般民众的利益基本一致。但在政府由于战争及维护自身统治不可能减少赋税征收的情况下,作为“民意机构”主持者的士绅及其他有产者往往失去了公正,对于基层行政自治人员转嫁负担的行为不但视而不见,还彼此勾结,从中渔利。四川省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第四十一条第五款赋予乡镇民代表会对临时经费征收的审核权、决议征收数额、征收标准等权利,结果却成为基层行政自治人员从中渔利的工具。“法定以外的捐税,即各种临时的摊筹派募,名目既多,负担又重,不但大家觉得有些苛求,尤其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摊,都可以筹”[8](16页)。再以征丁为例。因为缺乏真正民意机构的监督,造成极不公平的现象。“一则使保甲籍丁苛索人民,一则使豪势富户向保甲活动,纯至抽中者,多属独子单丁,尽出贫而无告之家,而有人力金钱之户,毫未抽中,此抽签法令,本属至公,保甲办理,极为不平”;“被抽之户,不见得平,随保甲之好恶,而估拉者有之,用金钱之运动而买充者有之,更有一般乡豪土棍,钱力两有,而不买充,而不应征者有之”[26]。
不可否定,民意机构中也并非没有“公正人士”,民意机构所通过的议案也不乏能维护一般民众利益的,但一旦同豪绅的利益发生冲突,则难以施行,“镇公所依仗土豪势力,对代表大会决议案,也视如具文”[15](147页)。
由于占人口多数的一般民众不能左右“民意机构”和执事当局的意志,因而一般民众的正当要求难以得到满足。新县制实施了四年,连国民党人士都称:“各级党政民机关,虽每次会议皆议□□□为完善之地方自治案,但执行人员大都视为老生常谈,而未尝加之意焉。”[27]“相沿已久的贪污舞弊,未见敛迹”,呈现“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为者不贤,贤者不为”的情况[8]。1946年7月,国民参政会9名参议员指出:“吏治腐败,政风荡然,政府虽具改革决心,但官僚政治积重难返。近来由于物价波动,生活不安以及接收敌伪产业人员乘机舞弊,风气之坏,更有甚于前清末年。各地行政人员或遇事敷衍或彼此推诿或浮报虚吞或逢迎欢逐,拉拢接纳惟恐不及,人民疾苦则毫不过问,甚至贿赂公行,穷奢极欲,恬不以为耻者,民生用是凋敝,政教因此凌夷。”[11]
吏治腐败的原因众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民意机构的选举、监督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不可否认,新县制颁行后,部分乡民也能控告基层行政及自治人员在选举和任职中出现的腐败行为。1945年3月,巴县永兴乡公民代表童雨樵、田可勤等控诉新当选的乡长萧炳辉吸食鸦片,请求巴县政府“从速究办,并另派要员,监选贤能”[28];1947年2月,巴县仁厚乡乡民代表会主席汪武烈控告该乡乡长赵治仁“侵蚀殊多”,请求县府“撤职另委”[29];1947年10月,县民陆玉廷等控告璧山县长刘宗华贪污舞弊;1948年6月,县民钟国材等控告江津县长朱镜清贪污不法;1947年12月,在乡军官控告綦江县长胡大斌贪污不法等等[30]。1947年1-3月,巴县人民控告乡镇自治人员贪污者有23案,经查属实,移交法院惩治者有4案,记过处分者有8案,查不实者有11件[3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县制下民意有所发挥,但同时也证明了新县制下地方官吏的贪污不法行为未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民众选择控告方式本身就说明民意机构发挥的作用有限。民众多向县以上行政部门控诉,很少向民意机构检举,表明他们对民意机构的权威持怀疑态度。新县制下民意机构在选举、监督基层行政人员中所实际发挥的作用也与民众的怀疑相吻合。有的乡镇在选举乡长时,由县派指导员监选,选举人由保长、中心学校校长以及保长邀请的士绅等构成,形成“由下级行政人员选举上级行政人员”的状况,“殊乏民选意义”[32]。即使是所谓民选的乡长,在其上任后的所作所为与其上任前的诸多承诺也往往大相径庭,民意机构也不能有效约束。以巴县永盛乡乡长封禹昌为例,他在选任之初,大肆鼓吹“实干苦干,经济公开,每月一次报销以昭公允”[33],但细查该乡长之作风,却恰其反,“迄今年之任,不但未见报销一次,而清算也无举行,并操纵一乡全权,什么乡财政保管委员会,虽有设置,毫无实际……该乡长乘机大张恶势,肆无忌惮,任意刮尽民脂民膏”[33]。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收稿日期:2001-0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