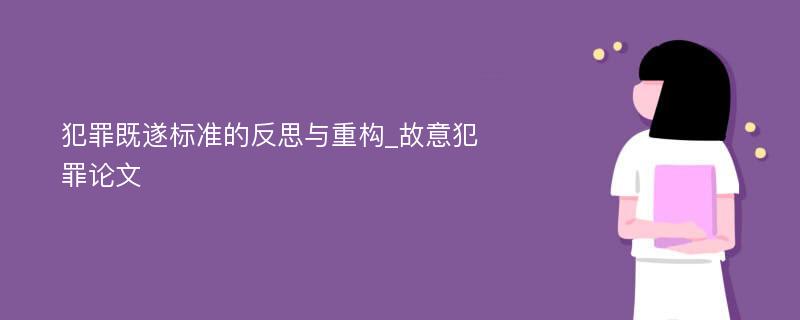
对犯罪既遂标准的反思与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2)01-0033-07
我国刑法理论界通常将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分为预备犯、未遂犯、既遂犯和中止犯四类。既遂犯作为其中犯罪形态最为完整的一个,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而既遂犯的认定标准,更是既遂犯的基础问题。这一标准也的确在我国刑法学界产生过长期的争论。
纵观各种教材和论著,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和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是犯罪既遂认定标准中经常被提到的观点。其中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无疑占据了通说的地位。[1-3]犯罪目的实现说主张认定犯罪既遂与否应当以犯罪人的犯罪目的是否达成为标准。批评者认为尽管此观点可以在一些犯罪中正确地认定犯罪既遂,但却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故意犯罪中。无法正确解决所有故意犯罪类型的既遂问题,是这一观点存在的最主要的缺陷。犯罪结果发生说主张认定犯罪既遂的依据应看犯罪结果是否发生。这里的犯罪结果一般认为是“法律规定的危害结果”。批评者常常以有形的危害结果不足以正确认定所有故意犯罪的既遂来指正此说的缺陷。通说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才是能够解决所有故意犯罪认定标准的“科学理论”,其理由大致如下:第一,它以齐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不仅使犯罪构成理论与犯罪既遂问题得到了有机的结合,而且也为研究完成形态的犯罪,找到了正确的基点”[4]494;第二,它避免了犯罪目的实现说和犯罪结果发生说不能适用于所有故意犯罪的缺陷,为犯罪既遂提供了一个统一简便的标准。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虽然在理论界成为通说,“我国高等院校的刑法学教材,几乎是千篇一律地采用了第三种观点”[5]65,但是近年来通说也受到了一些质疑,这些质疑由于本身立论存在缺陷,或者只是对通说的小修小补,很难动摇通说的地位。
一、对通说的质疑
综合起来,学者们对于犯罪既遂通说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犯罪构成要件齐备是罪与非罪的标准,而非故意犯罪既遂与否的标准
我国刑法理论界认为只有行为完全符合了四个要件才能构成犯罪,而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以齐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认定犯罪既遂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把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当成了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5]68,这样就只有犯罪既遂构成犯罪,否定了犯罪未完成形态成立犯罪。这一方面是学者们对通说批评最为集中的地方。
(二)犯罪构成不能用于指导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
犯罪既遂符合齐备的犯罪构成要件,而未遂、中止和预备形态符合各自不齐备犯罪的构成要件,构成要件不同,罪名自然不同,所以一个犯罪行为如果在不同的阶段停止,可能构成不同的罪名——这显然是很荒谬的。而且,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以构成要件为依据区分既遂与未完成形态,同时构成要件又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因此犯罪构成理论就发挥了两种功能:区分是否成罪和处于何种犯罪形态。而实践中构成要件理论从来就没有同时发挥这两种功能。[6]同时,还会导致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双重评价[7]。
(三)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的理论前提不存在
通说的理论前提是我国刑法分则对各个罪的规定都是既遂模式,而事实上并非刑法分则规定所有的犯罪都是既遂。对于过失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而言,一般认为是不存在既遂的,而且即使直接故意犯罪也并非都是既遂模式,例如刑法第92条规定的颠覆政府罪实际上只是犯罪预备,而刑法第105、107、108、109条规定的犯罪实际上只是犯罪未遂[5]66。
(四)与“既遂”的词义不服
按照《辞海》的解释,“遂”字的意思是“如意”、“如愿”,“既”的意思是“已经”,“既遂”就是“已经如愿”的意思,是与人的主观意愿分不开的。而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完全脱离了人的主观目的,只是以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为标准,好像行为人实施犯罪就是为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因而是不科学的[5]67。
(五)危险犯既遂后行为人主动排除危险状态的行为无法得到合理解决
刑法理论认为危险犯只要危险状态出现,犯罪就已经既遂,而故意犯罪停止形态一旦确定就不能继续或者倒流,所以危险犯既遂后即使自动排除了危险状态没有造成实害结果,仍然只能是犯罪既遂,对于行为人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利于鼓励犯罪人主动中止犯罪[8]68。
二、对通说的圆融
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虽然受到了上述质疑,但实质上并未受到根本动摇,相反,通过对这些质疑的回应,却可以使通说更加准确。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是以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谓的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都是犯罪既遂的模式为基础的,而犯罪的未遂、中止和预备形态要比照既遂犯才能认定。其理论基础就是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是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蓝本加以增删之后的结果。实际上,“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既遂犯的成立条件,而非犯罪的构成要件”[9]。所以,作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的理论基础,其所谓的“犯罪构成”并非犯罪论中的“犯罪构成”,二者并非同一概念。因为很少有学者认识到二者所表现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所以批评者对犯罪构成要件说会有上述的质疑一和因此而引出的质疑二,根源在于这些学者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实际上,虽然二者都叫“犯罪构成”,所具有的内涵并不相同。包含四个要件的“犯罪构成”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而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中的“犯罪构成”,是在符合四要件的犯罪构成基础之上,构成犯罪之后影响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各犯罪构成要素的总称。换言之,只有在行为构成犯罪(故意犯罪)之后才有可能讨论它的停止形态,二者是一个前后衔接的过程,并不是在同一层次上来讲的。后一个犯罪构成明显超出了前一个犯罪构成所包含的四个要件,还包含着更多的元素。以故意杀人罪为例,本罪的既遂就不仅包含着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还包含着“将人杀死”这一结果性构成要素。因此,批评者所谓的通说混淆了犯罪成立与犯罪停止形态的关系就是没有道理的。只要正确区分上述两个“犯罪构成”的内涵和所处的层次,这些批评就不攻自破了。
对于一些学者针对通说所谓的分则条文规定的都是犯罪既遂模式的理论前提不正确,因为过失犯和间接故意犯罪只有成立与否而没有既遂与未遂的区别,的确如此,但这并没有动摇基本犯罪构成理论的根基,只是把既遂模式限定在了直接故意犯罪的范围之内,实际上使得基本的犯罪构成理论更为准确。而对于学者们所谓的刑法分则有些条文规定的只是犯罪的预备形态或者未遂形态,其实刑法设定犯罪既遂的标准,体现了统治者的刑法价值观念,“立法者出于对现行统治关系及统治秩序的保护需要,而在立法过程中对自然事实意义的结果进行取舍来设计犯罪行为的完成形态……刑法规定的犯罪从自然的角度观察也未必都是完整的行为过程……立法者可以为了达到立法目的对客观过程进行取舍”[10],从自然行为的角度来看也许只是处于预备或者未遂形态,但是刑法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免受一旦造成就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实质损害,特意将犯罪的既遂标准提前实现。否则这些犯罪根本就不能出现既遂的形态,那刑法总则部分关于预备犯和未遂犯的处罚原则“比照既遂犯”又从何比照呢?
有学者从既遂的表面词义入手,认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应当是犯罪目的实现说。作为一种解释方法,这样的理由当然可以成立。但是法学研究毕竟不同于语言分析,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可行应当看其是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适用于所有的情况,而不是看它起了一个怎样的名称。法学理论中也有和通常的理解上不同的概念,比如法律渊源,渊源按照通常的理解是指来源或者源头,而法律渊源却是指法律的表现形式。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法学概念,不必拘泥于其原本的涵义如何。
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在解决危险犯既遂与中止的问题上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基本的分歧在于所处立场的不同,通说站在国家和社会的立场,认定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具有极大的潜在法益侵害性,一旦造成实害,后果就不可估量。批评者站在行为人的立场上,认为行为人已经放弃了犯行,且积极主动防止了危害后果的发生,实质上相当于中止了犯罪,这完全符合犯罪中止的特征,危险犯的犯罪既遂就应当是实害结果的发生而不是危险状态的出现。由于二者所处立场的区别,这样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不过,如果将实害发生前自动排除危险状态认定为犯罪中止,那有什么理由不将行为犯的实害结果出现前的自动终止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中止呢?这样一来,所有的犯罪就都是结果犯了,从而得出犯罪既遂的标准就应当是犯罪结果发生说。但从实践上来看,事实却并非如此。
三、对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的再思考
按照上面对通说的圆融,好像通说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不过需要一些小的补正就可以回应对其的质疑,但事实上通说还存在一些问题。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基本的构成要件理论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直接故意犯罪都是既遂模式,因而基本的犯罪构成就是既遂犯的成立条件,而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所指的又是齐备了基本的构成要件就是犯罪既遂。因此通说在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首先预先假定了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是既遂模式,又反过来说齐备了基本的构成要件就是既遂的标准,那基本构成要件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是既遂模式而已。这无异于说“各种犯罪的既遂模式就是它们的既遂标准”[8]69,就好比我们假设A是B的成立标准,然后又说B的成立标准是A一样,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说。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基本的犯罪构成理论到底有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确定、统一的标准呢?这将直接关系到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的确定性和统一性。
基本的犯罪构成是建立在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构成要件是最为完整的,并且在进行一定的修改和减少以后还能够以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构成犯罪基础之上的。“修正的犯罪构成是在刑法总则中,以通则的形式规定的,因而在确定这一类行为的犯罪构成时,要以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规定的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结合总则中关于该修正的犯罪构成综合加以认定。也就是说,修正的犯罪构成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没有离开具体犯罪而抽象存在的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4]93,那么,基本的犯罪构成就是抽象的吗?“基本的犯罪构成由刑法分则条文所直接规定,”[4]499而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每一个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并非指包含四要件的犯罪构成)又都含有自己的独特内容,如果说基本的犯罪构成包含了每一个犯罪的内容,那其包含的内容将会相当庞杂。如果把齐备这个意义上的基本犯罪构成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那么刑法上的每一个罪都只能符合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即该罪法条规定的部分,因而只能处于未完成形态,也就是说所有的犯罪都不能既遂。如果基本的犯罪构成包含的只是每个罪共同具有的内容,那基本的构成要件就只是和包含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相同的一个概念,从而未完成形态就不构成犯罪。所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不能是抽象的,而应和修正的犯罪构成一样也只能是具体的,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只能从某一个犯罪的角度把握,没有离开具体犯罪的基本的犯罪构成。
如果基本的犯罪构成只能从具体犯罪的角度把握,那么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也只能依据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个罪的规定一一认定其既遂的标准,换言之,每一个犯罪都有自己的标准,这怎么能说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呢?退一步讲,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的规定是否指明了既遂的标准呢?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如果说将人杀死是故意杀人罪众所周知的既遂标准,那第237条规定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的既遂标准又是什么呢?到底是猥亵或者侮辱行为开始就已经既遂,还是行为人觉得猥亵或者侮辱已经满足了内心的变态欲望才既遂呢?还有盗窃罪的失控说、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等不同的既遂标准,以及强奸罪既遂的不同标准的学说……从刑法条文里我们无法得出确定的观点,也就是说分则条文并没有确切指明每一个罪的既遂标准。
与此相对应的,通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犯罪既遂的类型中又分别介绍了结果犯的既遂、危险犯的既遂、行为犯的既遂,认为结果犯的既遂是法定犯罪结果的出现,行为犯的既遂是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危险犯的既遂是法定危害状态的出现①。正如有学者所说的“由于犯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法律条文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不可能千篇一律,从而也就决定了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犯罪,在认定其犯罪既遂的标准上必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在具体案件的认定上,我们应该在一个总的标准之下,按照具体犯罪的不同既遂形态类型加以确定。由于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的齐备上差异很大,因此不能作简单划一的判断”[11]。这实际上暴露了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既遂标准的不彻底性,归根到底还是要在对各种犯罪分类的基础之上寻找其各自的既遂标准,也就是说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只不过是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各自既遂标准之上设定的一个称谓而已。
综合以上的内容,应当说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并不能作为一个判断犯罪是否既遂的标准,因为它归根到底把齐备基本的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落脚在了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上,而刑法分则条文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这样的归结只能把这一犯罪既遂的标准引入只具有括号意义的概念中去。
四、犯罪既遂标准的重新构建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犯罪既遂的存在范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犯罪的停止形态不仅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还存在于间接故意犯罪之中[12];有的学者主张犯罪的停止形态只出现于直接故意犯罪中[13]。对于主张犯罪的停止形态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的学者而言,对于举动犯存不存在犯罪既遂与未遂也存在着争议。否定者认为举动犯一经着手实施即告犯罪行为完成,就只能存在预备阶段和着手,而不可能有未遂存在的可能性,从而否定举动犯的未遂,同时又认为未遂与既遂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未遂也就无所谓既遂,所以举动犯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而不存在既遂与未遂的问题。而支持者认为举动犯既遂与未遂的区分主要在于实行犯罪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足以抑制其犯罪意思的意外因素,并且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为例,认为行为人以外语煽动造成煽动的对象根本就不知道行为人的意思的,应当属于一种手段不能犯而构成犯罪的未遂。[4]426从而以此来认定举动犯也存在着既遂。
在这里,应当说未完成形态不应存在于间接故意犯罪之中,因为其在主观上只是放任,不存在特定的犯罪目的,不可能对于犯罪既遂有积极追求的态度和行动,对犯罪既遂与否都并不关心,犯罪没有实现的时候也并不违背其本意,在这种意义上说犯罪实现与否对行为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用既遂与未遂来衡量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没有质的区别的观点,实质上就否定了对二者进行分类的意义。应当说在间接故意犯罪中区分是既遂还是未遂的努力没有意义的。
对于举动犯是否存在未遂的问题上,以肯定说的观点所举的例子来讲,如果没有人理解煽动分裂国家罪的行为人煽动的内容,那又有谁去追究行为人的罪行呢?如果行为人的罪行得以追究,那行为人的煽动内容必定已经为人所知,那又如何说他的犯罪是未遂呢?行为人在实行犯罪过程中由于意外的因素抑制其犯罪意思的,如果着手之前抑制,那就不会有着手行为,如果着手之后抑制,那就是既遂之后的问题了。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着手过程中的抑制呢?应当说着手的过程必定很短,其中不可能有抑制犯罪意思因素存在的可能性,否则举动犯就不成其为举动犯,而应当叫做程度犯(有些论著中也叫做行为犯)。而犯罪既遂总是相对于未遂来讲的,没有未遂也就无所谓既遂,所以对于举动犯来讲没有认定既遂标准的必要性。同样,对于抽象的危险犯来说,行为已经着手就假定危险状态出现,与举动犯类似,应当认为它也不存在犯罪的既遂与未遂。
按照传统对犯罪的分类,可以将犯罪分为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三类。其中行为犯可以分为举动犯和程度犯,危险犯可以分为抽象的危险犯和具体的危险犯。如上所述,举动犯和抽象的危险犯无所谓既遂与未遂,因此可以将其排除出既遂标准的范围,只在程度犯、具体的危险犯和结果犯的范围中探讨既遂的标准。
有学者从犯罪构成体系的三个层次出发,认为犯罪既遂的标准应当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14]或者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充分[15],该学说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角度出发,对通说进行了修正,认为在已经符合了犯罪构成要件前提下,犯罪既遂齐备的是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通过分析犯罪是否具备了全部的基本构成要件要素来确定犯罪既遂与否。这与本文在第二部分区分两个“犯罪构成”时的观点具有一致性。无疑,这种观点深入到更加具体的构成要素层面,与通说相比更加确切。但是,能否以此为犯罪既遂的标准呢?
其实,依据传统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理论,犯罪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犯罪构成的第一个层次是犯罪构成的系统本身,处于整个构成系统的顶端,是最高层次的范畴。第二个层次是犯罪构成系统的两大组成部分,即犯罪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第三个层次是犯罪构成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下的四个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第四个层次是犯罪构成要件内部各个要件所包含的各个构成要素。在构成要素的层面,每一个具体的犯罪都可以用集合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A罪={犯罪的直接客体,犯罪的对象,犯罪行为,犯罪结果,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因果联系,犯罪的时间地点等,犯罪主体行为的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犯罪的动机和目的……}具备了具体刑法条文所规定的全部的构成要素,犯罪就达到了既遂。如果只是符合了第三层次的四大犯罪构成要件,即只具备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四大要件,但是在第四层次的犯罪构成要素上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或者修正,那么其犯罪的形态就只能是未完成形态。②
这个观点在形式上可以绕开结果犯、危险犯和行为犯的分类而直接衡量具体的每一个犯罪是否既遂,作为对构成要件齐备说的发展,的确可以解决通说的很多问题。但是这一理论却预先假定了危险犯的犯罪构成要素包含了危险状态而不包括实害结果,行为犯的犯罪构成要素仅仅只有行为而不包含实害结果,否则在衡量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时就都可以构成犯罪既遂,只不过一个构成要件要素里包含了实害结果而另一个没有,这样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等就有两个既遂了。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没能摆脱犯罪构成要件说所具有的缺陷——先预先设定了各类犯罪的既遂的标准,再以这个标准为基础进行结构上的分析。在实质上仍然没能绕过结果犯、危险犯和行为犯的三分。而且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侧重于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要素。犯罪故意产生在前,行为实施于后,从客观方面认定既遂的标准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这实际上忽视了犯罪的既遂和中止形态在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区别。对于行为实施终了的犯罪中止,固然要求排除了犯罪结果的发生,但是主观方面也必须要求出于本人意志停止犯罪,自动和彻底放弃原来的犯罪意图,这两方面都是犯罪中止区别于既遂的主要特征。对于犯罪中止来讲,其主观方面的要求相当于截断了犯罪故意的持续状态。而且,这一理论也不能清楚地表明何时犯罪达到既遂,并不能给出一个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志。
按照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的既遂是最完整的形态,而未完成形态是对既遂形态的修改与缩短,所以既遂相对于未遂总是会多出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的出现就意味着犯罪已经既遂,所以应当把这部分的内容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的重要考量因素。
前苏联刑法学家特拉伊宁首先用构成要件理论研究犯罪停止形态的结构,他把预备、未遂、既遂等犯罪停止形态用公式表达了出来:“预备行为=故意+不是(犯罪)构成因素的行为”、“未遂行为=故意+是构成因素的行为-结果”、“既遂行为=故意+是构成因素的行为+结果”[4]428,显然特拉伊宁所持的是犯罪结果发生说。虽然这种学说具有一定的缺陷,但是这种研究既遂结构的模式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可以从既遂与未完成形态的区别入手,即通过研究处在相对于未完成形态延长线上的既遂部分内容确定犯罪既遂的标准。
作为一个标准,应当说犯罪既遂的标准一定是涵盖了未完成形态的内容,如果既遂=A+B+C+D+E,那么应该说未完成形态=A+B+C+ D或者未完成形态=A+B+C+D+e,其中,要素“e”应当是对“E”的修正。在这一等式中,我们可以发现要素“E”的出现是我们认定犯罪既遂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承认基本和修正的犯罪构成的前提下,犯罪既遂无疑比未完成形态多了一些内容,处在相对于未完成形态延长线上的既遂部分,这部分内容用上面提到的构成要件要素来表示也未为不可,加上未完成形态所包含的构成要件要素就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即构成要件要素齐备或者充足,在确定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犯罪的四大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只要这部分内容在犯罪过程中出现就可以直接认定犯罪已经既遂——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志。这是在基本和修正的犯罪构成的前提下得出的必然结论。那这部分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犯罪构成包含了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主体四个要件,显而易见,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的内容不必考虑,上面也已经讲到,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在区分犯罪的既遂和未完成形态上起着作用,所以处在相对于未完成形态延长线上的既遂部分应当含有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先从主观方面来看,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故意内容包括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认识因素包含了“明知”和“会”,这是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都具有的内容,行为人一旦具有了认识因素就不可能中断或者撤销,而意志因素则不同,它具体表现为犯罪目的,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可以将其终止和撤销。所以在主观上,相对于犯罪中止而言,犯罪既遂是犯罪目的一直处于持续的状态,犯罪中止则是将犯罪目的放弃了或者终结了犯罪目的的持续状态。
再看客观方面,刑法明文规定犯罪中止只要处于“犯罪过程中”即可,许多刑法论著中认为只要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即可,无疑这是以结果犯为标本来讲的,而未遂犯也有实行终了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之分,从这些论著中所举的例子来看,也应该是以结果犯为标本的,且不论这些表述是否恰当,这至少可以说明犯罪既遂处在未完成形态延长线上的部分,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点,而非一个线段,在这个点之后犯罪就处于同样的状态而不必再进行评价,也就是说犯罪既遂的标志就是某种状态的出现。而结合犯罪主观方面的犯罪目的,可以把它称为是彰显犯罪目的的状态。与犯罪目的实现说不同的是,这种状态并非要求犯罪目的必须实现,只要行为实施到彰显犯罪目的,让一般人清楚行为人所意欲达到的犯罪目的的状态即表明犯罪已经既遂,如果按照一般情势发展的逻辑,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就一定会实现。如果这种状态出现之后还能够继续,那么所造成的更严重的危害结果就应当认为是结果加重犯。
比如盗窃罪,行为人入室盗窃在没有取财物前,外人在外观上可能无法分辨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什么,可能是意图盗窃,也可能是意图伤害或者杀人,还可能只是单纯的侵入住宅,当行为人将财物盗走,使财物处于所有人的控制之外时,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即已经完全彰显,所以可以认定犯罪既遂。再如破坏交通工具罪,行为人破坏了公交车的刹车系统,此时貌似已经彰显了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但是如果不能产生具体的危险,比如这辆车虽然停在公交公司院内,但实际上已经报废,就只能是不能犯而不能使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彰显出来,因而,要出现具体的危险状态——彰显犯罪目的,才能认定犯罪已经既遂。但是在一些情形中,比如故意杀人罪,行为人虽然已经着手实施了杀人行为,但是在没有将人杀死前,无法在外部让人了解行为人所意欲的是否是将人杀死的犯罪目的,比如行为人的也可能呈现出故意伤害的表象,所以直到将人杀死才能将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彰显出来,因而要求现实结果的出现才能确定犯罪既遂。
通过彰显犯罪目的状态这一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志,我们可以解决通说或者犯罪构成要素齐备说不能解决的缺陷——预设各类犯罪的既遂的标准,而且也可以明白地表现出犯罪既遂的界点。比如对于刑法所规定的第114条和第115条的关系上,只要达到第114条的规定的状态,犯罪目的即已彰显出来,而无需借助第115条的内容认定犯罪既遂,所以可以将其作为结果加重犯来看待,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个罪有两个既遂标准的问题。应当说,彰显犯罪目的的状态这一标准在理论上是基于已经构成犯罪的基础上展开的,它单纯是为了确定犯罪是否既遂而得出的一个标准,在理论上也是以修正的犯罪构成和基本的犯罪构成的区别为基础的。在实务中,面对查清的犯罪事实,在认定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之后,反过来再看行为人的犯罪停止的时候已经将这个犯罪目的彰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说已经完全将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彰显了出来,也就是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目的时所参考的其他情节和证据其实只起到了佐证作用,行为人犯罪行为停止时所表明的犯罪目的已经非常明显,比如小偷入室盗窃完毕后提着财物从家里刚出来就被事主给抓住了——那么就是既遂。如果行为人着手之后的犯罪停止时并没有彰显出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司法机关对行为人的犯罪目的认定时参考的其他情节和证据起到了证明犯罪目的是什么作用,那么,就应该是未遂,比如行为人意图杀人却没有将人杀死,在行为人被迫停止犯罪时我们可能无法从表象上认定他到底是要杀人还是要意图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但是,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对于犯罪目的是否双重评价的问题。在判定故意犯罪成立的意义上,要先考虑犯罪目的,在是否存在犯罪既遂的问题上再次将犯罪目的作为一个考量的对象,的确是对犯罪目的进行了又一次的考量,但是这两次考量不是在一个角度上进行的,而是有所侧重。在前一个层次——构成犯罪上,对犯罪目的的考量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来说的,即直接故意犯罪构成犯罪必须要有犯罪目的,在其他构成要件符合的情况下,只要再加上犯罪目的就构成犯罪,解决的是故意内容中的犯罪目的存不存在和是什么的问题。而后一个彰显犯罪目的状态意义上的犯罪目的,是考虑犯罪行为停止时所表现出的形态已经将犯罪目的彰显到了什么程度,这其实是在程度的大小上来讲的。因此,两次的评价只是对犯罪目的不同层面的考量,并非是双重评价,正如对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刑法可以对其科以刑罚,被害人也可以要求其民事损害赔偿,对同一行为进行两次评价,考虑的层面也不同。
五、结语
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我国犯罪既遂的标准,现在仍然处于统治地位,在理论和事务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但是由于这一理论在逻辑上具有先天缺陷.而且不能清晰地表明犯罪既遂的界点,因此,应当对其进行发展。犯罪构成要素齐备说将既遂的标准认定为构成要素的齐备,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仍没有合理解决全部的问题,所以应当借助于彰显犯罪目的的状态这一犯罪既遂的标志,对是否达到犯罪既遂加以明晰。鉴于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目前“一统天下”的局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注释:
①现行的教材多数会有犯罪既遂的类型或者表现形式部分,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②关于犯罪构成集合论的论述,具体参见李永升:《犯罪构成集合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李永升:《刑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148-198页。
标签:故意犯罪论文; 犯罪既遂论文; 犯罪构成要件论文; 结果犯论文; 行为犯论文; 犯罪主观方面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构成要件要素论文; 法律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故意杀人未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