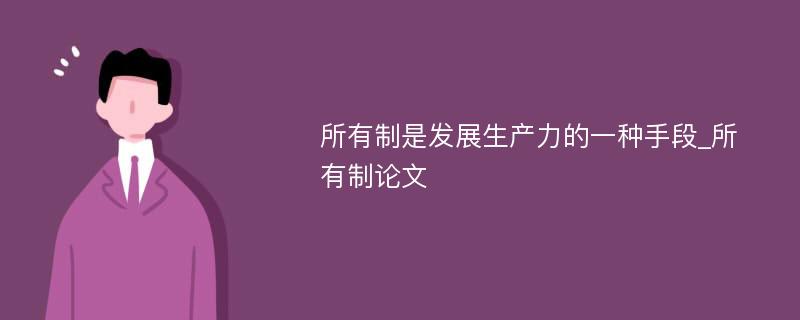
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手段论文,发展生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发展生产力来说是不是手段?有些人说是,有些人说不是。我认为是。本文想结合某些观点,发表几点意见。
我国正在不断深入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包括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自然包括改革过去那种单纯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在这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目的,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就是手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即伟大目的,而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是达到这一宏伟目的的手段;同时,“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又是目的,而进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的改革又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改革是一场革命,革命自然有革命的目的和革命的手段。
把所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基础,而人类生产总是社会性的,不是个人孤立进行的,人类正是为了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才结成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关系。所以,在原始社会,人类建立原始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分配关系,就是为了进行有效的生产,以满足原始人的生活需要。后来,由于原始公有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便又被当时的人们所抛弃,建立起新的所有制——私有制。以后,私有制的形式也有几次更替,都是由于原来的私有制形式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满足先进阶级和多数人的需要,而被人们不断抛弃,代之以能解放和推动生产力的新的私有制形式。所有制这样改来改去,都是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个目的进行的,所有制从来就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
有一种意见说,不对。如果认为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必然的逻辑就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共同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同的统治阶级有不同的利益和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并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有的论者还作出进一步推论:认为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共同目的,就是“美化剥削制度”。持这样看法的人,是想证明所有制不是所有社会形态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但这是证明不了的。
就以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资本家是把获得利润当作自己经营的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获取利润的目的,不仅仅要建立资本家所有制,而且还要依靠这种所有制来组织和发展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因为归根到底,剩余价值才是利润的源泉,而剩余价值是在生产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发展生产力是资产阶级获取利润的必要环节。把资本家所有制、发展生产力和获取利润三个环节联系起来就可看出:资本家所有制对发展生产力来说是手段,发展生产力对资本家获取利润来说又是手段。在这三者关系中,发展生产力具有目的和手段的二重性。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只是具体内容不同罢了。所以,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所有制对发展生产力来说总是手段,而发展生产力总是所有制所服从的一个目的,虽然发展生产力不是最终目的。这是客观事实,并不是“美化”什么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觉地建立某种所有制,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这个目的,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全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目的。但在这里,对所有制来说,发展生产力是目的,所有制则是发展生产力的直接手段,也是满足人民需要的间接手段。
有一种意见说,在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并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同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对立起来了。
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可以从多角度进行的,只要研究得当,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一定是互补一致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就可以从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进行研究,也可以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互补的。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上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可以直接揭示生产方式中人的主体性。目的和手段是标示人的活动的一对范畴,人类正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区分出目的和手段的。利用生产工具向自然界作斗争,获得生活资料,这里有目的和手段的区分;为了向自然界作斗争,人们需要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这里同样也有目的和手段的区分。说生产关系是手段,发展生产力是目的,就是从这里找到根源的。而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上进行研究,则是为了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运动趋势,这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是必要的。但仅仅从这个层次上研究,就会以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似乎同自然界的运动一样,是没有人参加的纯客观运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虽然有人的因素,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上进行研究时,并不着眼于人的主体性,而是着眼于客观性、规律性。如果把上述两个角度联系起来去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可以既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又揭示其客观性,岂不更好。具体地说,当某种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要从发展生产力这个目的出发,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社会中的先进势力正是从这个基本立场上对待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反之,如果错误地把生产关系当作目的,而把生产力当作手段,当发现生产力的发展正威胁着旧的生产关系时,就会去阻止或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以达到巩固旧生产关系的目的。历史上的落后势力正是这样做的,这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变更将损害它们的既得利益。所以,明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到底何者是目的何者是手段是必要的。
但明确发展生产力是目的,建立生产关系是手段,也离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因为要证明某种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好手段或不好手段,就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为指导,对这种所有制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进行具体论证。所以,把以上两个角度的研究对立起来,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是不行的。
还有一种意见是:市场、计划是经济手段,这是成立的,但所有制是比市场、计划更高层次的东西,不能当作手段。这也是难以成立的。如同目的有高低层次一样,手段也有高低层次之分。不论层次高低,只要是用于达到某种目的的东西都是手段。战略比策略高,路线比具体方针、政策高,但战略、路线对于某种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来说,都是手段。所有制比之市场、计划是属于高层次,高层次的东西如果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更大,更要积极改革;但也正因为是高层次的东西,或破或立也更要有充分根据,否则,将造成更大损失,如同路线错了,所造成的损失比某项具体政策错了所造成的损失更大一样。但层次的高低不能证明所有制不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
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生产关系是客观的物质关系,还是任人随意选择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把生产关系当作手段,就是主张人们可以任意选择生产关系。这就涉及到人们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不是可以任意选择某种生产关系作为手段的问题。
生产关系当然不能任意选择。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中,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的,只有从现实生产力的状况出发,才能确定建立何种性质和形式的生产关系。如果纯粹从主观愿望出发,任意建立某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并不能保证是发展生产力的好手段。“大跃进”时期由于主观地搞“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当时的人们就是把建立公有制当作目的,曾造成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就是明证。
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来说,假如目的被证明是合理的(正确的),也只有能够真正达到目的的手段才是可用的,不能达到该目的的手段则是不能用的。而且在社会活动中还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也限制着手段选择的范围,并非可以任意选择手段。恩格斯说:“我把道德问题丢在一边——这里不是谈这一点,所以我也就把它撇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2页)
不过,虽然达到合理目的的手段是不能任意选择的,但确实有一个认真选择的问题。把“所有制有一个选择的问题”笼统地加以批评是不妥的。因为为了达到合理的目的,往往有多种可用的手段可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最能迅速有效地达到目的的手段,往往是主体优先选用的对象。就发展生产力这个目的来说,虽然从总的原则来看,有什么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便决定着应该采用什么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关系,但实际生活是十分复杂的,究竟采取何种生产关系并不容易确定。因为,第一,在一定历史时期,同一种生产力可以容纳不同水平的生产关系,并且都能推动生产力发展。这是由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并不是机械的决定作用,而是有一定的弹性幅度的,只有从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看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最终决定作用。第二,从我国情况来说,各地区、各行业的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相差很大,究竟在某个地区、某个行业采取何种生产关系为适当,也有一个从本地区、本行业的实际出发进行具体选择的问题,并且不容易选择得当。第三,选择是一个认识过程,选择是否正确,并不取决于选择者对选择的主观承诺或宣扬,而是要经过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只有当实践的结果确实证明了某种生产关系能迅速推动生产力发展,也为人所公认时,才能说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否则,则是不正确的。选择就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由“试错”达到正确的过程。聪明人并不在于在选择中不犯错误,而在于当实践证明自己所选择的某种生产关系不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时,能主动进行反省,总结经验,再行选择,而不抱住既定的生产关系不放。建国以来,我国在生产关系的性质、水平和全国生产关系的结构上进行过多次选择,有选择得对的,也有选择得不对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曾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过社会生产。今天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包括纠正过去在选择中所犯的错误,再进行一次认真的选择,以便使我们的认识尽早地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相一致,使手段与目的相统一。
值得深思的是,有些论者反对在所有制上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可能并非真的反对一切选择,而是由于改革中在所有制上进行的某些选择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实际上主张继续坚持过去那种已经被证明是不恰当的选择。
有的论者还有这样一个观点,主张所有制是手段,就是主张私有化。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逻辑。一个人仅仅说所有制是手段,发展生产力是目的,是无法断定他是主张哪一种所有制的,因为所有制包括公有制、私有制和公私混合制等多种,并非说只有私有制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最好手段。所以,仅仅从“所有制是手段”这样一个孤立的命题,是推不出“主张私有化”的结论来的。
坚持所有制对发展生产力来说是手段,对今后继续深入进行体制改革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恐资病”。有的论者认为主张所有制是手段就是主张私有化,也许就是由于感到现在私有制搞得太多了,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并且针对这个“要害”问题,提出了判断的标准,即众所周知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邓小平的话真是一语破的。在讨论所有制是不是手段的时候,运用邓小平的上述分析和判断标准,就会很容易弄清是非。
进一步说,不仅仅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一切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体制都是为实现我国现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的手段,也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判断这些体制好坏的标准(是不是好手段的标准),仍然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如果实践证明某一体制不能达到“三个有利于”的目的,就不是好体制,就要坚持改革,直到能够达到“三个有利于”的目的为止。这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
一切经济、政治、教育等等的体制,都是人建立的,都是人用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人才是这一切手段或工具的主人。当某种手段已经被证明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抛弃它,另找新的。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是经常这样做的,他们从不把自己制造的手段神秘化,变成自己顶礼膜拜的偶像。当然,人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和忽视现实条件去任意地建立或改变体制,但在认识规律和条件的基础上,就应当主动地去考察体制的利弊,大胆地去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揭掉蒙在体制上的神秘外衣,暴露其为人的手段性或工具性,人才能从体制的奴仆变成体制的主人,才能在改革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了人民的利益,改变一切过时的旧体制,建立能达到“三个有利于”目的的新体制,使我们的改革不断夺取新胜利。
标签:所有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