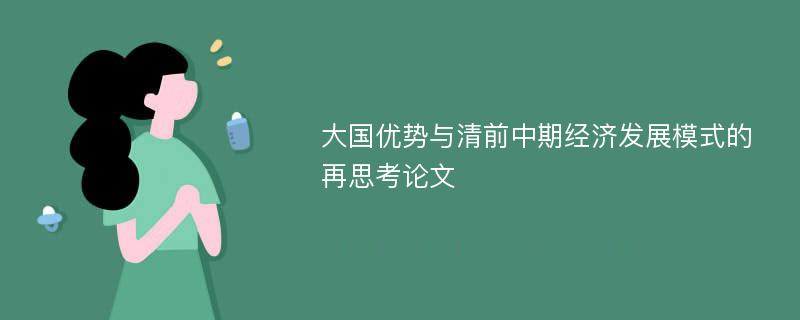
大国优势与清前中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文/徐毅
20世纪30至8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就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展开了三次大讨论,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清史学者着重从清代前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雇佣劳动的变化等方面展示清代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局限,认为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一样,17~19世纪的清代经济正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突出表现为清代经济中已经孕育出了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萌芽。此后,吴承明、许檀等学者在反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突出清代经济中市场需求与专业化生产互动的特点,认为清代处于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为此,王国斌、李伯重等加州学派的学者提出清代经济发展属于由市场规模扩大、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斯密型增长。资本主义萌芽论、斯密型增长论等诸多研究理清了清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成就和趋势,有力地反驳了“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论。当然,要全面揭示出清代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固有特征与长期影响,还需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近年来,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开始从国家规模的角度来探讨清代经济发展有别于欧洲小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问题。珀金斯(Dwight H.Perkins)、麦迪森(Angus Maddison)和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其著作中都认为18至19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总量、人口总量还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能力上都远超经济正在迅速崛起的欧洲,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以此为切入点,从清代经济发展的大国优势条件、独特的发展模式及其这种模式的局限等角度来作更为深入的梳理。
清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国优势条件
与欧洲小国相比,清代中国具有经济发展的三个优势条件,分别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数量众多的人口和庞大市场规模。
日本西铁城早在1956年4月就推出了一款名为Parashock的防震器(见图9),它与一般防震器不同之处在于取消了防震器基座,以一个螺旋状的弹簧片与钻眼固定住,上方则是与托钻固定在一起的弹簧片,所以两个宝石都有与弹簧片固定,明显与Incabloc防震器、Kif防震器有所不同。西铁城为此还在日本国内举办手表高空抛下的试验,在30米高空的直升机上,将手表朝铺有软垫的地面扔下,而搭载这款防震器的手表机心仍可以正常运作。
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清代统治下的国土面积增加了近2倍,已达到1200万平方公里,这是任何一个欧洲小国所无法比拟的。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清前中期中国所拥有的水土、林木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都十分丰富。据史志宏的最新研究,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全国的耕地面积从7亿亩增加到13亿亩,而且耕地扩张地区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地区,至19世纪中叶中西部地区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已到达2/3强。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很惊人,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中国人口从1亿增加到4亿,增长速度是同期欧洲的2倍多。
依托于大国的资源规模、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清代经济发展拥有了大国优势条件。在前工业化时代,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初始禀赋和基本条件;市场规模则是优化前两种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激发经济活力的主要条件。由于三种优势条件的结合方式不同,清前中期各个区域形成了三种具体的生产型式。
清代前中期特有的“规模优势型经济发展模式”
尽管由于清初以来的海禁和一口通商政策导致清朝国际贸易规模不大,但是其国内贸易的规模却很庞大。正如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形容的,“(清朝)中国幅员这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客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根据我们的研究,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全国的贸易总量增长了3倍,而同时期经济发达的英国和荷兰仅分别增长3%和2%。值得注意的是,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由一个包括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个层级,且运作自如的全国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所支撑的。因此,比同时期的欧洲、日本、东南亚国家,价格机制在18世纪的中国国内市场中具有更强的调节作用和整合力,其统一的国内市场已初具规模。
2.抓好关键人,不放松对党员领导干部党章意识的提升。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要在培养干部、选拔干部、教育干部、使用干部上注重考察党章意识,围绕党章对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考察是否坚定理想信念、工作是否实事求是、联系群众是否密切、能力素质是否合格、党的纪律是否遵守。只有抓好关键人的党章学习,才能为广大企业党员学习党章树立榜样,起到示范引领效应。
第二种发展型式在国家或商人的投资下很容易变成第三种发展型式,即“规模型的专业化生产”,它的生产组织即为过去学界认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有一定数量雇佣劳动力的手工业工场或农场”。大多数规模型的专业化生产分布于流通枢纽城市和中等商业城镇,仅有少数分布于承担大规模商品集散功能的农村集市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随着永佃租的盛行,出现“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的现象,土地所有权、租佃权、转租权、经营权的分离,无论广度和深度远超明代。一些租佃农户雇工规模性经营榨油、榨糖业,成为第三种生产经营型式中的一个亮点,甚至产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
广泛存在于各个区域的是一种自然资源、人口资源与农村集市结合的粗放型生产,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组织,以发展自给性很强的小规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内容,与小农经济联系紧密的农村集市仅仅扮演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提供必要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功能,并不具有大规模商品集散地的功能,我们可以称这种粗放型发展型式为“小农粗放型生产”,其最大的成就是支撑着清前期大量耕地的持续开垦与人口的持续增长。
耐用品部门与非耐用品部门名义工资调整的依据在于效用,即:当且仅当调整名义工资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用时,耐用品部门与非耐用品部门就业者才支持工资调整。与Gal1’ 和Monacelli[19]相似,决定耐用品部门与非耐用品部门最优工资的一阶条件为:
砖子说,十巴掌脸就肿了,我还怎么出门?我还怎么上班?要不四巴掌怎么样?砖子心中无奈地叹息,赵仙童这样实验下去,非把我实验到奈何桥不可。
在各个区域交通便利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受到省区内贸易和全国性长距离贸易的激励,部分小农或工匠依托当地的要素禀赋优势形成了以家庭农场或家庭作坊为主要生产组织的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专业化生产。这种称之为“家庭型的专业化生产”主要出现于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承担大规模商品集散功能的农村集市等附近。
后两种生产型式推动了一批专业化生产市镇的形成,如生产丝织品的苏州盛泽镇、生产瓷器的景德镇、生产铁器的佛山和印刷书籍的四堡,等等。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专业化生产的区域分工新格局:东部地区依靠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主要从事棉布、丝绸、瓷器、纸张、书籍和其他制成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的平原和盆地吸引着东部地区的移民从事粮食、棉花、糖、茶、烟草和其他经济作物原料种植与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的丘陵和山地则吸引着东部地区的移民从事药材种植、木竹加工、矿产开发和其他山货加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西部的草原则从事牲畜养殖和皮毛加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更重要的是,少数大宗商品的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如棉布的生产,受到清初政府的政策鼓励,各省棉织业全面展开,至19世纪初已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的江苏、浙江、直隶、山东、福建和湖北等省;丝织业也出现了同样的集聚趋势,嘉庆之前的丝织业广泛分布于大约11个省,至道光年间已集聚到江苏、广东、山东和贵州等省。
总之,上述三种生产型式与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交通便利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相匹配,其核心都是依托于清代中国丰富的资源规模和人口规模和多层次的大国市场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它们共同构成了清代中国特有的“规模优势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大成就体现于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提高,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年增长率为0.44%,占世界GDP总量的20%上升到30%。
清代前中期“规模优势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
清代前期规模优势型模式的发展局限也是相当明显的。由于清前期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率,所以当时人均GDP指标一直在下降。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中国人均GDP总量下降了37%;至19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的人均GDP是清代中国的4倍。尽管如此,18世纪的中国仍是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同时期北京、苏州和广州等大城市非技术工人的生活水平仍与南欧、中欧国家相当。具体来说,清前期的规模优势型发展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各地区的小农粗放型生产向后两种专业化生产的转型相当缓慢,迟滞其转型的最大障碍还是来自于市场规模的限制。清前中期,由于各地分散的农村集市向省区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开放度有限,导致向中等商业城镇和流通枢纽城市输送和接受的商品只有数量的增加,而品种则较少增加,且主要局限在少数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如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铁、铜、瓷器和染料等。其中,粮食、棉布和食盐就占了上述大宗商品交易量的80%左右;况且长距离贸易在清前期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始终没有超过1/3。也就是说,全国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还未能充分发挥清代中国所具有的市场规模优势,这正是大量小农处于维持基本生存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之下,而迟迟未能向专业化生产转型的主要原因。
第二,清前期出现的两种专业化生产——家庭型和规模型的专业化生产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也存在着极限,即斯密型增长论者所说的资本与技术的局限。清前期的专业化生产的构成属于一种“超轻结构”,即生产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生产来自纺织业(棉布生产属于家庭型专业化生产,丝绸生产属于规模型专业化生产),机械装备制造和矿冶业的比重则微不足道。而缺乏资本与技术突破正是“超轻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超轻结构”下,各地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有限,从而也就无法发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的潜在优势。可见,在市场体系、资本和技术等种种制约下,清前中期已经形成的规模优势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能够将清代中国所具有的三种大国优势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助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摘自《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标签:大国优势论文; 专业化生产论文; 优势型论文; 农村集市论文; 流通枢纽城市论文; 清前中期论文; 经济发展模式论文; 市场化水平论文; 集散功能论文; 中等商业城镇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