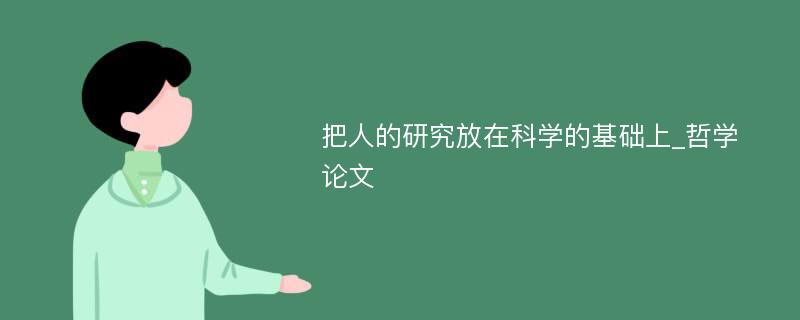
把人的研究置于科学基础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上论文,把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首先是并永远是自然存在物,永远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它的自然本质并不因为人类结成怎样的社会关系而改变,这正如松树生长在其群落、黑猩猩生活于其群体(社会),其植物或动物的自然本质不会改变一样。故人在研究人自身时,应用自己既有的科学知识对待之,即运用自己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来研究人的自然本质,运用自己学到的社会科学知识来研究人的社会本质,并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作综合研究。提倡把人的研究置于科学基础上,其侧重点是强调人学要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因为没有自然科学基础,仅从“哲学”来研究的人学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人学,充其量只是一种人类社会学。本文只是从方法角度来谈四个问题:把人的科学包括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的意义上理解人的社会性;多从自然科学了解人自身;论人与作人相统一。
一、把人的科学包括于自然科学
150多年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把人的科学包括于自然科学,他在述及工业的历史和通过工业形成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以及人的本质力量时写道: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129页)马克思从自然史角度追溯了人的产生。他指出地球构造说致命打击了大地创造说,自然发生说(生命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人的性结合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因而人的肉体存在也要归功于人。当然,整个所谓世界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同前,第130-131页)马克思以自己特有的敏锐关注自然科学并以极大的喜悦来欢迎它,他指出:自然科学已“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同前,第128页)把人的科学包括于自然科学这一说法,隐含了马克思思考人类问题的两个思想支点:一是把人类史包括于自然史,二是从人在实践中获得的其它动物无与伦比的改造世界的智能(自然科学和工业)来揭示人的“本质力量”。然而,人学理论家对后一点似乎关注过多,对前一点则关注太少,因而在迄今为止的人学论著中很少有反映从自然史、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人的成果。自20世纪上叶以来生命科学、人体科学、脑科学、精神科学、基因工程、医学、性科学、遗传学、社会生物学、生态学以及环境科学已获得长足的进步,人学家似未予以热切关注,人学理论仍在一些既成的概念中绕圈子,这难道不是憾事吗?不从自然史出发研究人类史,不把人的科学包括于自然科学,在现实上已不仅仅是一个能否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人学观、把研究引向深入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人能否与其环境协调一致、关涉到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因为人类空前发展的工业和自然科学已使人类自身难已驾驭,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过度开采已使它近乎枯竭,人类那似乎无所不能的力量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已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另一方面,人体科学的新进展也会引发许多新观念产生,如“克隆”人果真诞生,它必将改变人类的性伦理关系;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及网络社会的建立,会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且不说人脑——精神研究,人类睡眠——觉醒机制研究,人的本能和潜力研究这些难题令科学家煞费苦心了,因为它们所具有的难度并不亚于宇宙和海洋科学领域的问题。可见,哲学家自身多一些科学素养,把人学包括于自然科学,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年马克思就尖锐批评哲学疏远自然科学的可悲现象,他说:“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象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同前,第128页)马克思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哲学疏远自然科学的现象进行批评,因为他本人是结合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的典范,他的著作尤其是经济学著作隐含了一部科学技术史。马克思如果不懂数学和自然科学,他就难于完成《资本论》,也不可能成为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可以说,科学应用于一门学科的程度表明该学科成熟的程度。人学果能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有从自然科学出发思考问题的著作出现,那就表明人学这门学问基本上成熟了。从自然史、从终极意义上说,任一人都是自然的,任一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的,都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把人学包括于自然科学,把人类社会看成是自然的生成,不为人道而毁坏天道,既是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遵循,也是对中国古代贤哲那道法自然训示的恪守。
二、在自然的意义上理解人的社会性
马克思早年在批判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时,曾从物种角度提出了“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概念,并从人的类特性出发说明了人同其他动物的区别,他认为:“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的这种生命活动同动物与自身直接同一的生命活动不同,它是有意识的。人在通过实践改造无机界时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基于人这个物种的类特性,马克思否定异化劳动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把自由活动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成为动物的东西。(同前,第96-97页)在批判黑格尔时,马克思提出了自然主义概念,认为“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他强调“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有着能动和受动的二重性;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同前,第167页)可以说,从种的类特性来理解人是马克思的基本唯物主义立场。虽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批判费尔巴哈由于撇开历史进程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的不足,而注重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把握人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关系是这样解释的:他先考察一切人类生存的三大前提或因素即生活、需要和繁殖,指出生产满足吃喝住穿等第一需要的活动“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第一个需要满足后又会引起新的需要;而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繁殖)则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进而说: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同前,第79-80页)可见,马克思仍是在自然的基础上来讨论社会关系的,故他在往后的著作中有诸如此类的提法:“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人“天生是社会动物”。(《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3页)当马克思收回穿越人类社会之外的目光回顾人类社会自身、盯住人这种社会动物时,他高明地把握住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这一根本联系,根据人类曾使用过的生产工具及其生产方式来划分经济的社会形态,认为人类历史大体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时代(马克思也研究了氏族社会)。而在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人己具体成为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资本家和工人,等等,这些人之间既合作、更斗争。马克思从混沌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规律,这同样归功于他的自然科学素养和他把人类史纳入自然史的明智。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宣称:社会本身的运动有其“自然规律”和“自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同前,第11-12页)
三、更多地了解人的生物属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商品的交换价值时曾有过这么一个比喻:“在某种意义上,人很象商品。……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同前,第67页)马克思在这里又提到了“人这个物种”,他的比喻对于理解人亦富具启示。人之所以象商品,在于每一肉体的生命个体只有在与其同类的交往中印证自己的存在。这就象商品的二重性:商品是用来交换、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体现着商品的社会交换关系。同样,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有肉体人身、属于灵长类动物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群和社会中。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探讨人的生物属性方面曾作出过出色的成绩,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手稿中,综合和运用了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来说明人的祖先怎样从猿过渡到人:浑身长毛、成群地生活在树上的类人猿因环境的变迁而下地生活,学会以直立姿势行走而迈出了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手脚的分工使手变得自由而成为劳动的器官并不断完善。依据生长相关律,人手的灵巧和脚的发育又影响人的机体其他部分的发育。人共同协作的需要也改造了喉头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器官。而语言和劳动一起推动猿脑逐渐过渡到人脑,随之人的听觉、视觉等器官也同步发育起来。而人从只吃植物过渡到同时也吃肉时,就缩短了消化过程,赢得了更多时间、更多的物质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使消化过程更加缩短和肉食更加丰富。这样人离植物界越远、超出动物界的程度也越高,从而人能作出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不过恩格斯警告:“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85页)恩格斯不仅确定了人的自然性,亦探讨了人的社会性即人这种群居性动物的自然起源,他指出“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能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那里去寻求根源。”(同前,第376页)然而,在包括人体科学、生命科学、生物学、医学及其诸多分支学科在内的自然科*
突飞猛进的今天,却还没有人学家从科学学角度对人作出新的综合研究,这种综合研究也许有点像马克思说的“缺少结合的能力”之故。当然,在人学研究的起步阶段这样企求可能太高了。先争论一下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否应建立人学学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其规律是何种关系,以及对两种生产,主体性,个性,需要,价值,自由,理想,本质,能力,自我意识,自主活动等等,从人的交往关系一侧在哲学层次上作思考有利于渐进至对人的全面研究。不过,在自然科学划时代的进展及社会科学巨大的进步面前,人文科学该与之并驾齐驱地发展了。可否把人学划分为人类个体学和人类社会学两大分支,把主要属人体科学的问题划归到人类个体学、把主要属社会性行为的问题划归到人类社会学中去呢?不研究人的生物学本质,又怎么能最终确定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准则或价值评判标准呢?这就像不研究商品的自然属性即使用价值而要去弄清它的社会属性即价值一样难以办到。在探索人的躯体这个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小宇宙”问题上,国外学者作了基础性工作。1859年,法国著名生理学家贝纳德就提出了生命体有内环境和外环境这两个环境。1932年,美国的坎农(cannon)在《驱体的智慧》一书中进而研究了人体的稳态,他把神经系统看作躯体保持稳态次要的和辅助的工具(所谓“没有脑袋”的生理学),亦探讨了生物稳态与社会稳态的关系。1942年,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Schrodinger,1887-1961)在《什么是生命》一书中开始用热力学和量子力学来解释生命的本质,用密码遗传(染色体)、负熵、量子跃迁等概念来说明生命活动;70年代美国学者不仅写出了诸如生命科学史,亦写出了社会生物学和结合生物学探讨人类本性一类的书。但威尔逊(Wilson,1929-)70年代中下叶写成的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和《论人类的本性》等,我们至今对之似乎并未予以重视。至少,对侵害社会者或潜在侵犯者的基因作修补即能防患未然,这给我们将个体生物因素同社会行为结合起来研究的启示;而基因是物种遗传、自然选择乃至人类文化变异的基本单位的见解,则使我们为鉴定这种见解的真伪而去读一点生物学著作。此外,通过比较动物社会,比较动物间的合作、利他行为或侵略性行为,亦可加深人类社会行为的了解。
四、论人与作人相统一
言行一致、理论联系实际应是我们遵守的准则。论人与作人相统一意在强调作人。作人的意义有二:一是重自然道德,摆正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二是重社会道德,讲究修身养性。长期以来,人并未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人类总自以为是万物之灵,臆想自己在万物中具有绝对特殊的地位,因而傲慢至上,忘却自己也是地球万物中的一员,同样受到生物界和自然界种种规律的制约。具有所谓理性的人至今尚未完全醒悟:作为为自然界的产物,无论具备多么高超的能力,人类也总不能毁灭自然,而极有可能在理性的盲动中破坏自然平衡而毁灭自己。过去,外国学者已注意到“增长的极限”和生态平衡,并随之涌现出了绿色和平运动。现今,中国的生物学家也在痛心疾呼人类既要讲社会道德,又要讲自然道德,从自私的心态中解放出来,免除饕餮的贪婪,学会把野生动植物看成是自己的亲密朋友,因为正是依靠野生动植物的养育才使人类得以生存和繁衍,野生动植物陷入困境时最大的受害者是人类自己。(参见谈家祯《要讲自然道德》,《中华读书报》1997年1月22日)显然,在自然科学家的视野中,人类不管怎样远离动物界,它仍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众多居民之一、众多物种之一。人类所优越于动物的所谓理性在其终极意义上仍近乎盲目,仍与动物的本能差不多。如果人能摆正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学会以谦逊的态度从事生活,前景也许会美好得多。不过,尽管人类在自己的辞典中对动植物的解释多有一些寝皮食肉的文字(例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第2004页对虎的释义:动物名,哺乳纲,猫科——肉可食,骨可做药,皮毛可做褥垫和地毯等;第1442页对牛的释义:哺乳纲,牛科——有乳用、肉用、役用和兼用等种类。)但威尔逊认为人类远算不上凶暴动物,人类杀戮其他哺乳动物根本不是人类性好侵犯,而主要是维持自身生命的手段。人类这种取食与植物吸取阳光、空气、水分,免子吃草一样,是遵循生物界弱肉强食的规则。人类的侵犯性主要在于人类自相残杀,如侵略战争及其他不同等级的犯罪行为。人类把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达到“人”的地位,在于人类有发达的大脑,有其他物种根本不可能具有的智慧和文化。可是,文化能使人类行为趋于完美吗?文化能创造一个“圣贤”的种族吗?为什么人类除了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外,还有以众暴寡、恃强凌弱、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背叛出卖、口是心非、阴谋诡计、贪脏枉法、骄奢淫逸等奇形怪状的行径呢?有这种行为的人类在一些表里如一、忠诚友善的动物*
前难道不感到羞愧吗?人尽管如恩格斯指出的:“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2页)但人既然是文化动物,明了真善美是人生至境,为什么不去努力摒除假恶丑的东西呢?从长远看,鼓励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弘扬真善美的德行,鼓励每一社会个体的创造性,鼓励每一个人与他人和睦相处、发扬利他精神——为人民服务,建立一个合适的社会规范体系并建立适应人的需要的活动场所,是保持人类这个种族在进化过程中不断优化的必由之路。但惯于隐恶扬善的人类会在全社会的监测下持一个统一的伦理标准吗?如果要讲精神文明的话,中国的古贤们应是精神文明的先行者了,因为他们讲求修齐治平。看来,修齐治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致良知,慎独这样一些古训于现今时代仍有重要意义。对于人学理论家来说,率先实践这些训示,把说与作结合起来,引为社会风范,当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