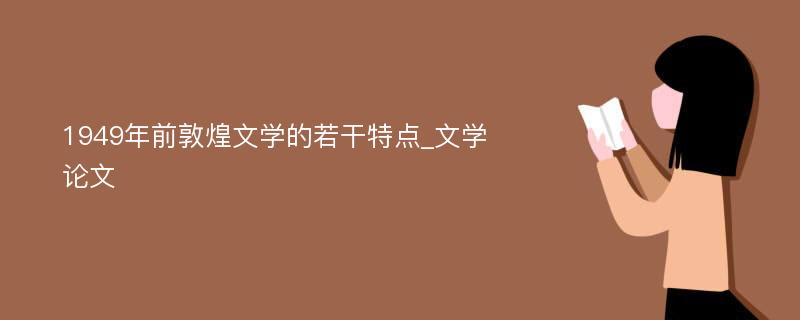
1949年前敦煌文学研究的若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年前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受材料、观念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制约,1949年前的敦煌文学研究带有很强的探索性。不过,尽管不少观点带有局限性,但整个研究是不断向前推进的。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随材料的发现而进展
敦煌藏经洞里的俗文学材料是一千多年前的文学文本,在我国的文献上早已失载,而且面世的过程又非常曲折,东鳞西爪一点一点地被挖掘出来。因此,学术界对这些材料的认识和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这方面,向达颇有感触:“唯以作者之志在于化俗,是以文辞鄙俚意旨浅显。敦煌学者之于此种作品、非意存鄙弃,即不免误解;研究通俗文学者又多逞臆之辞,两者俱未为得也。”(向达《唐代俗讲考》)傅芸子对此体会也很深:“关于敦煌俗文学,前虽有人为文绍介,然因近年新材料之继续的发见,因之亦获得与前不同之新的解释。”(傅芸子《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
由于写本的残缺不全和写本的不易获得,常常导致学者对有关文本产生错觉,只有等到文献充分挖掘出来后,才能有正确的认识。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傅芸子在研究《破魔变文》时就提到这一现象:自胡适收购到结构宏伟、篇幅完整的《降魔变文》后才知道罗叔言氏《敦煌零拾》收藏的一个残卷就是《降魔变文》的一部分。冈崎文夫氏自巴黎抄回的《降魔变押座文》、《破魔变文》共一卷(伯2187),后由青木正儿氏简单介绍于《支那学》中,当时也没引用原文,洎至后来《降魔变文》出现,所以世间对于这两个变文是一是二,多莫名其妙,连亲列巴黎去的郑西谛氏也没有看到此卷,不仅没弄清楚真相,而且还造成了误解;后来傅氏从冈崎文夫处抄得《降魔变押座文》、《破魔变文》,又利用那波利贞抄本加以校补,“才知道《降魔变文》与《破魔变文》并非一个东西。……至于《降魔变押座文》,实应作‘破魔’而非‘降魔’,因此一点,所以使人易于误会了。”(傅芸子《关于破魔变文——敦煌足本之发现》)
关于敦煌讲唱文学的称呼问题,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傅芸子从文献搜集的角度谈到这一问题:“最初介绍此种文体者为罗振玉氏之《敦煌零拾》,内有《佛曲》三种,时尚未知有变文之目,罗氏名为‘佛曲’也。变文之名最早介绍于世者,恐即胡适博士所记之《维摩诘经变文》,而狩野博士抄归之《孝子董永》,今知实亦变文,不过仅存唱词而已。厥后日本冈崎文夫博士又在巴黎抄得《目连缘起》、《大目犍连变文》、《破魔变文》三种,由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两博士为文绍介于《支那学》中,自是变文之名益著。继之者为刘复、小岛祐马、郑振铎、王重民、那波利贞诸君,先后续有抄录,而国立北京图书馆所藏变文,嗣亦整理完毕。”(傅芸子《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郑振铎则从文献研究的角度谈到这一问题:“在前几年,对于变文一类的东西,是往往由编目者或叙述者任意给他以一个名目的。或称之为俗文,或称之为唱文,或称之为佛曲,或称之为演义,其实都不是原名。又或加《明妃变文》以《明妃传》之名,《伍子胥变文》为《伍子胥》或《列国传》,也皆是出于臆度,无当原义。”(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这些称呼中影响最大的是“佛曲”,为学界所沿用。但这一称呼一开始就受到质疑。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是为罗氏《敦煌零拾》而作,他在文章中反对罗氏的界定,建议改称“演义”。
向达一开始也相信这一说法,后来接触到更多的材料,于是撰文加以修正,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论文集《唐代西安与西域文明》的“作者致辞”中,向达作了说明:“开始接触到佛曲这样一个名词,于是追溯列音乐方面,提出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渊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后来逐渐明白佛曲与敦煌所出通俗文学中的变文是两回事,佛曲与龟兹乐有关,而变文一类的通俗文学乃是唐代通行的一种讲唱文学即俗讲文学的话本。1937年在巴黎看到记载俗讲仪式的一个卷子,这一问题算是比较满意地解决了。”在论文《论唐代佛曲》中,作者说得更详细:“后来我把《敦煌零拾》中所收的三篇俗文反覆阅看,毫不见有宫调之迹。我疑心所见敦煌发见的俗文只是一斑,不足以概全体,遂又托人从北京京师图书馆抄得敦煌卷子俗文三篇,此外又在《支那学》第四卷第三号得见青木正儿介绍敦煌发见《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及《降魔变押座文》的一篇文章,知道敦煌发见的俗文变文体制大致相同……自觉所立佛曲是佛曲,俗文变文是俗文变文,二者截然不同的说法,大致可以成立。遂不揣冒昧,写成这一篇东西,一方面钩稽唐代佛曲,考其源流;一方面申论佛曲与俗文变文是两种东西,以证罗氏之失,并自已忏悔以前轻信之过。”
郑振铎对敦煌讲唱文学的界定则随着材料的不断挖掘而经历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他放弃佛曲说和俗文变文说,最后将敦煌讲唱文学界定为“变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敦煌讲唱文学的通称。
一开始,他也依据罗氏的提法写了一篇《佛曲叙录》,后来觉得不妥,于是又写了一篇《佛曲、俗文与变文》加以订正:“因为对于俗文与变文有了一番很浅薄的讨究,便察觉出俗文与佛曲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东西,不能相提并论的。后来的宝卷,乃是俗文或变文的支裔,所以与佛曲亦相差同样的远。”在《敦煌的俗文学》中,他把敦煌讲唱文学分为“变文和俗文”:“‘俗文’不能离了经典而独立,他们是演经的,是释经的;‘变文’则与所叙述的故事的原来来源并不发生任何的关系,他们不过活用相传的故事,以抒写作者自己的情致而已。”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他又指出:“变文的名称,到了最近,因了几种重要的首尾完备‘变文’写本的发现,方才确定……我在商务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编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里,也以为这种韵散结合体的叙事文字,可分为俗文和变文。现在才觉察出其错误来。原来在变文外,这种新文体,实在并无其他名称,正如变相之没有第二种名称一样。”后来,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再一次指出自己把敦煌讲唱文学分为变文和俗文“是错误的。总缘所见太少,便不能没有臆测之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郑振铎广泛阅读所能找到的材料,对学术界关于这个“文体”的种种的臆测的称谓作了辨析,最后指出:“但就今日所发现的文卷来看,以变文为名的,实在是最多。……像变相一样,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之意)。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或简称为变)。”
关于敦煌文学的分类,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更是经历了一个五花八门而又逐渐走向正确的历程。
罗振玉编《敦煌零拾》时,除《秦妇吟》、《云谣集杂曲子》、《季布歌》外,尚有《佛曲三种》、《俚曲三种》、《小曲三种》三类,显示了一定的分类意识。王国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文库》第71种《考古学零简》)介绍敦煌文学时曾使用“似后世七字唱本”、唐人小说、俗体诗文、唐人词、“当时歌唱脚本”等类别概念。
胡适将敦煌遗书分成七类,“丁类”为“俗文学”,包括词、小说、唱文(胡适《海外读书札记》)。
向达在《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中列出有关目录后指出“以上简目,略就性质归类,不依号码次序”,并分变文、唱文或唱经文、白话词文、故事、白话诗、俗赋、通俗书作了简单介绍。这一分类对后来的几篇专科目录都有影响(向达《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
郑振铎在《敦煌的俗文学》中把敦煌俗文学分为三类:1.诗歌(民间杂曲、叙事诗、杂曲子);2.散文的俗文学”(《唐太宗入冥记》、《秋胡》);3.变文与俗文。后来,在《中国俗文学史》又作了调整。在第一章中,他把俗文学分为五大类,即诗歌、小说、戏剧、讲唱文学和游戏文章。他把敦煌变文和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列为讲唱文学的子目,又把《燕子赋》、《茶酒论》当作游戏文章的典范。在第五章中,他把“唐代的民间歌赋”即敦煌歌赋分为王梵志等的通俗诗、民间词、民间小曲、长篇叙事歌和小品赋。在第六章中,又把变文分为“关于佛经的故事”和“非佛经的故事”两类,前者包括“严格的说经的”(含“仅演述经文而不叙写故事”和“叙写佛经的故事”两类)和“离开经文而自由叙状的”两类,后者包括历史传说和当代“今闻”。
后来,傅芸子《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在综述敦煌学学术史的同时,分变文(关于唱经及佛教故事的、关于非佛教故事的)、诗歌(佛曲及民间杂曲)、通俗诗、杂曲子、民间之赋、杂文、小说等类别对敦煌文学作了著录。
以上分类,无论是根据内容的分类还是根据体制的分类,其类目和作品的类别归属在今天看来都有不当乃至错误之处,但总的趋势还是随着材料的不断掌握而走向科学。
随观念的转变而进展
早期的敦煌学研究是以对四部书的整理和研究为中心的,敦煌文学的研究是这种研究的附带品。只有在白话文学、俗文学观念兴起之后,敦煌文学才被研究者从文学史的高度加以肯定,加以研究。
罗振玉、王国维、董康都曾东渡日本,对狩野直喜关于敦煌俗文学价值的论述都有所了解;但他们囿于传统四部书的理念,虽对俗文学作过收集、整理乃至研究,却无法对这些文献的重要性作出科学的解说。如罗振玉的注意力在四部书,所以尽管出版了敦煌俗文学的资料却名之曰《敦煌零拾》;王国维写了第一篇敦煌文学论文,但他还是把敦煌文学文献归入集部:“敦煌千佛洞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其中佛典居百分之九五,其四部书为我国宋以后久佚者:……集部有唐人词曲及通俗诗小说各若干种。”(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胡适为倡导白话文而写《白话文学史》。在这种理论视野下,《白话文学史》不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而且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变革要求,是白话文运动的学术体现。因此,《白话文学史》能够从文学史的高度对敦煌的俗文学作出很高的评价。他在第九章第十章《佛教的翻译文学》中认为:“印度文学(佛经)……的体裁,都是中国没有的;他们的输入,与后代的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指出转读是变文的源头,梵呗是《净土赞》、《太子赞》等歌曲的源头,也是佛教中白话诗歌的源头,唱导是白话散文的源头(胡适《白话文学史》)。此外,他还认为敦煌王梵志的白话诗和小说的发现改写了白话文学史:“六年前的许多假设,有些现在已得着新证据了,有些现在须作大大的改动了。如六年前我说寒山的诗应该是晚唐的产品,但敦煌出现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怀疑了。怀疑便引我去寻新证据,寒山的时代竟因此得着重新考定了。又如我在《国语文学史》初稿里断定唐朝一代的诗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了我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要更早几百年!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却不料隋唐之际已有了白话诗人王梵志了。我在六年前刚见着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说》,还很诧异,却不料唐朝已有不少通俗小说了!六年前的自以为大胆惊人的假设,现在看来,竟是过于胆小,过于持重的见解了。”
向达也在多篇文章中强调敦煌文学的价值。他认为敦煌文献使“谈中国文化史的,凭空添了将近两万卷的材料,不仅许多古籍可借以校订……尤其重要的便是佛教美术同俗文学上的新发现”;敦煌文献“对俗文学的贡献:一是题材方面,第二是活的辞汇的收集”;“今从敦煌所出诸俗讲文学作品观之,宋代说话人宜可溯源于此。纪伍子胥故事,《汉将王陵变》,《季布骂阵词文》,《昭君变》,以及《张淮深变文》之类,即宋代说话人中讲史书一科之先声;而说经说参请,又为唐代诸讲经文之分支与流裔;弹词宝卷,则俗文学之直系子孙也”;鼓子词,诸宫调乃至合生都与之有渊源(分见向达《论唐代佛曲》、《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唐代俗讲考》)。
这种文学观念的改变大大地促进了敦煌俗文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刘半农出版《敦煌掇琐》,及时为敦煌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关键材料。他抄写、出版这部作品跟白话文运动密切相关。他在前言里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书名叫掇琐,因为书中所收,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但这个小字,只是依着向来沿袭的说法说,并不是用了科学方法估定的。”“直到最近数年这种谬误的大小观念才渐渐的改变了。我们只须看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作,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一时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至少总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他还举吴立模研究五更调、顾颉刚研究孟姜女倚重他抄录的文献来说明《敦煌掇琐》的价值(刘半农《敦煌掇琐序》)。《敦煌杂录》的编者也在自序中指出《敦煌杂录》“略就文之性质分为八类(变文、偈赞、音韵、文疏、契约、传记、目录、杂类),以唐代民间通俗之作为多,可以考谣谚之源流,窥俗尚之迁易,欲知千年来社会之演进,及经济之转变者,此是重要之史料也”(《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自序》)。
当时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分别为这两部敦煌俗文学文集作序,对文献的价值和作者的辛勤劳动作了充分肯定。北大校长蔡元培认为:“刘半农先生留法四年,研究语言学的余暇,把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敦煌写本的杂文,都抄出来,分类排比,勒成此集……至于唐代文词……读是编所录一部分的白话文和白话五言诗,我们才见到当时通俗文词的真相。就中如五更转、孟姜女等小唱,尤可以看出今通行的小唱,来源尤古。”(蔡元培《敦煌掇琐序》)胡适认为:“《敦煌杂录》是继蒋斧、罗振玉、罗福保、刘复、羽田亨诸先生的工作,专抄敦煌所藏非佛教经典的文件。……第一类的佛教通俗文学,近年来已得着学者的注意,许君所辑之中,最重要的是几残卷变文,虽不如巴黎所藏《维摩变文》和我所藏《降魔变文》的完整,但我们因此可知道当时变文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所以是很可贵的。这里面的佛曲,如《辞娘赞》……如《归去来》都属于同一体制,使我们明白当时的佛曲是用一种极简单的流行曲调,来编佛教的俗曲。”(胡适《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
胡适的观点对郑振铎影响甚大。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文学观念的变化对敦煌文学研究的推动。
胡适关于敦煌文学的思考由于《白话文学史》有头无尾而没能够展开,郑振铎除了表示惋惜外,还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对胡适的观点作了发挥和拓展。他的这种发挥和拓展是通过三部文学史的撰写而一步步走向深入的。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世卷之《敦煌的俗文学》一章中对敦煌文学作了总的估价:“第一,他使我们知道许多已佚的杰作,如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诗集之类。第二,他将中古文学的一个绝大的秘密对我们公开了。他告诉我们小说、弹词、宝卷以及好些民间小曲的来源。他使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的许多未为人所注意的杰作,其产生的情形和来历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绝大的消息。可以用这个发现而推翻古来无数的传统见解。”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他不仅设《变文的产生》一章论述敦煌文学,而且还在《话本的产生》、《鼓子词与诸宫调》等专章里谈到变文对这些文体的影响。郑振铎关于敦煌文学的思考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他在第一章中强调:“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他甚至指出:“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第八、十一、十二、十三章分别论述鼓子词与诸宫调、宝卷、弹词、鼓子词与子弟书时都把源头追溯到变文,并进行了论证;第五、六两章以专章的形式分论《唐代的民间歌赋》和《变文》。作者在文学史中设专章介绍敦煌文学尤其是变文的原因在于: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样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氏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变文的发现,固然是最重要的消息,使我们对于宋元的通俗文学的发展的讨论上,有了肯定的结论。而同时,许多民间歌曲的被掘出,也使我们得到不少的好作品,同时并明白了后来的许多通俗作品的产生的线索和原因”。
通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敦煌文学乃至俗文学的地位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俗文学地位的确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敦煌俗文学的力量。这可以从傅芸子对敦煌俗文学研究的回顾中看出来:“夫俗文学者,向为吾国士大夫所不耻,谥为鄙陋卑俗,毫无研究价值;乃自敦煌俗文学发见以来,始引起世人之注意。直至五四后,国语文学运动勃兴,俗文学之研究亦随之兴起。至今俗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主要的成分,并且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吾人夷考其故,实皆由于敦煌俗文学之力有以造成之。此种敦煌俗文学可谓‘敦煌学’之一部分,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固亦可谓今日世界学术新潮流之一支流也。”(《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
随着争鸣的展开而走向深入
在敦煌文学的研究进程中,有关的学术观点还在学术争鸣中向前推进。关于变文之“变”的意义、变文的来源和俗讲话本构成的争论就是当时比较激烈的三大论争。
关于变文之“变”的意义的争论是其中最大的一次争论。
如前所述,用变文来指称敦煌的讲唱文学是郑振铎确立的。但他关于变文的定义却经历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他最初将敦煌的讲唱文学分为“俗文”和“变文”,认为“‘变文’则与所叙述的故事的原来来源并不发生如何的关系;他们不过活用相传的故事,以抒写作者自己的情致而已”(《敦煌的俗文学》)。1932年又指出:“‘变文’的意思,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容易明白。……起初,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但很快的便被人们所采取,用来讲唱民间传说的故事。”(《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8年再一次指出:“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之意)。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或简称为变)。”(《中国俗文学史》)
后来,向达发表《唐代俗讲考》,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变文”之“变”的大讨论。现加以综合介绍。周一良认为郑振铎先生的观点“近乎假设。长泽规矩也(《东洋文化大系》“隋唐之盛世”卷)说:变文据说原来是指曼荼罗的铭文;也无根据。向文第五节《俗讲文学起源试探》求变文之渊源于南朝清商旧乐,其说至为新颖”,但没有什么根据。“我觉得变文之变,与变歌之变没有关系。变文者‘变相之文’也。……我觉得这个变字似非中华固有,当是翻译梵语”,“我疑心变字原语,也就是‘citra’(此字有彩绘之意)”(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关德栋认为“变文一词的来源就是与变相图相同,也就是如郑振铎所谓像变相一样,所谓变文之变当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义”;看到周一良的文章后却认为“我以为与其说变字的原语是‘citra’,不如说变字的原语是‘mandala’”;后来又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列举四种说法后指出:“变文的变字就是变相的变字,变相的渊源是‘曼荼罗’,变相的变字就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关德栋《谈“变文”》、《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略说“变”字的来源》)。向达对这些争鸣作了回应:“变或变相一辞的来源,周、关两先生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尚待续考。”(向达《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
此外,傅芸子提出了又一种观点:“所谓变者乃佛的说法神变(佛有三种神变,见《大宝积经》八十六)之义。”“唐五代间,佛教宣传小乘,有二种方式,即变相图与变文,均刺取经典中的神变作题材,一为绘画的,一为文辞的,即以绘画为空间的表现者为变相图,以口语或文辞为时间的展开者为变文是也。”(《关于破魔变文——敦煌写本之发现》)在《俗讲新考》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关于变文的来源的争论。
最先发表意见的是胡适。他认为:“五世纪以下,佛教徒倡行了三种宣传教旨的方法:(1)是经文的转读,(2)是梵呗的歌唱,(3)是唱导的制度。据我的意思,这三种宣传法门便是把佛教文学传到民间去的路子,也便是民间佛教文学的来源。”“转读之法使经文可读,使经文可向大众宣读。这是一大进步。宣读不能叫人懂得,于是有‘俗文’、‘变文’之作,把经文敷演成通俗的唱本,使多数人容易了解。这便是更进一步了。后来唐五代的《维摩变文》等,便是这样起来的。”(《白话文学史》)
郑振铎和胡适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谈到“变文的韵式”时指出:“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来找到。……我们知道,印度的文籍,很早的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讲唱变文的僧侣们,在传播这种新的文体结构上,是最有功绩的。”(《中国俗文学史》)
关德栋也承袭了胡、郑二人的观点。他在分析变文的渊源时谈到“佛教翻译文学的影响”和“六朝时代佛教的唱导文学”,并认为:“我们知道因为支昙龠输入转读之法,使佛教深入民间。其逐渐演进,遂有中晚唐五代变文之作。”(《谈“变文”》)
与胡适稍有不同的是向达。他关于俗讲文学来源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后试图从中国的文艺传统中寻找渊源。1929年,向达认为:“敦煌发见的有韵的俗文学大致可分成纯粹的韵文和韵散相兼的两种。……这两种俗文学大概都受有佛教文学的影响。……至于敦煌俗文学发达的程序,大约先有《维摩诘经唱文》等等带宗教性的东西,然后有《孝子董永》、《季布歌》之类的世俗文学。”1937年,向达认为:“关于敦煌俗文学的真价……说到思想方面,自然受佛教的影响最大,表现得最浓厚……更进一步地去考察,这种俗文学的策源地原来就在寺院。”1944年,向达有了新的看法:“私意以为俗讲文学之来源,当不外乎两途:转读唱导,一也;清商旧乐,二也。”变文、讲经文各有其渊源,讲经文源于转读唱导,变文原为“民间流行说唱体”,其来源“当于南朝清商旧乐中求之”,即“变歌一类”;“唐代俗讲话本,似以讲经文为正宗,而变文之属,则其支裔。换言之,俗讲始兴,只有讲经文一类之话本,浸假而采取民间流行之说唱体如变文之类,以增强其化俗作用。故变文一类作品,盖自有其渊源,与讲经文不同,其体制亦各异也”(分见向达《论唐代佛曲》、《唐代俗讲考》等)。
周一良反对向达的看法,认为:“向文第五节《俗讲文学起源试探》求变文之渊源于南朝清商旧乐,其说至为新颖。但除去乐府里有变歌以及若干以变为名的曲子以外,似乎中国找不出什么连锁来。”(《读唐代俗讲考》)
和郑振铎把敦煌讲唱文学统称为变文不同,向达和孙楷第等学者倾向于从体制特点的角度对俗讲话本进行分类,于是引发了关于俗讲话本构成的争论。
向达根据伯3849号一卷纸背论俗讲仪式的记载指出:“私意以为俗讲话本名称,第一类之为押座文或缘起,第二类可以变文统摄一切大概可无问题……则俗讲话本第三类之名称,疑应作讲经文,或者为得其实也。”(《唐代俗讲考》)
孙楷第的观点也和向达接近而略有不同:“凡敦煌写本所录说唱诸本,其篇目虽繁,约而言之,不过二体。其一为引用经文者:其本先录经文数句或一小节,标曰‘经云’。继以说解,又继之以歌赞。如是回还往复,讫于经文毕为止,此经疏之体,乃讲经存文句之本也。此等本余初目之为‘唱经文’,向君文亦不弃余说,而又据伦敦藏敦煌本《温室经讲唱押座文》一题,疑本名‘讲唱文’。……余今取向君之说而变通之,目曰‘讲唱经文’。此一体也。其二以说解与歌赞相间,虽说经中之事而不唱经文,当时谓之‘转变’。谓其本曰‘变文’,亦省称曰‘变’,乃讲经而不存文句之本。此又一体也。其转变而非说经者,则又变文之别枝。然所说之事不同而文体实一。以文而论,自当附于经变,不得判为二也。”(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
向、孙二人在写作期间曾互相讨论,对第三类话本是称“讲经文”还是“唱经文”有过不同看法。
这些争论尽管无法达成一致的见解,有的争论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90年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些争论是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的,并对此后的敦煌文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收稿日期:2003年10月28日)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白话文学史论文;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文; 读书论文; 郑振铎论文; 佛教论文; 佛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