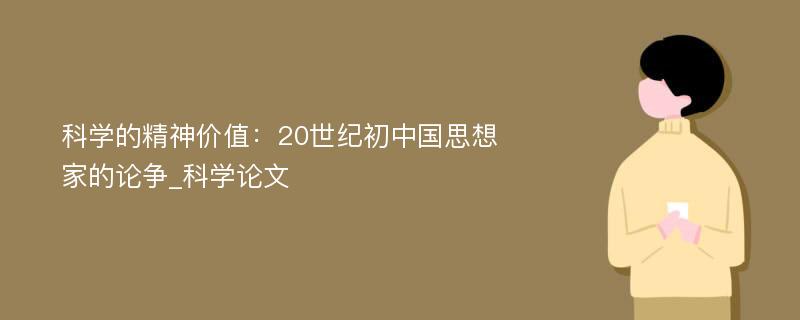
科学的精神价值:20世纪初中国思想家之间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家论文,初中论文,价值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洋务运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对西方近代科技之物质功效几无异议,而对科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却争论颇多。思想家们围绕以下几个大问题展开了许多辩论。
一、科学的应用是否必然有益于人的精神生活?
关于这个问题,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都坚信科学的应用必然有益于精神文明。第一,科学必然有益于人的智力发展。科学对于教育的重要尤在于“其所与心能之训练”(任鸿隽,第108页)。第二,科学研究能增加精神快乐。科学活动本身能满足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丁文江,1923年a,第53-54页;胡适,1929年,第159页)第三,科学是人格教育和品德修养的最好工具。(任鸿隽,1923年,第129-130页)科学知识能使人知道宇宙万物皆循因果律,帮助人们创造新因以求新果,从而增加人的自由;生物学的知识使人知道生存竞争的残酷,从而增加人类的同情心和道德责任。(胡适,1923年,第12-13页)科学还能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将真理作为人生的向导,从而成为改良人生观的有效途径。(同上)第四,科学能增强人的想象力和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天文学、物理学的发展可以使人知道空间无穷之大,从而增加人的美感。(同上)近代科学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了合理的信仰和人化的宗教,努力建设充满爱心的“人世的天堂”。(同上,1926年,第164-165页)
与上述见解相反,玄学派把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尤其是世界大战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文明过于发达,并进而指责科学对于精神生活的危害。第一,科学的发达使机械的宇宙观盛行,人与自然为敌,力求克制之道,无时无刻不在防御自然压迫之中。(瞿菊农,第247页)第二,科学发达使人的精神生活变得枯燥单调。因为,科学理智专重概念推理,科学越进步,抽象性也越显著,距真实的人生也就越远。况且,科学教育分工过细,学一艺而终于一艺,人格的健全发展难以实现。(屠孝实,第246、249页)第三,科学使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失去根基。自西方近代科学昌明以来,哲学家们根据实验心理学把心理和精神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善恶责任便成问题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全社会人心都陷入了怀疑、沉闷、畏惧之中。(梁启超,1920年,第261页)
也有人不同意上述两种观点,认为科学是中性的,其本身原本无好坏可言,其对精神生活的影响也不具有必然性。第一,科学教育并非必然影响人性向善。既有正例也有反例。况且科学家的真实生活并不必然受其研究习惯的影响。(林宰平,1923年,第178页)第二,科学旨在求真,德行旨在立善,其途术不同,的鹄亦异,两者实无因果可言。所以,科学并无直接进德之功,仅为进德之资。“有因科学而进德者,科学不任受德。有因科学而丧德者,科学亦不任受怨。”(唐钺,1917年,第316页)
二、科学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是否有其限度?
肯定科学能力有限的人将科学的作用限制在理智的范围内,认为在理智之外科学无能为力。第一,科学侧重于量的计算,其成功之处在于物理界,人的意志力强弱、文学创作的思想途径以及个人意志与社会进化的关系,并不能用科学方法来一一测定。(张君励,1923年a,第223页)第二,科学方法是分析,而人生观不能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实验和分析。(张东荪,1928年,第97页;徐复观,第56页)第三,关于情感的事项是绝对超科学的。(梁启超,1923年,第142页)“爱”和“美”具有神秘性,也绝不可以用科学来分析。宗教、道德和艺术等属于“文化价值”的范畴,但它们永远只能由心灵去接触,而无法用感知来把握。(张君励,1923年b,第38页)第四,科学的对象是自然因果律,而忏悔、责任心和牺牲精神等精神现象属于意志自由的范围,科学无法解释。(同上,1923年c,第93页)
相反,科学派则强调一切精神现象都是科学研究的材料。第一,宗教和艺术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虽然对宗教、艺术中的某些成分科学尚不能说明其所以然,但这只是受科学的发展水平所限,并不能说明科学不适用于研究这些现象。(唐钺,1923年a,第290页)第二,爱和美等情感现象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分析的。人们之所以把它们看得很神秘,主要是由于其成因复杂,一时难以分析得很精确。而且,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美术之普遍原理、审美的依据和美术创造的动机,能“把美感从本能感觉的范围之中,升到理解的水平线上”。(王星拱,第249页)第三,人生观也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因为人生观至少可从动机和方法两方面来分析。(唐钺,1923年b,第273-274页)
三、科学能否作为人类全部精神生活的基础?
在科学派看来,应该以科学作为全部精神生活之基础。第一,人生观只有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受科学方法的支配,才有是非真伪可言;否则,人人都可以将不讲理的人生观标榜于社会,社会将不得安宁。(丁文江,1923年a,第52页)况且,人生观是因知识而变的,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都确实使人类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唐钺,1923年c,第218页;胡适,1922年,第59页)第二,科学是道德教化的基础。人是心理的、生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综合体,道德理性只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当它通过具体生命来表现时,必然受到心理生理条件的限制,所以,道德问题决不是孤立的,而必须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来处理。必定有一天会出现道德的科学、宗教的科学,这并非使人成为实验室、真空管中的老鼠,而是应用科学方法对道德和宗教问题作知识性的研究,使之能为人的理性所接受。第三,科学是信仰的基础。科学要求,一切信仰都必须经得起理智的批判,须有充分的根据,否则,只可存疑,不可信仰。事实上,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和批判能力,旧宗教的迷信部分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胡适,1926年,第164-165页)第四,科学还是情感的基础。“知识越丰富,表示情感的能力越大;越能表示情感,知识越丰富。”(丁文江,1923年b,第203页)凡情感的冲动都要以知识为向导,使之发展程度提高,发展方向得当。(同上,第206页)
在玄学派看来,科学理性必须受制于价值观念,价值意识才是真善美的根源。第一,哲学高于科学。从对宇宙本质的认识来看,张君劢认为,各门科学的范围都是有限的,而哲学却研究知识、精神生活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以及信仰与希望的问题,哲学可以探究心灵活动的源头和思考方法,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比各门具体科学重要得多。从对科学本质的把握来看,张东荪认为,科学犹如一把快刀,一切东西碰着了便迎刃而解,即使最神秘的生命精神、情感意志也无一不受科学的宰割,但是,这能宰割一切的刀本身,却需要玄学的智慧来研究。(张东荪,1923年,第238页)从对人生最高境界的领悟来看,冯友兰认为,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靠直觉的方法,人生哲学必须从正(逻辑)的方法开始,以求得清晰的思想;终于负(直觉)的方法,以达到人生的最高点,所以,神秘主义不是反理性的,而是超越理性的。(冯友兰,第381页)科学的应用也需要人生哲学的引导,“人生哲学若不改观,自然科学总不免被人误用而成为毛病”。(林宰平,1926年,第28页)第二,道德高于科学。为了使知识服务人类而不至于使人类因科学而牺牲,必须使知识符合道德标准。(张君励,1965年,第704页;1955年,第369页)唐君毅认为,科学是见闻之知,道德为如何运用见闻之知的德性之知,人在从事科学研究或应用科学知识时,必有一依赖于德性之知的价值判断为之主宰。人必须在科学之上,而科学不能在人之上,故德性之知恒主宰见闻之知。他批评新文化运动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以科学的概念在人之上,乃一不知道本源之论,他称之为“科学一层论”、“理智一元论”或“泛科学主义”。(唐君毅,1958年a,第440页)第三,宗教高于科学。科学家对于真理的信仰是超出经验的,带有宗教性,需要靠宗教来培养。唐君毅指出,人类必须以宗教精神主宰科学精神,用宗教精神反省西方文明背后的罪过,防止科学的滥用。(同上,1958年b,第40-42页)傅伟勋将人的心理活动分为从高级到低级十大层面,科学处于第五层面,是知性探求;宗教处于第十层面,是对“天道”、“天命”、“上帝”等终极存在的把握,非科学知性所能穷尽。他批评丁文江、胡适等人将生命的较高层面简单地化约为知性探求,结果走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方法万能论。(傅伟勋,第67-68页)
四、是否有必要用科学来改造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
这首先涉及是否有必要用科学方法拯救中国传统学术的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毛子水强调,要吸收欧洲学术中的“重证”、“求是”和“精确”的科学精神,医治传统学术思想的痼疾,再造一个能与欧洲学术文化并驾齐驱的“国新”。(毛子水,第133页)陈独秀指出,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为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为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陈独秀,第136-137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科学方法不能把握中国古代学术(尤其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和高超境界。梁漱溟指出,孔子的“仁”是代表中国文化以有别于西方计较功利的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直觉方法和修养境界,非理智(科学)所能把握。贺麟也指出,陆王的致良知、程朱的格物穷理,皆非科学方法,乃直觉法。只有这种方法能综观万物的全体大用,理解事物的性理,把握经典古籍中的义理,而科学方法只能认识事物表面的、粗的、部分的方面,而不能认识形而上的、里面的、精的和全体大用。(贺麟,第191页)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是否有必要用科学来改进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对此,玄学派和科学派大多主张用科学精神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第一,要改掉注重人事而轻视自然的毛病。张君劢指出,中国的“格物致知”与西方的科学明显不同:前者目的是修身养性,而非求真理。学术的对象为人生、人伦,而非宇宙客观自然和客观社会;治学的方法为内省、读书和待人接物上的体验,而非观察实验;学术的标准在圣人和经典而非实验事实和调查成果的效验。(张君励,1935年,第207页)所以,“吾国两千年来忽视自然界之知识,因而不知有科学。此为吾国之缺点,而应以补救之。” (同上,1933年,第230页)第二,要革除思想模糊、不精确的习惯。中国思想界长期存在着片段而无系统、模糊而不准确、笼统而空泛等弱点,这是与科学绝对不相容的。改掉这些缺点,最好是研究科学。(唐钺,1923年d,第301页)“科学思想的发展,可以药中国思想界之‘囫囵吞’和‘差不多’的毛病”。(张君励,1934年b,第118-119页)第三,要树立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梁启超指出,科学精神是教人求有系统、可以教人之真智识的方法。中国学术界自秦汉以来因缺乏科学精神而导致笼统、武断、虚伪、因袭和散失等弊端,致使二千多年来思想界的内容平乏、求学问的途径阻塞。“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梁启超,1922年,第578页)
还有是否有必要用科学来改造中国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张君劢等玄学派人物虽然赞成用科学精神改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但反对用科学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张指出,自孔孟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则为精神文明。(张君励,1923年b,第38页)在人欲横流、世风日下之际,“欲求发聋振聩之药,唯在新宋学之复活”。(同上,1923年c,第118页)“中国之复兴,既不能没有科学,也不能丢弃宋明理学。”(同上,1933年,第212页)
科学派人物则竭力主张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任鸿隽说:“我们应该多提倡科学以改良人生观,不当因为注重人生观而忽视科学。”(1923年,第131页)胡适指出:“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借它的朝气来打掉一点我们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1935年,第420-421页)
五、短评
20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对科学的本质及其功能的认识在不断延续和深化,但争论远未结束。要加深对科学的精神价值的理解,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几大难题:
1.科学作用于全部精神生活的可能性
要说明科学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普遍有效性,必须有正确的规律观、科学观和人的本质观。第一,要对自然因果与自由意志的关系作辩证的理解。自由意志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之上的,而且,任何精神现象最终总可以找到其中的因果关系。所以,对精神现象进行科学研究是完全可能的。玄学派抬高了主观性和自由意志,而贬低了科学的精神价值;科学派则在举起客观因果律的旗帜时,将意志现象和主观性等同于机械运动,结果走向机械主义,无力与唯心论相对抗。陈独秀、瞿秋白和胡绳等人坚持唯物史观,在与观念论和机械论作战时,从这两者的对抗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来,这也是一条至今必须坚持和不断完善的正路。第二,必须对科学方法有正确理解。科学方法不等于实验方法,各门学科的方法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研究精神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说科学可以适用于研究一切精神现象,并不意味着物理学方法或实验方法可以随意乱用,而是说要用适用于精神领域的特殊方法来研究精神现象的特有规律。应该承认,确实有些精神现象是不能用实验方法测定的。唐钺说过,人的日常生活条件过于复杂,实验的方法不能够完全应用。各门科学既有各自特有的方法,也有共同的方法。普及科学不仅要提倡共同的方法,也要提倡各门科学的特殊方法。(唐钺,1923年a,第290-291页)张东荪也曾指出,科学方法不是科学所穿的衣服,可以随便剥下来给别的任何人穿。科学方法决不仅是形式论理,而是与科学内容不能分家的。科学各应其对象而各取其特殊方法,科学方法愈普遍就愈失其独到精神。所以,要真心提倡科学不能只注目于空洞的、根本的、抽象的科学方法。(张东荪,1923年,第236-237页)第三,对人的本质要有全面的把握。牟宗三将康德的“纯粹善良意志”与王阳明的“良知”拼凑成纯主观的“道德理性”,以此作为人的最高本质和真善美的价值之源,要求以此主宰科学理性。唐君毅从黑格尔的主客绝对同一的客观唯心论原则出发,设计出一个“道德自我”,以此作为人的本质和精神生活的主宰,要求科学的精神(理智的态度)受此支配。这显然都是对人的本质的误解,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摆正科学在人格修养和道德教化中的应有位置。
2.科学作用于精神生活的根本途径
从人类的全体来看,科学活动和道德活动是同一实践过程的两方面,因而科学作用于精神生活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科学的认知功能和道德功能统一于人类的实践过程之中。事实上,人类总是在科学的创造和应用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唐君毅反对康德“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绝然划分的思想,认为科学也不单是求知的过程,科学活动在求真理的同时就包含超越自然的本能欲望或其他自然心理束缚,而显现“道德自我”之本性活动。所以,在任何科学的求知活动中也有一道德价值之实现。(唐君毅,1958年b,第80页)张东荪指出,人类没有纯知和静观,任何思想和知识都有两方面:一是对付客观之主观的态度,一是主观自身因此种应付而起的变化。(张东荪,1946年,第330页)这实际上是把科学的功能问题放在认识活动的过程中来观察,比静态地、抽象地争辩科学有无道德教化功能要深刻得多。
3.科学作用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机制
科学活动确实可以直接创造出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和优良品质,也可以通过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而间接影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对此,吴稚晖、胡适和王星拱等人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所作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但是,科学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形成的品质是怎样影响其研究活动之外的精神生活的?为何有的科学家并不具有高尚的人格?科学又是怎样影响非科学家的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的?这些问题至今仍发人深省。
4.科学在人类全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
科学与哲学、道德、宗教和艺术有其各自的特点和功能,这就决定了它们在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求方面必然各有侧重。在人类真实的精神生活过程中,这些因素总是相互作用、互为补充的。我们固然不能因提倡科学而贬低哲学等其他因素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但是,更不能因强调道德等因素的作用而贬损科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基础地位。
5.用科学改造儒家文化的必要性
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一直在不断揭露和批判儒家文化中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腐朽成分,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对此有时也是认同的。当年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联系儒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评价其社会作用,分析儒学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其方向是正确的,许多重要结论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陈独秀和胡适、殷海光等人当年批评儒学、宣传科学的言论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辉。为了使科学在中国植根,必须继续将科学精神融入中国人的价值规范和行为习惯之中,继续用科学来改造儒家文化,努力营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精神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