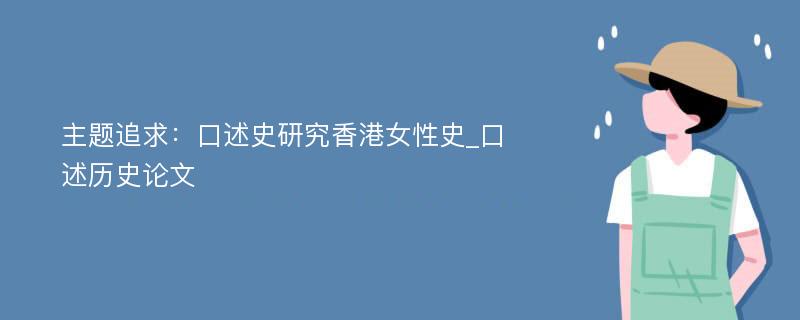
“主体的追寻”:口述历史作为香港妇女史研究的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香港论文,主体论文,史研究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2-0081-06
因为受到殖民地管治的影响,香港历史的关注一直以来集中在英国管治的模式、政策及其引申的社会变迁,少有处理香港特别是华人社群之间的张力和变化。直至蔡荣芳的《香港人的香港历史》(1993)提出由香港社群大众的生活出发书写历史,香港的历史论说才正式由殖民地统治为中心的观点改变过来。不过即使这样,蔡氏研究的早期香港历史主角仍然少有妇女的份儿。早期香港的居民记述中不乏商贾、苦力、矿工、工人甚至罪犯及海盗,① 然而有关妇女的部分除了指出男女失衡(女少男多)之外,就只有如“涉外婚妇”(protected women)、被拐带的妇孺及妓女等受害的妇女的片段,② 其他有关妇女生活的资料基本欠奉。
叶汉明在她的《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1999)详细整理香港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关香港妇女的研究,是香港“妇女史”的一个重要开创性参考。③ 按她搜罗的资料可见,有关香港早期妇女状况的研究大部分来自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包括了对中国文化传统或乡俗中家庭制度的兴趣,④ 或对早期香港社会存留下来的习俗如妇女的买卖、蓄婢、养妾及童养媳等问题的文献及个案研究。⑤ 有趣的是,来自历史学者而以妇女为焦点的研究却寥寥可数。⑥ 换句话说,撇开西方人类学式对中国文化传统习俗的“东方主义式”兴趣和发掘外,⑦ 香港过去的妇女历史研究近乎空白。由此可见,历史研究的发展并不如它最初宣称的客观。叶汉明指出,妇女史在近代社会史及新文化史的脉络中成为新的关注,正是因为20世纪中期以后学术界对史学的客观性提出质疑。⑧
除了人类学式的田野研究外,20世纪80年代开始多了一些点滴的记述,如黄玉梅编写的《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历史:1920—1988》以及何芷芊主编的《演进: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八十年》。⑨ 不过两本刊物的重点皆为个别机构的史略回顾,对早期的华人妇女广泛生活境况并无细述。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关几位早期华人妇女领袖如李添嫒(第一位受按立的华人女牧师)、李曹秀群(第一位香港立法会华人女性非官守议员)及李清词(第一位在香港按立的女牧师)的自传和著述的出版,才稍微给华人妇女提供了初步的历史存盘资料。⑩ 此类个人自传式的出版,就个别妇女在香港历史中穿插成长、经营家庭及发展事业所面对的种种情况,作了非常重要的补充。类似的作品最近可见于一本衍生自郑宏泰对何东家族历史长期研究的书稿,其中对生活于19世纪末、穿梭于欧亚族裔和华人社群之间、一手奠定今天显赫的何家基业的施氏的生活片段整理,总算丰富了香港早期华人妇女的生活面貌。(11) 除此以外,香港的历史写作正如小思在《晚晚六点半》的代序中指出的:它只限于殖民地政府“隐没式”的历史,(12) 像所有官方历史一样只可以说是男性的历史。
本文以叶汉明著作书名为引题,探讨口述历史作为香港妇女史研究的进路,也算是香港妇女史研究的一项延续。
一、妇女口述历史的发展
利奥塔(J.F.Lyotard)在他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提出现代主义充斥着“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s),它们建基于科学实证主义,以客观真实为基础,对人类的进程充满信心。然而,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正要针对此等前设,对于那些由建制权力主宰的宏大叙事能否为人类前景提供出路提出怀疑。相反,后结构主义理论者如福柯、德里达及拉康等,相继指出宏大论述如何不过是权力操作的结果,如何有系统地将“他者”如妇女、低下层、不同族裔、性向、能力等弱势社群边缘化。简单来说,人类的故事是复杂的,不可为某一个建制主导或主流意识所产生的宏大叙述所统摄。与现代主义后设论述中的理性、自主的主体相反,拉康所论说的后现代主体是零散的、破碎的及多重性的。从后现代论述来说,个人并不是一个生物或自然的独立个体,而是由权力和知识所塑造的,是从她/他们文化的处境中冒出来的。于是,如何对后者的主体进行一个全新的书写是一项挑战。生命故事的目的就是要去捕捉人类经验的社会建构意义,及其中文化语言伴随的主体性。换句话说,主体要通过言说,包括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不断相互竞逐的话语,才得以建立。(13)
口述历史可以说是从以上的疑问开始,并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工具。事实上,按汤普逊(Paul Thompson)所述,口述历史其实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记述方法,而19世纪的历史写作更视个人见证与法例、通俗及事件的文献为同等重要。当代的口述历史运动则由里芬斯(Allan Nevin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起,并发展成一股“从下而上”的历史书写运动,着意发掘普罗大众的生活史。(14) 20世纪80年代开始,口述历史被女性主义者引用为一个重要工具,以提取一直以来被忽略的妇女生活经验和故事。透过口述故事的补充,她们希望将妇女的声音重新引介到历史的中心。(15) 结果,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过去三十年有关妇女的传记、自传以及口述故事开始渐渐进入成为我们今日历史的重要部分。
汤普逊相信,口述历史可以转化历史书写的内容及过程,为发展一个更具社会意识及民主化的历史叙事提供一个更丰富的可能性。(16) 显而易见,口述历史的焦点和书写方法都有异于一般的史料及文献的阅读、搜罗、选取、整理和阐释,它是以叙述者为历史主要资料的选取者和诠释人,以他/她诉述的生命经历为主要的文本。另一位学者培克斯(Robert Perks)亦曾指出,口述历史专注于捕捉人独特的记忆和生命记叙,为历史添上丰富多彩的个人面貌,并赋予生命。通过收集和保存“第一手”的个人资料或“亲身”经历,历史书写记录多重而不是单一的声音、复数的而不是线性的历史片段,让创造和体验历史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和声音介入、细写历史。(17) 在亚洲,洪莉莎(Hong Lysa)曾在她关于东亚社会的研究中指出,口述历史对于从16世纪开始广泛受殖民洗礼的亚洲地区别具效用,它为历史学家提供一个更适切的途径,去搜罗及聆听殖民时期中普罗大众的日常经验及个人视点。(18) 事实上,有关香港在1941—1945年日本占领期间的生活经历,现在还得通过当年的历史见证人靠记忆一点一滴地补充。(19) 同样,今天香港的普通民众自1997年后,本土意识大大提升,对香港早期历史的兴趣大增,于是,不同的口述历史计划陆续涌现。这些以香港为中心的口述历史由关心个别小区的变迁,到深入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并延展到对边缘社群生活故事的关注和尊重,正在默默地汇聚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为本土历史增添丰富多元的面貌。
女性主义者对于口述历史的重视,来自对正统历史的失望,因为它们不仅少有记载妇女的生活和故事,更对妇女在历史中的角色存在有意无意地扭曲和贬抑。(20) 女性主义者相信口述历史可以更有效地保存妇女的声音,填补传统历史记录的空白,使不单是妇女而是整体人类的历史更全面。再者,因着它独特的资料收集和演绎的方法,口述历史能更深入地开发女性鲜为人注意的生活部分,通过来自不同阶层和社群的妇女所阐述的故事,更有效地开发不同的妇女议题和展示其中的复杂性。(21)
纵观不同妇女口述历史的书写经验,它还具备一项建立妇女社群的功能。汤普逊相信,口述历史根本改变了书写历史的内容和过程,其中最明显的转变是历史学者的身份成为一位访谈人。(22) 格路克(Sherna Gluck)更认为访谈人与受访者的关系并不是中立的,相反,访谈者是带着女性主义关怀进入访谈之中,即使受访者本身并非女性主义者,彼此相遇已经构成了一个女性主义的相交,访谈者与受访者的接触就是一个跨越年代的妇女交流机会。在讲述、聆听和分享的过程中,访谈者与受访的妇女“惺惺相惜”、交流“女性主义”的见地,并通过大众记忆的共同塑造,使口述历史成为一个结聚横跨时空和地域的女性社群意识的平台。(23)
科丝丽(Tess Cosslett)、卢莉(Celia Lury)和森玛菲尔德(Penny Summerfield)特别强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口述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元素。事实上,没有一个生命是单独的、孤立的主体。相反,是我们意识中一个不可或缺部分。自我叙述本身就是建基于他者的认同,“我”和“他者”实在是两个不能分割的组构成分。这一点对妇女来说尤其重要。当受访者收到自己叙事的记录,她们才重新发现自己,为自己走过的岁月下定义。如是,妇女的个人叙事不单是了解妇女经验的最佳工具,也可以同时就妇女的不同处境、不同生活空间,为她们遭遇各种因性别身份而带来的困境和她们的不同解脱方法保存最丰富的记录。历史亦不再是关于过去而已,而是当下意识的一种建造和再建造。
二、香港的妇女口述历史
1997年回归前后的香港,一些研究单位陆续开展了不同的口述历史研究计划,(24) 其中除了历史文化目标较显著的寻根式的地区,也有以个别机构为中心的口述历史。(25) 它们分别着眼于后殖民香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急剧变化,并进行因地缘和建制改革所引起的具体人事和景物的变迁从事记述。
从1990年代末到2000年,三个公开宣称是妇女口述历史的作品相继登场。它们包括蔡宝琼统筹和编辑的《晚晚六点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曾嘉燕和吴俊雄编的《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和《16+:少女口述历史》。(26) 这三部作品都是由新妇女协进会半资助或全资助完成,后两部作品正式由新妇女协进会出版,而第一部作品的准备工作、实际采访、录音、传译、最后书写和编辑原稿等过程,均是由新妇女协进会的成员参与完成。《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和《16+:少女口述历史》是用广东话口语写成,有意地凸显及展示妇女“本来”的话音,而《晚晚六点半》虽是用白话文写成,却把编辑的个人反思和整理好的故事,与原来故事的叙述者的言谈和阅读后响应并列于每章节中。
至于它们的内容,《晚晚六点半》叙述大约30个生长在20世纪70年代、赶上夜校的工厂女工的经验;《又喊又笑》包括10名从63岁到106岁年长妇女的叙述故事;《16+》则收集了16名从16岁到25岁青春少女的生活片段。三个口述历史各有不同的关注:1970年代妇女劳工、年长妇女、16岁或以上青春少女。它们有的叙述香港早期女工为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必须提早投入劳动市场,只能靠自己边做工边上夜学来进修;10个阿婆的口述历史则是首次为香港妇女从战后到香港的生活,留下如此详尽和精彩的片段;再加上16到25岁这组年龄段的大女孩,畅谈她们的工作、恋爱和情欲,记录了香港新一代的女性的地道经历,并在漫不经意的意象和文字中渗透着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反叛和坚持。从香港历史一直以来都缺失妇女的关注来说,三个妇女口述历史可以说都是冲着香港历史的片面性去写,目标是要将不同阶层和时段的妇女生活写进香港的历史之中。
2000年以来,女性口述历史越见蓬勃,而边缘妇女社群成为一个重点关注。首先,新移民妇女接连出现悲剧,(27) 于是有关她们的口述历史相继出现。其中道出中国内地和香港在经济发展歧异下,两地婚姻出现了大量低下层男性劳工回乡娶妻之后的家庭适应问题。那些初来乍到后捱尽白眼和歧视的年轻妇女的种种遭遇,通过自我叙述跃然纸上。(28) 其中,陈惜姿以12位新移民妇女每日的生活及其间踫见的人事种种编写成的《天水围十二师奶》(2006)最为触动人。(29) 2008年,蔡宝琼、叶汉明及潘毅完成另一本以20世纪70年代成衣女工为焦点的口述历史,展现一代妇女如何辛勤而自信地投入香港经济建设,却换来80年代香港制造业北移后的淘汰和唾弃。(30) 如此一段段辛酸但隐秘的香港妇女故事,要不是通过口述历史的记述,就只会为公众所忘记。它们的出现,为香港妇女运动历史写下不可能遗漏的重要部分。
四种涉及女同性恋、女双性恋者以及性工作者的书籍在21世纪初出版,记述着新一代女性为自己的身体、情欲及性向身份而挣扎的点滴。它们是:《双性情欲》(2000)、《月亮的骚动——她她的初恋故事:我们的自述》(2001)、《她们的女情印记》(2005)以及《性是牛油和面包》(1999)。(31) 前三本书情辞恳切地述说以女性为中心的同性爱和双性情欲的个人经历,尝试闯开探讨女性多元情欲的空间。第四本记述女性工作者如何从一个平常生活的观点,谈论各自的工作境遇和性经验。它们所组构的是首个由妇女发起、叙述少数群体色性经验的平台。通过自我叙述,她们努力排解经常强加于身上的不同类型标签,为自己的性向身份抗辩。
2007年,在香港大学拨款委员会展开研究基金的资助下,“华人妇女基督徒与香港基督教”的口述历史计划正式开展。由黄慧贞、蔡宝琼、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代表组成的研究队伍,分别约访了26名年过65岁的基督徒妇女,进行深入访谈,聆听她们的生命故事,最后成功誊写出版22个故事。(32) 受访妇女来自不同的教会宗派,带着不同的成长背景,经历各自不一样的家庭和婚姻生活,跨越不同阶层,各有各的际遇,各有各的精彩,非常难得。每位妇女最少有两次访谈会面,受访者与访谈员之间逐渐建立起一定的信任,由小心谨慎的分享,进展成开怀畅谈动人经历,受访与被访的关系已相互渗透,访谈成为一场跨年代、跨时空的姊妹支持和心路交流。
聆听华人基督徒妇女的历史叙述,不单能使我们对香港历史事件的理解更立体,对大时代中普罗大众包括妇女的生命如何纠结其中有更深入的领会。首先,今日香港“背山面水”的两个边界——罗湖和香港海域——却是从来都没有完全封闭过。直到今天,香港主要人口增长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移民,他们继续与被香港各式国际业务吸引过来的海外专业人员,共同编织着大家渴慕的国际都会图像。聆听一群资深的基督徒妇女述说故事,跟着她们的记忆去寻索妇女如何穿过中国近代的历史时空,在战乱与流徙中经历家庭的种种变迁,总算可以窥见妇女如何也一样跨境越界,游走于模糊的地域边缘的两方。其次,通过一群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妇女叙述,我们可以具体窥见成长于中国家庭的祖母、母亲及姊妹,如何承受着制度及文化的束缚,在应守的礼节和从属的地位中寻找生存空间。吊诡的是,中国人对以生育及家庭作为妇女侍奉天职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一偏见是对她们生命的打击,同时也是激励。
相对于传统的中国式严管家庭,基督教信仰并没有给予妇女释放自己、摆脱父权建制的力量。相反,华人基督徒妇女在其中遭受到双重的束缚——中国父权家庭对她们“安守妇道”的要求和基督教要她们顺服妇女本分的教导。然而,相对于女性自主的心灵和具体的实践空间,基督教确又能赋予她们一个家庭以外的据点,让妇女在生活的桎梏中仍然可以保留一点面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念,在无法完全摆脱传统价值观念之余,又能实践一定程度的自主。在两种束缚交碰之下,竟然无意间释放出另类的妇女生存空间。在实时的实践要求和求生的本能意志的推动下,华人、妇女和基督徒构成的不是三个身份,而是相互扣连和流动的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复合体”。
三、主体的追寻:从口述历史看香港妇女史研究
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大学“大众记忆小组”倡议将口述历史作为一个社会生产的记忆。它的性质是政治的,因为它要拒绝放弃日常生活的和大众的记忆。当一个社群能集体地生产一定的共同回忆,它就可以在整体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因此而结聚成转化的力量。(33) 这大概也是各种妇女口述历史的期许。上述香港妇女历史的计划,事实上也在有意无意间建构着某一种的社群身份认同:70年代的晚7点半下班上夜校的女工,无意中见证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转变的阿婆(35),一群经历新一代成长空气的青春少女,受困于新市镇并缺乏支持的新移民妇女,以及各个生活情况经历中的女性小众社群。通过口述历史,她们的声音因结聚而发出不容忽视的“巨声”。(35) 当我们通过那些不完备的记忆与有待修补的情节去记述她们的故事时,口述历史成了最有效的工具,将她们未说的话,包括叹息和感悟,捕捉和记录下来。
除了社群的结聚之外,口述历史更是一个妇女的主体追寻过程。后结构主义拆毁任何稳固的自我观念,后结构女性主义者亦怀疑女性是否可以经验一个现代主义式的主体,包括拥有自主性、持续的身份、能动性等。相反,她们相信妇女的自我是破碎的,而且是在关系中建立的。上述所提到的女性主义式的相遇和结聚正好提供了平台,让妇女自我在得以保持其流动性之余也可以结集成力量,产生一定的转化和更新。在访谈者与受访者、撰稿人与叙事人的“主体间性”交遇中,妇女可以彼此看见,为过去、今日和将来互相扶助、凝聚和转化。从上述故事看来,妇女作为一个叙述主体,所呈现的正好是一个“流动”的能动者(agent)。她既成长及孕育在华人“传统”妇女的低微身份意识之中,却又得经常独自在复杂的社会年代中,面对每日沉重的生活责任。她们一方面既要努力地竭尽她作为女儿、母亲及妻子的“本分”,另一方面又得同时兼顾家庭生活及关顾经济支持,成为一个自觉以丈夫为首却实际要“独断独行”的复杂主体。诡异地,女性主义历史学者提出妇女“自我”的不稳定性,指出她们的记忆往往徘徊于屈从与抗拒建制秩序之间,变得矛盾、零散和破落,却在有限的选择时空中,让能动力显示在不知不觉的生活点滴间。通过不同的经验自述,看似屈从的举措,在叙述者的选择记忆之中,化成了对建制的顽强抵御。严格来说,通过个人叙述,生活最艰难的妇女都成为自己命运的“改造者”。
口述历史的书写在方法论上具有争议性,不断受到质疑:在叙述者所“口述的”与记叙者所“书写的”中间存在的隙缝是否可以弥补?这个问题在香港这个以广东话为主的城市中更见显著。女作家西西就曾经在她著名的小说《我城》中,自嘲香港人的“口”和“手”多年来在言语表达上的争执。(36) 再加上香港从开始就是一个汇聚广东及中国其他省份不断“南来”的移民的地方,不同的乡音、方言在表述上的差异,都构成书写“口述”故事的困难。如何在众多语言、经历和情感表达大不一样的受访妇女的叙述中,誊写出最接近她们“原意”的稿件,正是“口述历史”面临的最大挑战。女性主义叙述中提及妇女的断语、话语之间的停顿、悬句,甚至叹息、重复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因为妇女要在整体仍是父权中心的语言秩序下发声,每每因为要配合句法要求的逻辑而不能畅所欲言,又或要逃避背负颠覆语言所代表的建制秩序的污名而顾左右而言他,结果言词中出现冲突、自我矛盾或失语等,呈现的是非一般的零散和断裂的发声“主体”。(37) 在整理妇女口述历史计划时,除了一众编录人员再三彼此提醒要细心聆听之外,对于由录音带逐字逐句记录的初稿,到整理为“可读的”、有一定时序的稿件的过程,曾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互相参照,以尽量查检并减低书写过程中以文字掩盖叙述意图的程度。计划求得不同的故事写手,而且在书写风格上有意不寻求统一,就是通过不同聆听者的敏感度和各自书写的笔触,企图保留一点多元叙述的空间。
女性主义历史学者期望寻找的女性历史主体,通过妇女对自己生活的叙述,一次整理、审视、就事件的重演并赋予意义建立起来,成为她们自己生命的主人。因为生命故事的叙述不单是一个个人记忆的重述而已,更是一个创意的主体能动力的行使。(38) 香港的妇女史仍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土壤。目前,从口述史的收集可见,妇女口述历史为香港妇女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面貌提供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① Jung-Fang Tsai,The Hong Kong People’s History of Hong Ko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38-39.
② “涉外婚妇”特别指19世纪末香港与洋人(通常是欧洲人)生活的华人妇女。洋商或军官或买人给她们提供住宿和生活,她们则为对方停留香港期间提供包括性在内的家居服务。Carl T.Smith,“Ng Akew,One of Hong Kong’s ‘Protected’Women,”in A Sense of History: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Educating Publishing Co.,1995,pp.266-275.有关当时的娼妓问题,参见Elizabeth Andrew and Katharine Bushnell,Heathen Slaves and Christian Rulers,Oakland:Messiah’s Advocate,1907。
③ 参见叶汉明:《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第77-114页。
④ H.Baker,“Marriage and the Family:Aspec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Weekend Symposium,No.9 & 10,1964,pp.27-31 ; R.Watson,“Wives,Concubines and Maids:Servitude and Kinship in the Hong Kong Region,1900-1940,” in R,Watson and P.Ebrey,eds.,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231-255; R.Watson,Inequality among Brothers:Class and Kinship in South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M.Topley,“Marriage Resistance in Rural Kwangtung,” in M.Wolf and R.Witke,eds.,Wome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67-88; and A.P.Sankar,“Spinster Sisterhoods,” in Mary Sheridan and Janet W.Salaff,eds.,Lives:Chinese Working Women,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p.51-70.
⑤ H.L.Haslewood and Mrs.Haslewood,Child Slavery in Hong Kong:The Mui Tsai System,London:Sheldon Press,1930; J.Hayes,“Women and Female Children i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to 1949:Documents of Sale and Transfer,” in Joseph S.P.Ting and Susanna L.K.Siu,eds,,Collected Essays on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Hong Kong:Urban Council,1990,pp.33-47; M.Jaschok,Concubines and Bondservants: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hinese Custom,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⑥ Carl T.Smith,“Ng Akew,One of Hong Kong’s ‘Protected’ Women,” in A Sense of History: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Educating Publishing Co.,1995,pp.266-275 ; Carl T.Smith,“The Chinese Church,Labor and Elites and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the 1920s,” in Chinese Christians:Elites,Middlemen,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⑦ 这里是指由欧美19世纪传教士发展下来的一种对东方妇女的想象,就是她们都是受异教文化所捆绑的女人,急待救援。对于这些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桎梏中的妇女惨况的阐述,遂成为西方学者的访查对象。
⑧ 参见叶汉明:《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第2-3页。
⑨ 参见黄玉梅:《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历史:1920—1988》,香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1988年;何芷芊主编:《演进: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八十年》,香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2000年。
⑩ 参见李曹秀群:《浮生岁月》,香港:私人印行,1993年;李添嫒:《生命的雨点》,香港:圣公会宗教教育中心,1993年;李清词:《半边天——妇女在教会的地位》,香港:基道书楼,1993年;李清词:《我忆故我在》,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2000年。
(11) 虽然施氏的出身没有摆脱“涉外婚妇”和被拐卖妇女的类别,此书能从有关施氏的旁证重新组织她的故事,为上述类别的妇女提供了更立体生动的参考,实属难得。参见郑宏泰、黄绍伦:《三代女子的传奇:何家女子》,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第1章。
(12) 小思:《代序(一):美丽的书》,载蔡宝琼编《晚晚六点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1998年,第1页。
(13) Dan Goodley et al.,Researching Life Stories:Method,Theory and Analysis in a Biographical Age,London:RoutledgerFalmer,2004,p.101.
(14) Paul Thompson,The Voice of the Past:Oral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19-20.
(15) Joan Sangster,“Telling Our Stories:Feminist Debates and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eds.,The Oral History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8,pp.88-92.
(16) Thompson,The Voice of the Pa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7.
(17) Robert Perks,Oral History:Talking about the Past,London: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ral History Society,1992,p.5.
(18) Hong Lysa,“Ideology and Oral History Institutions in Southeast Asia,” in P.Lim Pui Heun,James H.Morrison and Kwa Chang Guan,eds.,Oral History in Southeast Asia:Theory and Method,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6,pp.33-43.
(19) 参见张慧真、孔琼森:《从十一万到三千:沦陷时期香港教育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 Joan Wallach Scott,“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Joan Wallach Scott,ed.,Feminism &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2-180.
(21) Joan Sangster,“Telling Our Stories:Feminist Debates and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eds.,The Oral History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8,pp.88-92.
(22) Thompson,The Voice of the Pa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7.
(23) Sherna Gluck,“What’s So Special About Women? Women’s Oral History,”in David D.Dunaway and Willa K.Baum,eds.,Oral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New York:Sage,1996,p.229.
(24)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约两年前开展一个大型的“香港口述历史档案计划”,其中进行的项目包括“湾仔口述历史”、就不同行业及不同领域的领袖人物,采集各年代和人事的相片、私人文件等,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备的香港口述历史馆。
(25) 参见顾思满、区士麒:《教院忆旧:师生口述历史访问录》,香港: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1999年;黄素兰:《香港美术教育口述历史:从图画堂开始》,香港:香港美术教育协会,2001年;顾思满、区士麒、方骏编、姚继斌等辑录:《教院口述历史》,香港:香港教育学院,2002年。
(26) 参见蔡宝琼编:《晚晚六点半》,香港: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1998年;曾嘉燕、吴俊雄:《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香港:香港新妇女协进会,2001年;曾嘉燕、吴俊雄:《16+:少女口述历史》,香港:香港新妇女协进会,2001年。
(27) 2004及2007年先后发生两宗震惊小区的悲剧。前宗事件的新移民妇女,虽然已寻求社会服务支持,然终未能逃脱与女儿被丈夫杀害的厄运。后宗事件的新移民妇女则趁长期病患的丈夫人院期间,将两个儿女抛下二十六楼然后自己跳楼自尽。两宗个案中的丈夫都是年长和失业或待业的低下阶层。
(28) 参见薛泽华等编:《回忆:新来港妇女口述历史》,香港:循道卫理杨震社会服务处,2001年;曹疏影、邓小桦:《是她也是你和我:准来港女性访谈录》,香港: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2008年。
(29) 参见陈惜姿:《天水围十二师奶》,香港:蓝天出版社,2006年。
(30) 参见蔡宝琼、叶汉明、潘毅:《千针万线:香港成衣女工口述历史》,香港: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2008年。
(31) 参陈宝琼、陈惠芳、黎佩儿:《性是牛油和面包》,香港:紫藤及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1999年;基恩之家:《同心事件簿》,香港:基恩之家,2001年;陈宝琼:《亚洲性坊间:性工作者的现实与梦想》,香港:紫藤及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2002年;麦海珊、金佩玮:《双性情欲》,香港: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2000年;金晔路:《月亮的骚动——她她的初恋故事:我们的自述》,香港:Cultural Act up,2001年。其中《同心事件簿》和《双性情欲》两书均为香港民政事务处为推广平等机会教育的计划而赞助出版。
(32) 有关各个华人基督徒妇女的故事,详细内容已出版成书。参见黄慧贞、蔡宝琼编:《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以下不另注述。
(33) Thompson,The Voice of the Pa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7.
(34) 就华人基督徒妇女的口述历史研究计划,书籍出版后曾召集有关被访者出席一次重聚。会上受访婆婆的真情分享,互相祝贺及鼓励,特别教人动容。
(35) 香港近两年的一个电视台歌唱比赛节目的中文名称(英文“The Voice”),此处借用其向公众有力发声的意象。
(36) 参见西西:《我城》,台北:洪范出版,1999年,第150页。
(37) 黄慧贞:《在空白和静寂中述说异音:三个香港妇女口述历史的文本政治》,载洛枫编《媒介拟想:媒介与性/别》,台北:远流出版,2005年,第94-98页。
(38) Sarah Lamb,“Being a Widow and Other Life Stories:The Interplay between Lives and Words,”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Vol.26,2001,p.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