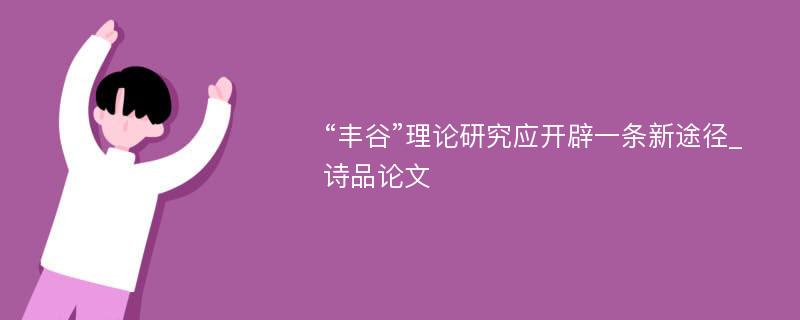
“风骨”论的研究要开新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骨论文,开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3-0103-07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文心雕龙》的研究是一个热点,而关于“风骨”的争论又是其中的焦点。“风骨”的内涵是争论最热烈的课题,产生了种种解说,据汪涌豪先生归纳,主要的已有12种之多。(注:见《文心雕龙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看来,讨论还要继续进行,因为直到上个世纪末研究者们还没有取得共识。
我们细读了各家的论文和论著,发现上述主要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其中的一派,或认为风骨分别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联系,或认为风骨是风格形成的条件,或认为风骨就是风格。这一派涉及风骨内涵的解释不多,这里暂且不议。另两派在风骨的含义上意见相反,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争论最多的是这两派。第一派以黄侃为代表,认为风关乎文意,骨关乎文辞,或者说风是对文意的要求或是意气骏爽的表现,骨是对文辞的要求或是语言质朴刚健的表现。例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先粗略地指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进一步解释说:“结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气之骏爽者,即文风也”,“辞精则文骨成,情显则文风生。”同意黄说或基本上同意黄说的有范文澜、傅庚生、詹锳、王运熙、周振甫、吴调公、缪俊杰、蒋祖怡、敏泽、寇效信、陈伯海、汪涌豪、陆侃如、牟世金、毕万忱、李淼、穆克宏、杜黎等学者。当中有个别学者曾直接说风是文意,是作品的思想感情,骨是文辞,是作品的形式,如范文澜、傅庚生等。这一派学者阐发刘勰的风骨论,依据的是《风骨》篇中的核心语句,我们姑且称之为尊刘派。第二派学者对“风骨”的理解与之相反,这一派以刘永济为代表,认为风指作品的情志或是感情的力量,骨指作品的事义、思想内容或是逻辑力量。采取这一观点或基本赞同这一观点的有宗白华、廖仲安、刘国盈、郭晋稀、郭豫衡、赵仲邑、刘纲纪、张少康、涂光社、张文勋、杜东枝、罗宗强、叶朗等学者,其中也有个别学者在肯定骨即文意的同时把风归于文辞或“文”的范畴,如朱恕之、舒直、陈良运等。这一派学者阐发刘勰的风骨论,在风的含义上与尊刘派有些接近,只是把尊刘派说的风是意气情志显豁的表现径直说成风是情志或感情的力量,对骨的含义的解释就与尊刘派绝然不同了,他们把骨从文辞方面拉向作品的内容方面,直说骨就是作品的思想、事义。这一派主要着眼于对刘勰风骨的概念另作解释,对“风骨”(主要是“骨”)的内涵加以改造,我们姑称之为改刘派。
改刘派批评尊刘派的方法之一就是抓住黄侃的“风即文意,骨即文辞”八个字。我们认为,单就这八个字而言,是有毛病的,引申下来,一切文学作品都有意与辞,岂不是一切作品都有了风骨了!标举风骨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但这一批评不难反驳,因为黄侃随后还有解释,这一解释是符合刘勰原意的。
改刘派批评尊刘派的方法之二是从《风骨》篇外找根据,他们引《体性》篇云“辞为肤根,志实骨髓”和《附会》篇云“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作为根据,认为刘勰讲过骨是志或事义,而对于《风骨》篇的核心语句则多有回避。我们认为这两个根据也不难反驳;首先,骨髓是髓,不是骨,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其次,所谓肤根、骨髓、肌肤、声气之类也是以人体作比喻,肤根、骨髓是一个系列,神明、骨髓、肌肤、声气又是一个系列,风骨更是一个系列,在不同的系列中,这些概念有不同的搭配,各有特定的内涵,不可因字面上相近而互相“代入”或“置换”,得出风骨的骨是情志或事义的结论。
改刘派批评尊刘派的方法之三是通过训诂的方法把刘勰所说的“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中的“辞”解说为“篇章”,然后从“先”和“待”上做文章,认为骨是思想内容,骨与辞有先后关系,有因果关系,即树骨于前(指思想内容决定于前),选词于后(指运用文辞加以表现于后),骨为辞之因,辞为骨之果。我们认为这一解说似是而非,把骨理解为思想内容,说骨在辞前,针对刘勰所说的“沈吟铺辞”等四句可勉强说得通,针对刘勰的另外两句“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就说不通了。因为在这后两句中,言直辞精是因,骨变成果了。持此论者难以自圆其说。黄侃似乎早就预见到会有人在“先”与“待”上求新解,故在《札记》中预先声明“言外无骨。”意为骨是结言端直的结果或表现,是言或辞本身的属性,故而说言、辞外不存在另外的骨。我们认为把骨理解为思想内容诚然是一个好的见解,然而把这个见解塞入刘勰论述语言文辞的句子中就会扞格不通。
平心而论,我们认为尊刘派的解释是忠于刘勰的原意的,各位学者的阐述空前的一致,而改刘派则力图从不同的角度改变这种解释,角度不同,力量就显得分散。我们一直在想,为什么大家都研究刘勰的风骨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呢?思之再三,我们以为可能是尊刘派认为刘勰的《风骨》篇讲的是正宗的风骨论,舍此之外不应有第二家,不应有第二种解释,他们对刘勰的解说深信不疑,对自己的解说也非常自信,黄侃就说过:“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或者舍辞意而别求风骨,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彦和本意不如此也。”(《札记》)改刘派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攻诘,我们认为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而是因为对刘勰的风骨论不满,他们心中另有一套不同于刘勰的风骨论,可能是我们的学术界对刘勰过于崇拜,他们大概不便直说刘勰错了,故而用另作解释的办法来改造刘勰名义下的风骨论。
我们认为风骨论的研究要取得突破,就应该开拓新路,应该把刘勰的风骨论纳入到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风骨论背景之下来观照。当我们回到魏晋时代品评人物的“风骨”概念的原始意义上把握“风骨”的基本内涵时,我们就会发现刘勰“风骨”论本身的局限性。
一
首先,我们认为刘勰背离了早于他存在的魏晋人物品评的风骨概念,在风与骨的内涵上完全改变了传统的理解。
众所周知,汉代已有通过骨相品鉴人物之风气,通过骨法判断人的富贵贫贱的命运,也可察骨法而知人的操行清浊。到魏晋时代,上层社会极重人物的风度、形貌之美,通过风骨考察人的精神气质,在名士们互相品评时常常用“风”、“骨”、“风骨”等词,如《世说新语》、《宋书》品评王羲之、刘裕就风骨二字连用,这些资料,研究者们多次引用,已为大家熟知,我们就不再引述了。此外在古代画论、书论中也有人使用“风”、“骨”、“风气”、“骨体”、“骨气”、“风骨”等概念。但这些画论和书论成书的年代和刘勰很接近,我们很难找到它们成书的绝对年代以确定与《文心雕龙》成书的时间先后,故而不敢断言刘勰把“风骨”概念引入文学理论也是受到它们的影响,只肯定刘勰是袭用当时广为流行的人物品评的风骨概念。
“风”、“骨”、“风骨”等概念在人物品评中的含义是什么呢?研究者们的意见没有什么差异。王运熙先生说:“风骨这一概念,原来用以品评人物的风度、神气、形貌。”风偏重于“品评人物的风姿、风神”,“品评人物的骨,是指骨相,即人的骨骼长相。”(注: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风骨论》,《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第54、55、57、60、60页。)詹锳先生说:“实际上,六朝时代论人的风骨,也是取其比喻义,是通过某个人的风神和骨力来比喻他的风采品格,并非仅限于他的形体特点。”(注:詹锳:《再论“风骨”》,《〈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0页。)我们认为,这些解释都很准确,能为学术界共同接受。如果我们再稍作解释,是否可以这样说:风是一个人表现于外部的风貌,从人的顾盼颦笑、举手投足中显示出来的风采,是一个人的精神气质的外现。骨是一个人存在于内的品质、气质(詹锳先生认为“骨力”即比喻“品格”)。风表现于外部,是人的生气、生命力的外现,骨在形体之内,由肌肤包裹,是人的形和貌的决定因素,是人的生气、生命力的本源。有什么样的骨就会有什么样的风,骨决定风,风不能决定骨,只能反映骨。人在不从事社会活动、不与人群相接触时,风看不出来,而骨却是客观存在的。因而,骨是第一性的。
刘勰把风骨概念从人物品评移用于文学理论,我们认为他大体上应该采用上述人物品评的风骨的内涵,然而事实不是如此。
关于刘勰的风骨概念的内涵和人物品鉴所用风骨概念有没有本质联系的问题,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有,认为“基本上是一致的”,“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两三位学者认为没有本质联系(这些学者既有尊刘派,也有改刘派),其中有人认为刘勰对人物品评的风骨概念做了相当彻底的改造,新词与原词的词义基本上互不相干,刘勰只是借用了其语言外壳,只用了相同的两个字。
我们认为少数学者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风骨》篇开头就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看来,刘勰的风是《毛诗序》中的讲的风,刘氏是崇儒尊经的,所以他用《毛诗序》的观点来解释风,认为风是教化力、感化力的源头。他用儒家传统的风教思想解释风,但到此为止,往下并没有贯彻全篇,而是从第二句“志气之符契”生发开去,认为风也是情志的表现,于是风又和意气、情志联系起来,接着刘勰把风当作意气骏爽、情志显豁的表现,说:“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深乎风者,述情必显。”由此可见,刘勰的风和人物品评中风的含义全不相干。王运熙先生解释刘勰的意思说:“在《风骨》篇一开头,刘勰强调了风的重要地位,指出它是‘化感之本源’,这实际上是说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首先取决于风,即作者的思想、感情、气质等在作品中是否表现得清峻爽朗。它正像人物的风神和书画的神气一样,是能否打动人的首要因素。”(注: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风骨论》,《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第54、55、57、60、60页。)王氏的第一句话是符合刘勰的原意的,但他的第二句话用“正像”二字把刘勰的风和风神、神气拉近,似乎刘氏之风就是风神,这不合刘氏原意。按刘勰的解释,风是作者的思想感情等表现得鲜明的状况,而风神是风度、风姿等事物,两者是扯不到一块去的,刘氏本人也并不想把它们扯到一起。王氏所以这样说,因为他曾说过人物品评中的风指人物的风姿、风神,又认为人物品评、书画理论、文学理论中风骨的内涵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故而要把这两个概念拉近。但事实证明,刘勰的风的释义和传统人物品评中风的含义相去甚远。
再说骨的含义。刘勰的骨的内涵也不同于人物品评用的“骨”。人物品评的骨指人的骨力、骨气、内质,引入文学理论应相当于作品的思想感情力量(风引入文学理论应指作品表现出的风貌)。刘勰认为骨指作品的言语、文辞端直刚健精炼有力(学者们解释说骨是对作品文辞方面的美学要求,或者说是文辞精炼有力的表现),故而刘勰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又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由此我们发现,刘勰释骨,与人物品评中骨为内质的含义也不相同。
再者,在风骨二字的关系上,刘勰的风骨论与传统的人物品评中风骨二者的关系也不相同。前已述及,在人物品评中,风外骨内,骨是决定的因素。在刘氏的理论中,风关乎意气情志,骨关乎言语文辞,风成了决定的因素,二者的位置是风内骨外。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刘勰的风骨论脱离了深厚的文化渊源,和传统的人物品评所用的风骨内涵有着本质的差异,因而不能为古人和今人普遍接受。由于人们已有了对风骨的先入为主的理解,故而今天的改刘派要极力改造它。
二
风与骨这两个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理论,常常是连缀起来使用的。这两个概念在刘勰的理论中存在什么关系,各占什么地位呢?尊刘派认为刘氏的风骨论就是他的文质论,骨与风分别属于文与质。黄侃则就意与辞两方面加以发挥,说:“察前文者,欲求其风骨,不能舍意与辞也;自为文者,欲健其风骨,不能无注意于命意与修辞也。”(《文心雕龙札记》)由于他把命意与修辞对举,有的尊刘派的学者就把风与骨的关系说成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孙耀煜先生说得很明确:“‘风’与‘骨’是情感与语言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属性,也是从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所显示出来的特征。黄侃提出:“风与骨分属两个范畴,是与内容和形式相联系的两个概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对风骨论的研究是一个重要贡献。”(注:孙耀煜:《中国古代文学原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71页。)
改刘派在阐述风骨概念的时候,一般不涉及内容和形式问题,只有少数学者提到它们,如廖仲安、刘国盈二位先生说:“风和骨都是内容的概念。”郭预衡先生说:“‘风’‘骨’都指内容,不指形式。”可见他们并不认为风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我们认为风骨论不是文质论,风与骨的关系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质论从总体上论述文与质的关系,即“文附质”,“质待文”,并不包含具体的价值判断,即要求文是什么样的文,质是什么样的质。刘勰所阐发的风与骨都有特定的规定性,既不能抽象成意与辞的关系,提高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认识,也不具有对应性,认为此风只与此骨相配。因为在文学创作中,一定的内容固然要求一定的形式与之相适应,但某一内容并非只能有一种形式与之配合,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具有不完全的对应性,例如鲜明的情志并非只能以质朴刚健的语言加以表现,也可用其他语言加以表现。反过来说,质朴刚健的语言也并非只为一种情志所用,也能表现其他情志。以唐代诗人李白的诗为例,李白诗的情志可说是骏爽鲜明的,但李白并非只有一种笔墨,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而在刘勰的观点中,风、骨不是泛指,他只要求这一种风,只提倡这一种骨,因而风骨的连缀没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其次,刘勰的风骨论是排斥文采的,也不符合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普遍规律。文采应该包含在语言形式之中,刚健有力的语言也可能同时是有文采的语言,也就是说采可以包容于骨之中。但刘勰的骨的内涵不含有文采,因而为了写出精美的作品,他不得不另外求助于文采,要求风骨和文采结合。在《风骨》篇中,他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风骨乏采”、“采乏风骨”这两句话就表明刘氏的风骨概念是排斥文采的。由此看来,刘勰的所谓文质论,岂不成了风骨加藻采的文质论了?风骨本身已是一质一文,再加一文,就成了“二文一质”的文质论了。黄侃虽是尊刘派,但凭着他的高度的理论素养,也看出了刘勰上述言论的漏洞,故而在“风骨乏采”四个字之后批评道:“骨即指辞,选辞果当,焉有乏采之患乎?”(《札记》)另外,三种鸟的比喻也表明只具有风骨的作品在刘勰的心目中尚不是最优秀的作品,只不过像一只缺乏美丽翎毛的鹰隼,比凤凰还差了一级,他的风骨作为文学批评的术语,只能是个较低档的或者说起码的美学概念。有了风骨还得要采来补充,这算什么样的文质论!刘勰的风骨与人们心目中用作高度评价文学作品的风骨又岂可同日而语!
再次,刘勰的风骨论的概念还存在交叉、分界不清的毛病。刘勰分别确定了风和骨的内涵,但并未指出两者的主从关系,在讨论到风的时候并未联系到骨,在阐发骨的时候也未联系到风。他在《风骨》篇后文讨论风骨或有或无的表现时,也应继续贯彻这种分论的做法,即在讨论无风或有风的表现时不必引入骨,在讨论到无骨或有骨的表现时,也不必引入风。但刘勰并非如此。他说:“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这三句话里,刘勰的风骨概念都混淆不清。例如第一句话是说辞藻繁富,语言华美的毛病,这本是语言不精,文骨未成,和风没有关系,但刘氏把风也带进来了,似乎语言软弱无力也是风不足造成的。第二句话说用字妥贴,语言有力,这本是文辞锤炼成骨的表现,和风也没有关系,刘氏却说它是“风骨之力”。第三句话分析语言无骨的表现,本是由于析辞未能精练,结言未能端直,和风同样没有关系,刘氏却说它的原因是“瘠义”(即文意贫乏),又扯到了风上去,骨似乎又成了意的表征。有的学者为刘勰辩护,说刘氏前文是分论,后文是风骨合论。我们认为此说牵强。如果刘勰的风骨论是文质论的话,按照“文附质”、“质待文”的规律,应先讲清骨附风、风待骨的道理,具体说明没有孤立的刚健有力的文辞,它必须依赖于内容的鲜明有力;鲜明有力的内容也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藉刚健是骨,二者风马牛不相及,《风骨》篇一开篇就细细地分论,到下文讨论语言文词时,再塞进几个“风”字,就算是合论吗?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着,要说刘勰的风骨论有多么强的科学性,我们是实在不敢苟同的。
三
最后,我们再来考察刘勰的风骨论在历史上被认可、被使用的情况。
从刘勰以后,一些理论家和诗人也常使用“风力”、“骨气”、“气骨”、“风骨”等概念来评论文学。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风骨论是一脉相承的,尽管用的字面不完全一样,其涵义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认为不完全如此,历史上不少人虽然也用了“风骨”二字,却在暗暗地改造刘勰的风骨论,注入自己的理解,有的人则提出新的概念以代替刘勰的风骨概念。
首先让我们来看年份略晚于刘勰的钟嵘的风骨论。钟嵘的《诗品》的序和正文中未出现“风骨”一词,只有“风力”、“骨”、“骨气”等词。今天我们很难确定钟嵘是否读过《文心雕龙》以及他是否有意标新立异,但钟嵘确实没有把风骨二字联用。钟嵘在评论玄言诗时说:“建安风力尽矣!”詹锳先生说:“所谓‘建安风力’也就是‘建安风骨’。”(注:詹锳:《齐梁美学的“风骨”论》,《〈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31页。)王运熙先生说:“钟嵘把风骨叫做风力。”(注: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风骨论》,《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第54、55、57、60、60页。)我们认为这个判断不确切。从《诗品》的全部内容看,钟嵘的“风力”不等于刘勰的“风骨”,钟嵘的“风力”只相当于刘勰的“风”(风力),这是因为刘勰已经把风骨析为风力和骨鲠。《风骨》篇的“赞”说:“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按:蔚和严两个动词的含义也表明风力和骨鲠分别指风与骨)所以钟嵘的风力就是刘勰的风力(即风),不等于风骨。钟嵘使用的骨字不是刘勰所云关乎语言文辞的骨,钟氏骨的含义和风、气的意思接近。《诗品》评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的作品说:“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刘桢的诗有气,有骨,有风,超过其文辞,文辞的藻采太少。气、骨、风与文相对,可见钟嵘的骨字的含义是思想品质,和刘勰所谓“析辞必精”的骨不是一回事。再看对建安之杰曹植的评论。《诗品》说他的作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其中骨气与词采对举,可知分指意气情志与语言文辞两个方面。这个骨气即曹植诗的意气,和刘勰的骨也不是一回事。上述两例可见钟嵘的骨、骨气指的是意。总之,钟嵘的风力、骨、骨气都不等于刘勰的风骨,钟嵘的风力、骨气属于文学作品的感情精神方面,与语言文辞无涉。
钟嵘的《诗品序》中谈到诗歌创作,主张运用赋、比、兴三种方法,还要“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钟嵘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这两句话是钟嵘关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主张。对此,王运熙先生解释说:“即以明朗刚健的语言和风格为基干,再用美丽的辞藻加以润色,这与刘勰的风骨与文采相结合的意见是一致的。”(注: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风骨论》,《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第54、55、57、60、60页。)我们认为,这个解释不符合钟嵘原意。因为,第一,钟嵘所云风力与丹采结合不等于明朗刚健的语言与美丽的辞藻相结合,前者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后者是形式与形式的结合,二者怎能相等呢?第二,钟嵘所谓风力与丹采结合,同刘勰所谓风骨与文采的结合是不一致的,因为风力不等于风骨,钟氏所云是严密的科学的表述,刘氏所云出现概念的内涵重叠,在逻辑上是有毛病的(参看第二节)。
据此,我们认为钟嵘的风骨论(实为风力论)与刘勰的风骨论是不相同的;钟嵘只着重强调文学作品的风力(即作品思想感情表现的力度),刘勰兼论风和骨两个因素。钟嵘的风力加丹采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是清晰的,刘勰的风骨加文采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夹缠不清。
刘勰、钟嵘之后有些理论家也用风骨这一概念评论诗文。如北齐祖莹说:“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魏收《祖莹传》引祖莹语,《魏书》卷八十二)宋代严羽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沧浪诗话·诗评》)明代胡应麟说:“宋、齐之末,靡极矣。而袁阳源《白马》、虞子阳《北伐》,大有建安风骨。”(《诗薮·外编》明代费经虞说:“唐司空表圣以一家有一家风骨,乃立二十四品总摄之。”(《雅论·品衡》)他们对风骨的含义都未作解释,上述四句都缺少上下文,我们很难判断他们是否使用了刘勰的定义。这四处“风骨”大体上都可以理解为风格。
另一些诗人、评论家则“骨气”、“气骨”、“风骨”兼用,从其上下文推断,其含义不是刘勰讲的意与辞两方面的特征,而只在情志精神一方面。
先看诗人的用语。唐代杨炯批评唐高宗龙朔初年逶迤颓靡的文风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他认为上官体风行的时代,前代文学优良传统“骨气”和“刚健”都失去了。这篇序文是用骈体写的,骈文喜用对偶句将两个不同事物对举,因而上述“骨气”、“刚健”不指同一事物,如果“刚健”偏重于语言的话,则“骨气”当指作品的意气情志一类事物,不是刘勰所说的“骨”。由此可见,杨炯的“骨气”概念不同于刘勰的风骨含义。稍后的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倡“汉魏风骨”,汉魏风骨的含义同于建安风骨。这一风骨的内涵我们暂时看不出来,但下文陈子昂称赞友人东方虬的诗说:“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我们认为,这个“骨气”指的是情志,因为它是和“音情”对举的。彭庆生先生解释此句说:“骨,指风骨的骨,指作品的思想内容;气,指作品的气势。骨气端翔,指内容健康,气势飞动。《诗品》卷上:‘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注:彭庆生:《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9页。)彭氏对骨的解释不同于刘勰,他又引钟嵘的“骨气奇高”四字作证,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周振甫先生说:“这里讲的‘骨端气翔’,就是刘勰讲的‘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注: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我们翻检各本陈子昂集,见此句都作“骨气端翔”,不作“骨端气翔”,不知周氏何所依据?他把这句的骨讲成刘勰论语言文辞的骨,是不妥的,把气字丢掉也不合适。再者,刘勰、钟嵘等人称赞作家作品的风力时常用“高翔”、“高”等词,如刘勰最理想的作品是“藻耀而高翔”(“藻耀”即文采辉耀,“高翔”即风力高飞),钟嵘称曹植诗“骨气奇高”,都用了“高”或“翔”陈子昂正用“翔”字,则陈子昂说的“骨气端翔”,是指风力刚正高昂,而非语言质朴精练。许多学者都认为“骨气”是“风骨”的同义语,则陈子昂使用的风骨一词也不同于刘勰的风骨。他和钟嵘、杨炯一样,都改变了刘勰的骨的含义。
再看评论家使用的情况,唐代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常用“风骨”、“气骨”赞美一些诗人的诗篇,如评高适说:“多胸臆话,兼有气骨。”评崔颢说:“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评薛据说:“(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用于前两个人的“气骨”、“风骨”的含义,因为没有解释,不容易看出来,评薛据时就可以看出来了。骨鲠有气魄是形容其人品的,其文品也是骨鲠有气的,这里骨和气意思相近,由此可知殷璠论诗之骨鲠不同于刘勰专论语言文辞之骨或骨鲠。同一个人在同样的场合使用气骨、风骨、骨鲠这些概念的时候,如果不加特别的说明,其含义应该是大体一致的。据此,我们认为殷璠的风骨论也不同于刘勰的风骨论。
唐以后的评论家也继续使用风骨、气骨等概念评论诗文。元代陈绎评论六朝文学说:“六朝文气报衰缓,唯刘越石,鲍明远有西汉气骨。”(《诗谱》,《历代诗话续编》本)说刘琨、鲍照诗有气骨,是就六朝文气而言的,可知这气骨属于气与风的范畴,不指语言文辞。明代胡应麟赞美曹植的诗说:“才藻宏富,骨气雄高。”(《诗薮》内编卷二)与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是一样的,骨气都指意气、风力。他评孔融的诗说:“词理宏达,气骨苍然。”(《诗薮》外编卷一)这与曹植评孔融“体气高妙”是一致的,气骨苍然是说意气很盛,气骨即骨气,骨也不指语言文辞。再看明代胡震亨的观点,他评高适说:“高常侍适性拓落,不拘小节,其诗多胸臆语,兼有风骨。”“高常侍气骨朗然,词峰峻上,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唐音癸签》卷五)他从人品论及诗品,从人的风度论及诗的特色,“气骨”与“词峰”对举,可知胡氏的气骨、风骨指作品的意气情志,与语言文辞无涉。胡氏还评论了岑参和刘禹锡,他评岑说:“岑嘉州参以风骨为主,故体裁峻整,语多造奇。”(《唐音癸签》卷五)评刘说:“刘禹锡诗以意为主,有气骨。”(《唐音癸签》卷七)他以意释气骨,气骨即风骨,指作品的意气情志,虽也提到了“语”,但这“语多造奇”是作品总体上有了风骨的结果,并非如刘勰专用以释骨。由此我们发现陈绎、胡应麟、胡震亨等人使用的风骨概念与刘勰的解释不同,他们的骨都属于意的范畴,没有一个人把骨纳入语言文辞的范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涉及风骨论的材料很多,我们难以尽举,但从上述著名的理论家、诗人使用风骨概念的情况看,至少可以说刘勰的风骨论在历史上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他们在使用风骨概念的时候在悄悄改造刘勰的风骨论的内涵,改造的焦点集中在刘氏的骨上,把它的含义从专指语言文辞方面拉向了意气情志的范畴。
一些评注家也在改造刘勰的风骨论。明代学者杨慎说:“诗有格有调,格犹骨也,调犹风也。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也,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两致矣。”(注:杨慎、曹学佺、钟惺合评《文心雕龙》,《合刻五家言文心雕龙文言本》。)从杨氏的比喻可以看出他的风骨论,骨与风的关系是内外关系,骨是文学作品的内质,风是其外现。正如诗有格调,格是内在的品质,犹如骨,风是表现于外的风度,犹如风。又如美女,美是美的本身,犹如骨,艳是美的鲜明动人的外现,犹如风(这一解释近于魏晋人物品评中风骨的含义)。杨慎对风骨涵义的解释是否正确,且不深论。可以看出,杨慎不同意刘勰的定义,而加以彻底的改造,代之以自己的理解。
与杨慎合评《文心雕龙》的曹学佺说:“风骨二字虽是分重,但毕竟以风为主,风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气属风也。”看来,他基本上采用刘勰的概念,但想舍去刘勰的骨字,而以风、气代替刘氏的风骨,原因是他不满刘氏对骨的定义。
清代的黄叔琳说:“气是风骨之本”。(注:黄叔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芸香堂刻本。)黄氏的用意和曹氏相同,也是基本上采用刘勰的概念,并用气代替风骨,淡化刘氏骨的内涵。而纪昀显得更干脆,直说:“气即风骨,更无本末。”曹、黄、纪三位学者也在改造刘勰的风骨论。
清代一位诗评家李重华提出神气说:“曰:诗以风骨为要,何以不论?曰:风含于神,骨备于气,知神气即风骨在其中。”(注:《贞一斋诗说》,《清诗话》本。)明知有风骨一词,却不用,而代之以神气,看来他想以神气论代换刘勰的风骨论。何以如此?大概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基于对刘勰风骨论的不满吧。刘勰是古代一位优秀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心雕龙》影响很大,他的风骨论作为“龙”学中的一个概念当然可以继续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刘勰的风骨论”,但“刘勰的风骨论”并不等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已经使用了一千多年的“风骨”概念。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已使用了一千多年的“风骨”概念,我们认为应该重新解释。我们建议参照它在魏晋人物品评中的原始含义和它在文学批评史上被理解使用的情况作这样的界定:骨指文学作品中由强烈的思想感情构成的坚实的精神力量,风指这种力量表现于外部的鲜明的特色和气势。风骨二字合言之可算是诸多风格中的一种鲜明有力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