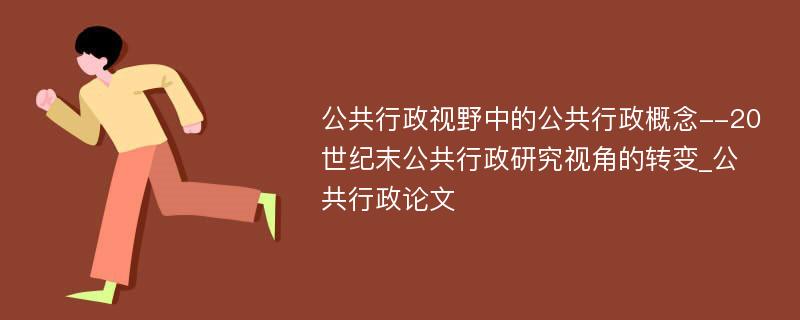
公共性视角下的公共行政概念——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研究视角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行政论文,后期论文,概念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3)03-0009-09
公共行政的概念中包含着“公共”一词,表面看来,它天然地就是用来定义行政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行政”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心。大致是在“二战”之后,学者们似乎忽然发现了公共行政的“公共”内涵,使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成了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一种学术倾向。尤其是196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公共行政运动”,更是对公共行政的“公共”内涵作出了一种独特的诠释,为我们理解公共行政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尽管新公共行政运动很快就沉寂了下去,但这次运动的出现却标志着“公共性”的视角在公共行政研究中获得了应有的话语地位。显然,对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探讨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新公共行政运动的衰落并没有造成公共行政规范研究的衰落,相反,随着一种抽象的明诺布鲁克观点的破裂,在研究途径多元化的条件下,公共行政的规范研究反而走向了繁荣,尤其是“公共性”的视角,在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正如哈蒙所说的,“作为一个社会实践的范畴,由于公共行政基本所关注的是承担或有助于负有公共目的以及对于国家意志负有责任的机构之社会实践活动,因为这样的特质,所以或多或少有别于其他社会实践的范畴。不管是在事实或原则上,‘公共性’(publicness)这个观念涵盖的是那些负有责任的机制或者其他达致公共同意的方法,而这些机制或方法乃决定了这些实践活动的有效性或合法性。”①因此,无论是对公共行政的实践还是研究来说,“公共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公民主义兴起中的公共行政概念
今天看来,新公共行政运动的最大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重视公共行政“公共”方面的要求,但在如何定义“公共”一词的问题上,不仅新公共行政运动,而且整个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的学者们,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无法明确定义“公共”一词的内涵,才使得公共行政的概念一直存在着多义的理解,能够转化为实践的总是这个概念中的一部分内容。甚至,随着每个人都开始人云亦云地谈论公共,毫无外延边界地使用“公共性”概念,“今天,‘公共’一词的崇高含义已经被稀释得仅仅意味着一个政治单元界限内的享乐主义的、没有差别的‘每个人’了。不幸的是,当那一崇高的含义受到抛弃的时候,公共行政作为民主的一个必要而独特部分的存在理由也就失去了。不同于艺术品,行政并不是一件为了自己而存在和仅仅去做就够了的事情,它需要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并因此而得到证明。所以,在一个民主制度中,‘公共’应当指涉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其公民权利和义务得到了所有人的明确理解。由于一个民主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理由是实现它所宣称的价值,‘公共’行政就是实现这些价值的一种必要(但不充分)的和独特的行政形式”②。根据这种意见,公共的内涵应当被定义为公民,因而,强调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也就等于强调公共行政对公民的责任,即促进公民整体的利益和价值。只有这样,公共行政才能成为使民主得以实现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公共概念的这一分析,哈特(David K.Hart)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关于公共行政官员作为公民而不是民选官员之代表的主张作出了理论上的证明,特别是包括他这篇论文在内的名为“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的特辑在《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上的推出,标志着“公民主义”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正式兴起。
不过,弗雷德里克森则认为,公民主义本是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一种传统视角,比如,锡拉丘兹大学的麦克斯韦尔学院全名叫做“Maxwell Graduate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南加州大学的公共行政学院原名也是“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体现了早期公共行政学者对公民权利、公民精神等问题的关注。然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行政原则”成了学者们的口头禅;40年代,“效率”与“理性决策”等主题又占据了学术讨论的中心舞台,公民主义就此失落了。“尽管这些问题对于从事公共行政实践与研究的人是至关重要的,但人们对于公民精神和公民在民主政府中的角色却没有多少兴趣。关于民主理论的问题和政府伦理的问题,更是很少被人们提及。到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政府变得极其庞大。与大多数制度一样,公共行政正在经历一场身份危机,公民们对我们社会中大多数制度的支持,开始不断下降。公民主义(civism)在公共行政中消失了。公民主义的复兴,将为公共行政的实践与研究提供其必要的支持,这不仅是一个公共行政发现其身份的问题,而且也是为了变得更有效率。”③
在弗雷德里克森看来,复兴公民主义首先是出于重塑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要求:“恢复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公民对政府的支持,是需要政府对公民的关切的,政府应当对公民的需要作出回应。就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教育而言,这意味着重新强调这一领域的公共方面以及民主理论的基本问题。如果公共行政希望变得有效率,那么将其付诸实践的人就必须更加熟悉代表性以及直接性的民主、公民参与、正义原则和个人自由原则等问题”④。同时,复兴公民主义也是出于回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公民们需要的是变革,而且是根本性的变革。公共机构正在面临的恰是与他们现在所做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了满足变革的需求,我们对机构和人员进行了削减;由于入学率的下降,我们对教师队伍进行了削减,然而,我们却更难判定公民们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削减是一种短期策略,我们所需的恰恰是一种长期变革。公共行政需要强化其创新能力和开发替代方案的能力。能够带来创新、变革与回应性的,在我看来,正是一种‘新公民主义’(new civism)。未来的高效率的公共行政应当是属于紧密联系于公民精神、公民整体以及直接与公民打交道的公共官员的效能”⑤。最为根本的,复兴公民主义将是重建政治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对于公民精神、正义和自由的共同承诺是存在于整个共同体之中的。然而,当代美国却出现了一种共同体感的明显失落。所以,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观念和理论问题就是共同体感的重建。我们必须发现确立共识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既运用了现代技术,又能够保证人们完整而直接地参与到政策过程之中。没有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感,公共行政将继续构成对公民的威胁,而且,也会继续成为民选官员的替罪羊”⑥。在弗雷德里克森看来,根据以上这些理由,复兴公民主义,或者说倡导“新公民主义”,是一项势在必行的事业。
作为新公共行政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雷德里克森在公民主义中读出的是民主,因而他认为复兴公共行政的公民主义在实质上正是要根据民主的要求来重建公共行政。具体地说,民主的要求在公共行政这里所应体现的就是直接性、正义与自由。“民主过程的直接性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基本问题”;“民主理论的第二大观念是正义。……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通过它们的决策过程而与什么是和什么不是正义的问题打着日常性的交道”;“自由是民主理论中与公共行政有着重要联系的第三大观念。当然,宪法中对自由有着许多规定——表达、宗教、出版等等。就公共行政官员而言,自由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政府有责任保障社会中每一个体的自由;其次,更重要的是,政府有责任确保政府本身不会侵犯这些自由。”⑦从这些方面看,根据公民主义建构起来的公共行政实际上是能够承担起政治部门的许多职能的。但是,仅仅满足这些条件,还不能够判定公共行政已经转化为了民主行政。如果说民主行政作为一种理念是值得提倡的话,是不能够满足于在行政过程中推动民主参与和实现行政官员与公民的直接互动的,还必须看公共行政是否会威胁到政治过程中的民主。因为,公共行政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与政治系统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只有当民主行政与政治民主有着相互呼应和相互支持的功能时,才有着值得倡导的意义。弗雷德里克森看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对于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民主过程的直接参与难道不会侵蚀选举民主的过程吗?如果公共行政官员对于他或者她的特权与责任及其与民选官员的特权与责任之间的边界并不敏感的话,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将是肯定的;如果公共行政官员一心向往的是自我实现或者权力的话,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公共行政官员只是将民选官员、公民以及公务员都包括在内的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且这一过程不受公务员的关切、需要和利益支配,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毫无疑问是否定的”⑧。也就是说,民主并不仅仅反映在选举过程中,而且在决策过程中也有着根本性的价值。然而,从现实情况看,正是因为缺乏对当选官员行为的有效约束,致使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不民主甚至反民主的问题。也就是说,民主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民选官员的选择上,而且要落实到民主官员的决策过程中去,只有这样,民主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如果把民主简单地定义为对民选官员的选择,那么,当选出的官员去开展行动、去制定政策时,却完全可能背离民主的原则。所以,民主行政所要求的是让决策过程向与公民有着日常性接触的行政官员开放,以对民选官员形成某种制衡,并使公民的诉求与利益要求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当然,即使参与到了决策过程之中,行政官员与民选官员间也仍然有着分工和职权上的差异,并不能取代民意代表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所以,需要鼓励公共行政官员与公民的直接接触和互动,切实保障公民的利益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得到代表。只有当决策过程中充分地反映了公民的诉求,才能使行政具有民主的属性。只有当行政成为民主的,只有在决策的过程中使公民真正得到了代表,民主才有了彻底性。可见,民主行政不仅不是对选举过程中政治民主的威胁,反而还是对政治民主的发展与增强。
在1988年召开的第二次明诺布鲁克会议上,弗雷德里克森关于公民主义的倡议得到了文特里斯(Curtis Ventriss)等人的积极响应。文特里斯认为,“如果公共行政认真对待它所运行于其中的与之相互依赖的环境,那么,其实践就不再能够舒适地局限于摩天大厦般的组织,而必须以某种方式扩散到集体宿舍之中。在集体宿舍中,人们对于相互依赖才真正有着直接感受。简言之,公共行政实践必须进一步扩展到那些在个体与国家之间起着调解作用的公民和志愿团体之中。通过这样做,公民团体就能够被转化成鼓励公民参与和责任的活生生的民主实验室。作为培育公民精神的潜在教育手段,公民团体可以成为重要的公共论坛(在公共管理者的帮助下),可以促进关于公共问题的相互关联性质以及公共互赖性对政治体之影响的批判性讨论”⑨。只有这样,公共行政的实践与研究才能摆脱里根时代“经济学化”了的公共哲学的控制,才能够根据公共行政的独特性而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公共哲学——一种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哲学。在弗雷德里克森与文特里斯等人的倡导下,公民主义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关注,继起的讨论发展成了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研究中一股引人注目的思潮,并成为了90年代兴起的参与治理浪潮的重要理论依据。尽管在近代早期的政治生活中已经生成了公民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政治建构基本上是建立在公民主义的精神之上的,但是,自公共行政产生以来,公民主义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甚至可以说公共行政包含着一种反公民主义的内涵。公民主义概念的提出以及要求把公民主义的精神贯彻到公共行政之中来,是应当归功于新公共行政运动的,正是弗雷德里克森等人为之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行政伦理研究中的公共行政概念
如果说“行政”的概念中包含着“价值中立”的内涵,那么,“公共”一词却又必然是行政价值的体现。因而,公共行政绝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性的概念,相反,“公共行政必须被理解为并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行政形式,必须明确地反映出这个国家建立于其上、对公民至关重要的自然法价值。‘公共’行政必须被视为一种‘道德努力’的形式。”⑩也就是说,从公共性的视角看,公共行政是一种具有道德内容的社会治理行动,因而,关于公共行政的研究也必须关注伦理问题,必须重视公共行政的道德层面。尤其是在1970年代初的“水门”事件后,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成了公众关注的核心问题。于是,就在公民主义兴起的同时,行政伦理也发展成了公共行政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甚至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伦理运动。“虽然社论作家和国会委员会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水门和CIA事件上转移开了,但在学术界,这些事件则因可以被称为‘政府伦理’的运动而存续了下来。本科生和研究生现在被给予了(并经常被要求选修)‘应用伦理学’的课程;建立了研究中心(纽约的哈斯廷中心,马里兰的哲学与公共政策中心);组织了会议;创办了杂志(《哲学与公共事务》);设立了资助;写作了博士论文。哲学、政治科学、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的教授们,全都变成了这一运动的主力军,在高校入学率不断下降和学术部门面临财政困难的时期,伦理学则是一桩大生意。”(11)
不过,尽管伦理教育成了“一桩大生意”,但在许多学者看来,当时大学中的公共行政学院却没能做好这桩“生意”。比如,利拉(Mark T.Lilla)就指出,“今天为公共服务做准备的学生没有接受到可以被称为道德教育——它类似于劝导高洁品性的宗教教育——的教育;他们接受的是一种相当奇特的哲学探讨,它允许他们为他们的行动找出老练的借口,而没有为他们做好在一个民主制度中负责任地行动的准备。道德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分析方法,通过将抽象的伦理推理引入公共行政研究,这场伦理运动帮助建立起了一个道德真空,而不是填满它。……通过对哲学研究和公共行政实践的目的进行混淆与折中,这场伦理运动只能被指望制造出新一代的诡辩家,而不是复活一种道德的公共服务传统”(12)。也就是说,当时的行政伦理教学过于抽象,过于注重分析,因而忽略了行政伦理的现实关怀,忽略了公共行政的政治语境。“因此,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学院中,重点必须首先落实在关于民主的道德教育上,而不是像在哲学系中学习到的那种道德哲学。当前所理解的应用伦理学事实上在教导未来的公共官员如何用崇高的理由为他们的行动辩护,而没有教导他们是何种义务与德性构成了民主政府中的个人道德生活,更没有让他们把这种理解转变成习性。显而易见,在一个学习公共政策的学生仅仅拥有形式分析的技能的时代,在一个本科学校对于民主政府的态度充其量是含糊不定的时代,关于民主的道德教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13)
利拉的观点在罗尔那里得到了共鸣。罗尔认为,当时的行政伦理教育主要来自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和人际关系学派中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而这两大来源都是不适用于公共行政的。就前者来说,要读懂罗尔斯,必须具备康德哲学的基础知识,而要读懂康德,首先又得读懂休谟,这显然不是公共行政专业的学生所需要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多余的。因此,“满足于在伦理课程中获得对政治哲学的一知半解,对于学生或哲学本身,都是不公平的。出于这一理由,我们必须到其他地方寻找伦理课程的基础”(14)。就后者而言,“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中,重要的是个体的人,而不是他如何被雇佣的。由于我们的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某种(公共)雇佣的裁量权而来的结果,所以,基于个体的人的规范性体系是不符合我们的目的的”(15)。也就是说,人本主义心理学无法解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区别,因而无法突出政府伦理的独特性,所以,也就不可能符合公共行政教育的需要。有鉴于此,罗尔提出,“作为对政治哲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种替代,我建议,既然公共行政的学生渴求特定政体(regime)中官僚机构的领导职位,那就应该了解政体的价值,并把这种政体价值作为伦理反思的出发点”(16)。也就是说,一个特定政体的政体价值应当成为该政体中公共行政官员从事行政活动的基本伦理原则。
罗尔进一步强调说,“‘政体价值’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所有官僚保持一致。不存在所有官僚都必须采纳的、对美国经验唯一‘权威’的解释。重要的是让他们接受这样一种道德义务,使他们保持与美国人民价值的接触。而如何解释这些价值,则是官僚自己才能做出的决策。……官僚,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如果打算保持其道德完整性,必须忠于其最内在的信念。可喜的是,‘政体价值’将使官僚有能力完善其内在政治信念的内容。在坚持官僚‘遵从良心’的义务时,我并不是在建议他仅仅‘做他自己的事情’。不幸的是,在流行的宣教中,这两组表达已经混在了一起。我希望我的方法将提供给官僚一种被启迪的良心,它将引导他去与他所服务的政治社会开展对话,并严肃地思考其价值。在使自己服从于这种约束之后,他将能够自由地遵从其良心”(17)。在这里,罗尔遇到了伦理学中的一大难题,即外部规范与内部动机间的协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罗尔的解决方案是宣誓仪式。他认为,通过宣誓的行为,公共行政官员做出了认同于政体价值的选择,因而,也就把政体价值变成了他的“被启迪的良心”。进而,当他“遵从良心”而行动的时候,就会做出有利于维护和促进政体价值的行为选择,就能够实现外部规范与内部动机的统一,并能够实现自身行为的道德化,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其所服务的政治社会的需要。这样的话,公共行政就变成了实现政体价值的工具,而不再是仅仅服务于效率目标。
库珀也认为,“只是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公共行政才是一种工具性的实践。它存在的理由在于,为诸如公共卫生、计划、会计、执法与教育等其他实践的繁荣而创造和维持组织的以及其他的框架。支持这些实践的理由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民主的公民集体直接或通过他们的代表决定的、符合其集体利益的东西。因此,公共行政不应在‘古典范式’——它假设了政治与行政的分离——的意义上被理解成工具性的。公共行政的实践所涉及的远不仅仅是从属于政客的行政角色,功能理性的支配也不意味着它是行政官员唯一合法的思维方式。相反,正是公共行政官员作为公民受托者的角色,产生了与践行内含于这一角色之中的信任有关的某些内在的善与德性”(18)。具体地说,“对行为与政策最根本的检验应当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公民整体利益的实现。实现组织或公共行政实践者的利益应当成为第二位的考虑。除非一项行动首先产生了显著的公共利益,否则,即使它增强了组织或促进了实践者的利益,也不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19)。也就是说,公共行政应当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行政与私营部门管理的区别在于:政府有义务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从道德和常识的角度来看,公共行政必须服务于‘更崇高的目的’。即使社会大众对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迭有争议,但是,其作为公共行政管理者的职责所在和其行为的指南,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他们的行为未能符合公共利益要求时,便可能受到把部门利益或个人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批评。公共行政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确保公共行政管理者能够代表并回应民众利益。否则民主制度便可能无以为继。”(20)
可以看到,美国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伦理探讨与公民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在政治民主的大前提下,它们所关注的都是民主行政实现的可能性。库珀就是根据公民权的概念来理解行政责任的,他认为,“在现代民主行政体制中,恢复并深化公民权所包含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体现民主的公民权所包含的意义和现实性日趋衰微,民主行政就不可能实现。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应在理解公民责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21)。进一步地说,“公共行政人员的这种综合受托责任表明: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何时,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公共雇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这是最基本类型的伦理关怀问题”(22)。由此看来,作为一场学术运动的行政伦理研究与公民主义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它们都突出了公共行政对于公民的责任,都要求公共行政促进公民整体以及由这一整体所构成的特定政体价值的实现。在这两种学术流派中,“公共”都是从公民的角度而得到理解的,公共行政相对于公民的责任,就是其公共性的源泉所在。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的公共行政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旗帜下,公共部门掀起了一场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基本内容的政府改革运动,这一运动促进了公共管理概念在公共领域中的再度流行,从而使公共行政概念的运用环境变得严重恶化。在这场后来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运动的冲击下,公共行政变成了低效与浪费的代名词,自“水门”事件以来本就不断下滑的社会形象更是一落千丈。然而,进入90年代中期,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这一运动的支持者们也开始反思市场化、私有化的局限性等问题,并对公共行政学者们所强调的民主等规范性价值进行重新认识。在此背景下,公共行政学者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并在公共行政领域中掀起了一场反新公共管理的学术运动,为基于公共性的公共行政概念进行正名。在某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所发生的一场学术运动恰恰是一场为公共行政正名的运动。
作为一场崇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公共”从公共行政的概念中剥离了出来,使公共行政重新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实践。尽管它也自称“公共”管理,但这里的公共却不是以公众、公民为内容的公共,反而还是以市场为基本内容的。因而,新公共管理实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管理,当它被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的时候,显然对公共行政的概念作了一种市场化的改造。哈克(M.Shamsul Haque)认为,这种市场化的理解是错误的,“如果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是建立在以市场为中心的假定基础上(正如公共选择视角所坚持的)的,那么,每当市场考量占据了优势(正如近来的私有化运动所取得的那样),这一领域就很容易被迫强化用市场规范替代公共规范,尽管它将导向更严重的规范混淆”(23)。弗雷德里克森也认为,“在当代公共行政理论中,其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就是所谓的公共选择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倡导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主张最低限度的政府,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人们进行成本和利益的竞争制定规则。这种理论倡导的是极其简便易行的运算,这是方法论专家们的强项。运用电脑、合适的软件和数据,分析者就可以计算出资源的最佳配置方案。这种理论把公共行政的作用降低为只是作决策,即从最小限度的政治接受度出发,计算个人成本和利益的分配。除了日复一日的日常性工作(毕竟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之外,这样的公共行政完全丧失了目的”(24)。
如果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所指的不是市场,那么,公共行政中的“公共”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弗雷德里克森的回答是,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具有四大要件,分别是宪法、公民精神、回应性与爱心:“公共行政的公共的一般理论的第一个要件是,它必须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人民主权原则、代议制政府原则、权利法案中的公民权利、程序性正当的法律程序、分权制衡,以及联邦宪法和州宪法中的许多规定,都是这种理论的基础,这种基础是稳固的、不可动摇的。”“公共行政的公共的一般理论的第二个要件是,这种理论必须建立在得到强化了的公民精神的理念的基础上;在有些地方,人们把这种理论一直称为‘品德高尚的公民’理论。人们认为,一个好政府必须有一群它所代表的好公民。得到强化了的公民精神的观念应该成为一种公共行政的承诺,这是恰当的。”“公共的一般理论的第三个要件是发展和维持这样一种制度和程序,它能够听到集体的和非集体的公共的利益要求,并能够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回应。”“公共的一般理论的第四个要件是这种理论必须建立在乐善好施与爱心的基础之上。乐善好施,或者对他人的爱心,是关键。”(25)也就是说,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公共行政必须以宪法原则为基础,宪法原则有助于公民精神的生成和培育,能够及时回应公民的需要,并且满怀爱心地对待其每一位公民。弗雷德里克森把这些要件概括为“公共行政的精神”,认为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公共行政就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公共”行政。
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导向也就是顾客导向,因而,反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学者们在批判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公共概念的市场化理解时,也对其顾客导向表达了反对。登哈特认为,“……与政府互动的并不简单地是顾客,而是公民。……与政府进行直接交易——例如,购买一张彩票——的人的确可以被视为顾客。然而,从政府那里接受一种职业服务——例如,教育——的人则可以更恰当地被称之为当事人。当然,我们也是政府的臣民——我们要纳税,要遵守规制,并且要遵守法律。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公民并且政府提供的大部分服务似乎都属于这一范畴”(26)。在这里,登哈特重申了公民主义的立场,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对民主价值观的关注在我们思考治理系统方面应该居于首要位置。尽管诸如效率和生产积极性这样的价值观不应该被丢弃,但是它们却应该被置于由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构成的更大环境中”(27)。所以,登哈特强调,在公共行政中,“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到公共服务不是一个经济思维的产物,而是一个政治思维的产物。那意味着改进服务的问题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顾客’的需要,而且还要关注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情况。从根本上说,在新公共服务中,提供服务是拓宽公共参与和扩大民主公民权的第一步”(28)。在此意义上,90年代以来的反新公共管理运动可以被看做是80年代兴起的公民主义的一种发展,其基本内核是要强调公共行政在维护公民权利与鼓励公民参与上的责任。总之,反新公共管理运动实际上应当被定位为一场参与治理运动,它是根据公民权的要义而要求参与社会治理的运动。
参与治理运动在进入21世纪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场运动的反对对象也从新公共管理运动扩展到了整个现代公共行政。全钟燮看到,“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行政管理思路适应于一种稳定的组织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服务和日常运作不需要太多的创新;在这种环境中,民众的价值和需求应该保持稳定;在这种环境中,组织对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顾客、技术和经济具有可预测性。但是,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如此平静。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社会现象不可能保持如此稳定,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持续变迁不断地将新的价值观、新的思想意涵、新的结构和新的网络引入。因此,直面后工业化社会动荡、不断演进的社会环境是每一个组织不可逃避的任务。环境、组织、信息技术和民众价值观的复杂性迫切需要行政管理者通过与民众的互动、对话和信息分享,促成新的理解和思维方式,促成与民众的广泛合作”(29)。全钟燮将公共行政与民众的互动看作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认为它是通过向社会开放而接受社会建构的过程。这与传统的行政建构或政治建构不同,所强调的是公共行政与外部公众的关系。在全钟燮看来,“公共行政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同时,它也通过解决社会中今天和未来的问题来影响社会。公共行政的现实是由客观化的社会因素以及行政管理者的主观行为来决定的。公共行政存在于社会世界(也就是公共的)的背景中:它不是社会中一个孤立的实体。一个社会环境能改变行政管理者思维和计划的方向,同时,行政管理者根据他们的知觉、知识和体验解释着社会环境。通过与环境和公民的互动,行政管理者建构了社会环境的意义。因此,公共行政是一个正在进行中并存在于社会、制度、行政知识和个体之间的辩证发展过程”(30)。根据这一公共行政的建构思路,通过鼓励公民参与,公共行政不仅得到了社会的建构,而且也参与到了对于社会的建构之中,因而,公共行政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真正的互动。正是在这种互动的基础上,公共行政才成为真正“公共”的行政——一种为“公共”所有、在“公共”之中、为“公共”服务并不断重塑着“公共”的行政。
随着参与治理浪潮的出现,公民主义与行政伦理的发展在公共领域中汇流到了一起,共同增益于公共行政概念的公共性内涵。根据学者们的看法,它们在公共行政中鼓励了公民参与的追求,这既是对公民权的承认,也同时成了行政官员的道德义务实现的途径。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民权的实现是一种外在要求,而行政官员的道德义务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当公民权与行政官员的道德义务结合到了一起,就转化为了鼓励公民参与的行动。在公民对公共行政过程的参与中,公共行政才真正成为“公共”的行政,公共行政概念中“公共”方面的价值才真正地凸显了出来。在今天,参与治理正在成为一场方兴未艾的运动,而在学术史上看,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公民主义和行政伦理研究的。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也同时是后工业化的起点,那么,公共行政学术史上的公民主义和行政伦理研究的意义可能是具有历史性的。虽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实的要求以及对时代的回应却赋予了这两场同时发生的运动以解决后工业时代公共行政重建的内涵。这是值得关注的历史性事件。
注释:
①Michael M.Harmon著,《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吴琼恩、陈秋杏、张世杰译,初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页。
②⑩David K.Hart,"The Virtuous Citizen,the Honorable Bureaucrat,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44,Special Issue:Citizenship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r.,1984),pp.111-120.
③④⑤⑥⑦⑧H.George Frederickson,"The Recovery of Civism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42,No.6 (Nov.-Dec.,1982),pp.501-508.
⑨Curtis Ventriss,"Toward a Public Philosoph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A Civic Perspective of the Publ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20 (4-5),1997,pp.1041-1069.
(11)(12)(13)Mark T.Lilla,"Ethos,Ethics,and Public Service," Public Interest,No.63,(Spr.,1981),pp.3-17.
(14)(15)(16)(17)John A.Rohr,"The Study of Ethics in the P.A.Curriculum,"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36,No.4 (Jul.-Aug.,1976),pp.398-406.
(18)(19)Terry L.Cooper,"Hierarchy,Virtue,and the Practi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A Perspective for Normative Eth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47,No.4 (Jul.-Aug.,1987),pp.320-328.
(20)[美]罗森布鲁姆、[美]克拉夫丘特:《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第五版),张成福等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1)(22)[美]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张秀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7页。
(23)M.Shamsul Haque,"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Current Epoch of Privatization," Administration & Society,Vol.27,No.4 (November,1996) ,pp.510-536.
(24)(25)[美]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9-42页。
(26)(27)(28)[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68、61页。
(29)(30)[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孙柏瑛、张钢、黎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