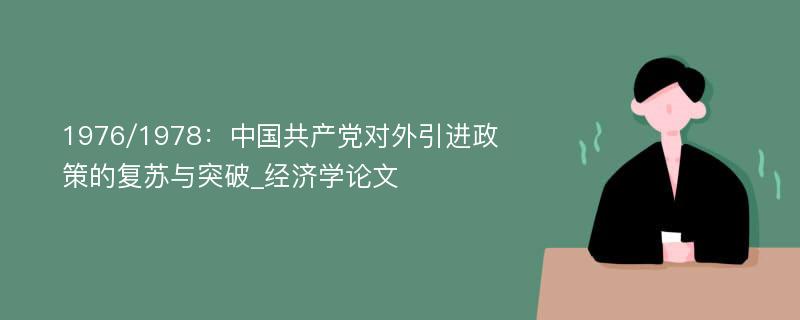
1976~1978:中共对外引进政策的恢复与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7)02-0032-06
“文革”结束以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1976-1978两年徘徊时期,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
一、重新恢复引进资本主义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
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是中共的一贯主张。“文革”期间,因“左”的思想和林彪、“四人帮”集团的干扰破坏,使这一正确主张未能得到顺利贯彻。“文革”结束以后,中共重新恢复并确立了这一思想主张。
1976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关于引进外国技术设备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的观点,肯定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必要性,“那种认为凡是引进先进技术就是‘洋奴哲学’,就是‘爬行主义’,实际上是主张‘闭关自守’,这是对人类文明史的愚妄无知,是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恶意歪曲”。在此基础上,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了引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意见,并形成《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提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洋为中用,这样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善于学习前人的好经验,吸取外国的长处,这是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因素。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什么都要从头摸索起,那就会放慢我们一些工业技术的发展,那也是爬行主义。”① 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同意了此汇报提纲。很快,中央领导层就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和技术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达成共识。
1977年7月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今后8年引进技术和设备的计划。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今后8年,除抓紧把1973年批准的43亿美元进口方案中的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其中,支农工业3亿8千万美元,包括以粉煤和重油为原料的两套大型化肥装置,以天然气或裂解尾气为原料的两套化肥关键设备;轻工4亿美元,包括3套大型石油化工设备,4套化纤设备,2套合成革装置,3套洗衣粉原料装置;石油工业13亿美元,包括地震勘探船,数字地震仪,以及资料处理系统等勘探设备;煤炭工业10亿美元,包括1套年产1000万吨规模的露天煤矿成套设备,2套年产400万吨规模的矿井和洗煤厂的主要设备,2套年洗煤300万到400万吨的洗煤厂关键设备;电力工业5亿美元,包括1套60万或90万千瓦的原子能电站,大型水、火电施工机械。此外,冶金工业7亿美元,化学工业6.2亿美元,机械工业3亿美元,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5亿美元。
1977年12月全国计划会议形成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指出:中国的工业技术非常落后,很多方面基本上还是苏联四五十年代的东西,已经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断地提高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水平。同时,还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在今后5~8年内,要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时机,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运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把学习和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
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努力学习国内和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决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②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的纲要》,对引进规模作了具体的规定。接下来,7~9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和9月份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都强调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为了做好新技术的引进工作,1978年5月,国务院成立了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担任组长,副组长由当时国家计委的副主任顾明担任。小组的任务主要是统筹提出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引进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有关引进的方针、政策和建议;组织引进计划的实施,进行督促检查,总结交流这方面的经验;组织有关方面研究、消化和发展引进的新技术等。另外,完善相关引进法规,使引进工作有根据、有保证。1978年9月召开了全国进口成套设备检验工作会议,指出了目前进口成套设备检验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以后的引进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要求。根据这次会议的情况报告,国务院通过了《进口成套设备检验工作的试行规定》,强调了进口设备检验工作很重要,“是关系到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事。做好这项工作,对于维护国家权益,监督外商履约,严防帝修反的破坏捣乱和外国资本家的投机诈骗,以确保进口设备高质量及时建成投产,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③ 这为有关部门加强领导,落实措施,密切配合,切实把进口成套设备检验工作抓好提供了法律规定,有力地保证了引进工作的顺利进行。
由于国家领导人对引进工作的大力支持和为大规模引进所作的一系列积极准备工作,在1978年的引进高潮中,一年中同国外签订了22个重点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1978年已签约部分为78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1978年一年中,引进已经签约金额相当于前5年(1973~1977)成交总额的两倍,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总额的89.2%④。
重新恢复确立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的思想政策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是中共的一贯主张,只是“文革”期间因“左”的思想和林彪、“四人帮”集团的干扰破坏,使这一正确主张未能得到顺利的贯彻,“文革”结束后,极“左”思潮得到遏制,重新恢复确立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的思想政策理所当然。二是因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要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当时情况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文革”结束以后,中共领导层开始走出国门去了解外国发展情况,并在1978年前后掀起了出国考察的热潮。这些考察团作为探索对外开放国策的先导部队,被人们称为共和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对外开放的“侦察兵”。这些出访不但改善了我国的对外关系,而且还使中共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了比较直接和全面的了解。其中感受比较强烈的,就是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三是中央领导层对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的重视。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就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的谈话中提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还说到“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⑤ 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又指出:“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⑥ 此外,李先念、陈云等也非常重视引进工作,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提出“学会同外国资本家打交道”,“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等口号,充满着改革开放思想。
正是在上述因素推动下,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确立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二、突破“两个不允许”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的外汇。根据1977年7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的8年引进计划,共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建投资需要400亿元人民币。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很有限,1978年仅有15.75亿美元⑦。所以外汇严重不足成为我国引进技术设备遇到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中共采取了如下一些办法:1.发展出口创汇,采取各种形式把出口贸易做大做活。2.发展非贸易创汇,特别是国际旅游业,“要大量增加各种非贸易外汇收入。旅游事业要加快发展,并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服务态度”⑧。3.采取延期付款、分期付款、补偿贸易等灵活方式,减少现汇的支出。1977年7月,国家计委在批判“四人帮”对外贸工作的破坏时,肯定了过去被“四人帮”反对的延期付款、分期付款以及补偿贸易的做法,认为“为了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必须增加出口,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可以按照国际贸易中延期付款、分期付款等通行做法,由外国供应成套设备,然后用我们生产出来的煤炭和原油偿还”⑨。在实际工作中,当时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延期付款的做法。1977年,中国签定的引进技术设备合同220多项,成交金额30多亿美元,其中26个大型成套项目,43套综合采煤机组,用汇占80%以上,而其中40%的金额采用的就是延期付款的办法支付的。
但是,“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对于利用外国贷款和直接投资两种引进外资形式,仍然是不允许实行的。1977年3月《国际贸易》发表文章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允许外国资本家来开发资源,也不允许外国资本搞什么联合经营。”1978年4月22日,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利用外资形式之后明确指出,对于借款和合资经营两种形式,“我们是坚决不干的”⑩。直到197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编写出版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一书中还表示:我们既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同我们办合资企业,更不允许把领土领海主权租让给外国。
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以后,其它引进形式都逐渐允许,而这两种形式却不允许呢?主要原因是60年代以后,毛泽东就把利用外国贷款和直接投资两种形式看作是对外引进的两大禁区。“文革”结束后,当时“左”的思想尚未肃清,在思想上还没有摆脱“两个凡是”观点的束缚,所以中共仍然坚持“两个不允许”政策。但是,就在党和政府在重申“两个不允许”政策的同时,促使中共突破这个禁区的因素也在不断体现。
第一,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开展,使人们的思想不断得到解放,“两个凡是”的阵地愈来愈小。9月16日,邓小平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11) 邓小平的讲话,为中共和政府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提供了思想保证。
第二,客观因素在促使中共不得不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一方面,大规模的引进与外汇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中共和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扩大出口、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形式,但都不能解决问题。当时中国每年的商品出口收入不过100多亿美元,其它非贸易外汇收入,更是不超过10亿美元,这相对于巨大的外汇需求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正如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写的《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所言:如果不寻找国外长期贷款,那么,中国当时提出的特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发展规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进口方面的巨大需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2)。另一方面,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剩余资金急需出路,而中国搞现代化,对它们是一个刺激。一些国家主动表态要借款给中国,1978年4月,外贸部长李强访问联邦德国时,联邦德国经济部部长狄特马就向他表示,只要中方肯接受,联邦德国经济界可以向中国提供不仅是4亿,而且是40亿马克的贷款。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也表态可向中国贷款。另外,一些国家的商人表示愿意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到中国来投资或合资办厂。这些客观因素促使中共不得不考虑是否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
第三,中共领导层的出国考察以及出国考察团的回国汇报为中央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提供了促进剂。“文革”结束以后,中共领导层开始走出国门去了解外国发展情况,例如,1978年是邓小平一生中出访密度最大的一年。从这年年初开始,他接连出访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中国周边国家。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使得中共领导层对先进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中外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和感受,这就为对外引进政策的突破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
出国考察团的回国汇报,特别是以谷牧、林乎加、段云为团长的3个出国考察团的回国汇报更加促使中共领导层对引进政策进行理性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经验是3个代表团所要考察汇报的内容,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本经济代表团总结日本为什么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飞跃进展时,指出两条经验,一是大胆引进新技术;二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总结港澳发展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是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和廉价劳动力。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西欧经济考察团指出欧洲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科技高度发展,资本更加集中,生产更加社会化。3个考察团的汇报,在中央产生了巨大影响,言外之音,中国如果要想快速发展,就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这样,“两个不允许”政策势必就要被打破。
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共开始逐渐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1978年5月30日,在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邓小平又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13) 1978年6月3个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强烈建议: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14)。邓小平约谷牧谈话,详细询问了出访情况,指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15)。1978年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李先念就指出: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16)。随后,全国计划会议确立了“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7)。9月28日,《人民日报》指出:我国还准备采取更加灵活的贸易方式和支付方式。联系当时的形势,明显灵活的方式指的就是利用外国贷款和直接投资。10月,当邓小平访问日本,日本政府表态可向中国贷款时,邓小平回答:“我们还没有考虑,今后将研究这个问题。”(18) 邓小平虽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但显然没有拒绝之意。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根据会议精神。11月11日,李先念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表示:在不损害我国主权的条件下,我国可以利用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以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速度(19)。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指出:“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20) 当有人问怎样看待接受日本政府的贷款时,邓小平回答:“可以接受。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方式。我曾请教过士光敏夫会长,他说巨额贷款需要政府间来办。民间不能解决的,需要政府间解决。”(21) 12月15日,外贸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今天我们做贸易有了很大的改变,采取了很多灵活的做法。不久以前,我们在外贸上还有两个‘禁区’:第一,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不干,只有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贷款;第二,外商在中国投资不干。最近,我们决定把这两个‘禁区’取消了。基本上,国际贸易上的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2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就表明“两个不允许”政策最终被打破,从而实现了中共对外引进政策重大转折。
三、小结
由于1976~1978年“文革”遗留下来的“左”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肃清,对外引进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跃进,所以,在具体的对外引进实践中还存在盲目性。在作出大规模引进决定的1977年,中国的全部财政收入才847亿元人民币,整个出口的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基本建设总投资382亿元人民币。同国家计划引进所需要的180亿美元外汇和1300亿元人民币投资比较起来,差距太大。国内资金不足,寄希望于从国外借钱,实际上也是不现实的,出口的货源和外汇收入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很大的增加,近期的还贷能力根本不具备(23)。但是,实践中的冒进不能否定引进政策本身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首先,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引进外资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在落后的基础上搞建设,仅靠中国自身力量不行,要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认为西方先进技术经验是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邓小平说:“抢时间很重要,全国准备引进上千个项目。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必须是七十年代的,配套也要是七十年代的……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4) 其次,在怎么引进上,中央也形成了一些共识。如提出引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引进技术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再如,提出要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引进的关系。学习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勇于创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我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但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可以说,从引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利用外资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三中全会前夕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为后来对外开放思想的确立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这表明包括引进政策在内的对外开放国策已经确立。
注释:
①《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中发[1977]12号。
②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红旗》1978年第3期。
③《国务院批转关于进口成套设备检验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国发[1978]262号。
④参见: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⑤⑥(13)(15)(2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210、320、335、437页。
⑦转引自李正华:《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⑧《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⑨国家计委大批判组:《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评“四人帮”对〈二十条〉的“批判”》,《人民日报》1977年7月16日第1版。
⑩《李强同志谈灵活的对外贸易做法》,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第59期,1978年5月29日。
(11)(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9页。
(12)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上海市对外贸易国际贸易研究室译:《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1卷(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1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6)转引自张树军、高新民:《共和国年轮1978》,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17)《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320页。
(18)《中日经济合作余地很大》,《新华月报》1978年第10期,第227页。
(19)《李副总理会见美国朋友》,《新华月报》1978年第11期,第218页。
(21)《宣传动态》1978年11月30日。
(22)《突破“禁区”,为四个现代化大干贸易》,《经济导报》第1600期,1978年12月20日。
(23)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