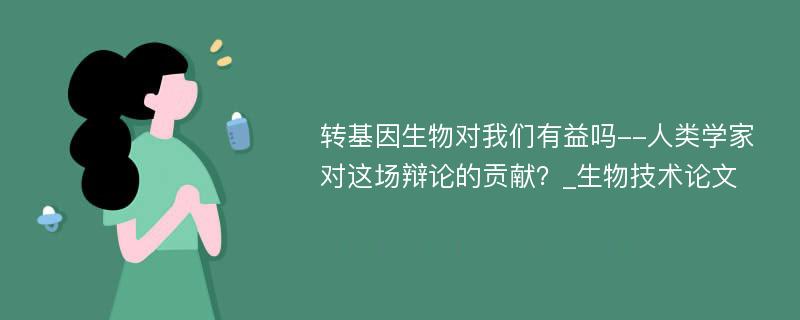
转基因生物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么——人类学家对这场争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家论文,转基因论文,这场论文,说是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07)04-007-08
转基因生物(GMOs)是通过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转移基因而获得。传统的动植物培养是在同一物种内部具有较好特性的个体之间进行杂交,而基因工程可以把北极大比目鱼的基因嫁接到草莓里以获得抗冻性,或者把细菌的基因嫁接到玉米里从而使其免除虫害。
抛除用于生物医学目的的转基因生物不谈,基因工程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通过转基因农作物以及其他转基因生物进入到我们的食物系统中。转基因农作物是有望带来巨大益处的新的生物体:可能比传统物种高产,能避免虫害和疾病,对水或农药的需求更少,甚至可以产生更多的维生素。然而,转基因生物同时也会带来诸多风险,不仅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和环境,还连带有一些社会与政治牵连。就像核能与DDT一样,转基因农产品以及由转基因农作物制造的食品里包含了Beck(1999)所谓的“人为不确定性”,一项新技术的全球性长期影响是不可能预见的。
第一个见之于大众的转基因农作物Flavr-Savr西红柿,是在1994年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批准销售的。从那以后,大量的农作物与食品在美国得到批准,包括玉米、大豆、油菜籽(canola)、西红柿、椰菜、番木瓜果,以及猪、家禽和鲑鱼。美国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仅仅在1996年到1999年之间,就从三百万英亩剧增到六千三百万英亩。到2001年,美国种植的24%的玉米和63%的大豆都是转基因品种。转基因品种与传统品种被农产品公司掺杂到一起,因此,转基因玉米淀粉、玉米油以及玉米汁、大豆面粉、大豆油,以及大豆蛋白,几乎存在于当今美国出售的各种食品里。转基因发酵粉和凝乳酶替代品也被广泛应用,大多数奶制品都包含一种被注射了转基因生长激素rBST的奶牛的奶。尽管美国1/3的消费者尚未意识到这个现实,但是在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大约有70%的食品都包含转基因成分。
在欧洲、日本、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尽管转基因产品的采用最初获得了大多数政府的支持,但是却受到了来自科学家、农场主、消费者以及与环境、贫穷、社会公正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媒体上有关支持和反对转基因生物的讨论,引发了更强烈的公众争论。反对者组成一个虽不整齐划一然而却十分有效的全球性反转基因联盟,现在他们已经取得诸多进展,包括取得了有关转基因农作物与技术的禁令,转基因食品要强制性贴上标签,转基因产品市场显著萎缩。尽管反转基因生物联盟已经赢得了很大胜利,全球性的关于转基因工程的争论仍在进行。
美国的形势很不一样。连续几年内管理部门都热衷于支持生物技术工业,批准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生物技术工业已经紧密控制了有关转基因生物的信息传播,他们通过发布几乎所有可利用的科学数据、游说议员、雇佣品牌推广公司和资助新闻记者等方式去型塑公众的判断(Rosset,2001)。主流媒体没有提及任何严肃反对转基因生物的声音,大多数的公众对此几乎没有什么意识或者是对此漠不关心。
然而,最近出现了转机。新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80%~90%的人支持对生物技术食品强制使用标签。他们声称,当得知自己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消费了多少转基因产品时感到非常惊讶和愤慨。但是,这里仍然很少有人知道足够的转基因知识。大的生物技术公司,比如Monsanto,宣扬转基因农作物将会修复环境、解决饥饿问题并能治疗疾病。绿色和平组织则反驳说基因改造食物(Frankenfoods)必将招致厄运。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外行又如何才能判断应该站到哪一个立场上呢?
人类学在对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问题上提供重要的批判视角方面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它能帮助我们分析科学知识和实践的意识形态,并且指导我们去解析那些用于为这种权力系统做辩护的修辞技巧。它十分强调诸如转基因生物之类的人造产品的社会和政治维度。而且,它关注于把全球性进程和地方性影响结合起来,涉及公司资本、食物链、消费者—公民行为,以及和农民、农村贫穷等因素之间的交叉关联。
为了澄清什么是利害攸关的,区分公共转基因生物和公司转基因生物(public and corporate GMOs)是有用的。所谓公共转基因生物,我是指那些为了公众利益而发展的,通常在一些公共研究机构中研究获得,而且不以出售盈利为目的的转基因生物(例如,为了农民而发展的改良型农作物)。而所谓公司转基因生物,我是指那些由公司研发出来用于商业用途的转基因生物。在实践中二者的界限通常是模糊的:公司研发或者获得产品技术专利是在公共实验室里开始的;公共项目通常免费或者以很少的费用使用公司研究获得的数据;公司资助公共实验室里的研究。但是当考虑到某种特定的转基因生物所带来的风险时,把二者进行区分还是很有用的。
作为新的生命形式,所有转基因生物表现出来的环境和健康风险都应该被严格地研究。而且任何熟悉绿色革命的人都知道,新的农业技术,即使是免费提供的,也并不必然能够帮助穷人。公司转基因生物比公共转基因生物呈现出更大以及更多样性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公司主义技术(corporatist technology)。用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呢?公司转基因生物是特定设计的,用来增加公司利润、扩展公司垄断以及加强公司控制的工具。公司已经把控制风险和责任的政策成功地强加到了美国政府身上,并且在别处也极迫切地实行。这些政策中包含了公司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坚持认为商业行为具有要求它们的投资获得有效回报(尽可能大规模、快速和垄断的)的合法权利,而且拥有它们生产或只是加工过的任何知识的所有权,但是对产生的任何不利影响仅负有极其有限的责任(Crook,2000)。由于追求快速盈利的动机塑造了用于验证它们的科学,公司转基因生物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很高,而且其环境和健康的风险比公共转基因生物要高很多。
一、公司主义技术
在20世纪80年代,聪明的年轻生物学家们开始离开大学的实验室,以追求由于生物技术的出现而带来的独立、创造性和财富。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物专利的申请在美国取得合法地位,生物技术公司开始注册智力财富所有权,不仅包括技术加工工艺,所绘制的基因图谱,还有他们生产的转基因生物体。例如,2001年1月,Syngenta公司完成了水稻的基因图谱,现在它已成为该公司的“私有财产”了。转基因研究成本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需要用到已经获得专利的植物原料和私人拥有的基因数据库。而且,转基因生物被批准之前必须进行测试,测试得越彻底,成本就越高。完成一个新的转基因农作物需要几十甚至几百万美元的投资。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的是,目前几乎所有投放市场的转基因农作物都是由生物技术公司制造的,而且主要是日用农作物品种。
基因工程尽管可能在抗病毒或抗干旱物种培育,不需要额外化肥而增加产量的作物培育等方面有显著作用,但是只有少数的公共实验室可以承担起这种研究。即使它们能够进行这类研究,在将一种新的农作物免费提供给农民之前,它们必须获得许多公司的专利许可。欧盟生物技术计划(The European Community Biotechnology Programme)、瑞士联邦工学院以及洛克菲勒基金共同资助了一个最近轰动了新闻界的超过一亿美元的风险项目。“黄金水稻”包含了水仙花基因以产生β-胡萝卜素;这种水稻可以帮助减少贫穷人群因饮食单一引起的维生素A缺乏。Syngenta、Monsanto以及其他生物技术公司已经捐献了许多专利许可给一些公共研究所,使发展和测试黄金水稻能够进行,并且把它们免费供给那些需要维持生计的农民。当然,如果黄金水稻被商业农场主使用,这些公司将保留该产品的所有权。
大部分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研究都是关于日用农作物的,这些研究主要是公司进行的。这些公司的主要目标市场是那些投了重资的大规模的商业农场主。通过一系列买卖与合并,这个产业现在主要由七个公司把持(一些在美国,一些在欧洲)。每个公司的年销售量都在20亿美元以上。其中最大的公司Syngenta(设在瑞士),是2000年11月由瑞士的Novartis和英国的AstraZeneca公司合并的;然后依次是Monsanto(美国),Aventis(法国),DuPont (美国),Dow(美国),Bayer(德国)和BASF(德国)。生物技术公司也生产农化产品(如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并且出售种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公司生产的转基因品种是有意设计用来增加公司利润和控制能力的一种技术形式。Monsanto开发了很多品种,包括玉米、棉花和大豆,这些品种都对另外一种Monsanto产品Roundup除草剂具有免疫力。由于这种除草剂可以直接喷洒到田地里不会杀死农作物,因而没有必要机械除草。但是如果使用任何其他除草剂,Roundup-Ready品种就会死掉,因此Monsanto公司可以依靠这个把除草剂卖给每一个买了他们种子的农场主。Monsanto公司希望Roundup-Ready玉米的全球市场能够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从300万英亩扩张到两亿英亩。生物技术产业生产的其他为了增加公司销售和控制的转基因农作物,包括反对者称之为“终结者”(Terminator)的技术(最初是由Monsanto进行的,在1999年由于公众的反对而放弃,但是一直还在研究),这项技术可以致使谷物成熟的时候绝育而不能再用作种子;还有“叛逆者”(Traitor)技术,它致使农作物显现出依赖某种附加的化学制品的显著特征——自然,这种化学制品是由同一公司生产的。
生物的专利所有权竞争激烈。一些国家,如印度和墨西哥已经对西方公司宣布拥有诸如Basmati水稻和谷物等表示强烈不满,这些农作物是它们的农民在数世纪前培育的。情况还在变糟,当种子通过它的DNA排序被认定的时候,就像软件一样如果不付费就不能复制。由来已久的储存和交换种子的方式,以及在农场上的选择和培育的实践都变得不合法。Monsanto公司拥有自己的马铃薯DNA测试田地,并且控诉那些改种它的“新叶”(New Leaf)马铃薯的农场主。近来,这个公司成功控告了加拿大的一个农场主,这个农场主种植了没有经过授权的转基因菜籽,尽管他的传统作物是被附近农场的转基因农作物的花粉污染的。
转基因农作物经常被宣称对解决全球饥饿是必须的。适当形式的转基因农作物,如果它们是免费的且不需要任何其他附加耕作费用,也许真的可以帮助改进大约6.5亿无所依靠者和一些小农的生计问题,这些人占了世界范围内13亿穷人的一半。然而,就如来自热心科学家联盟(Union Concerned Scientists)的Margaret Mellon所说,如果有人愿意投资那些无利可图的研究,同样可以通过传统物种选择的方式培育品种,在低环境风险的情况下达到相同效果。对于那些完全不了解乡村经济和饥饿状况,生活于舒适的中产阶层中的西方人来说,转基因生物技术也许提供了一个不可拒绝的好的技术解决途径。然而,公司转基因农作物的生产是用来推进大规模产业系统,并且把农民束缚到一个互相依赖的系统之内的。
全世界的农场主们很快就意识到转基因农作物对他们的生存来说是一个威胁。类似绿色革命的杂交品种,公司转基因生物需要农场主们购买种子和化学制品上的投入。在地方上,他们因此青睐那些比较富裕的农场主,这些农场主可以卖掉多余的东西换成现金并且通过拥有的土地获得贷款。贫穷的农民不一定能负担得起新技术;如果他们采用了新技术,但是农作物收成不好或者卖价过低,他们将会破产(1999年印度Andhra Pradesh穷人种植转基因棉花的事件导致数百个农场主自杀)。对于那些仅能维持生计的农场主来说,每季购买转基因种子的费用就足以使他们生活窘迫;他们不能再使用动物肥,不能再变换他们的种子,不再用手工除草而是采用了除草剂,但是必须需要钱去支付化学制品的投入。最后,许多贫穷的农场主或者无所依靠者都只能依赖于通过给富裕农场主耕作而获取的工资,但是转基因物种,例如Roundup-Ready将通过化学过程代替这类工作。20世纪60~70年代的绿色革命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那些主要用于增加产出和减少劳动力投入的技术通常会加剧农村贫困(Bray,1994)。从全球来说,如果美国、澳大利亚或者欧洲的商业农场主对转基因谷物的采用增加了产量并降低了价格,那么南半球地区的谷物市场将会被廉价的进口农产品所充斥,导致当地的农场主破产。因此,毫不奇怪,全球范围内的农场主组织已经开始积极地反对转基因生物,而且许多贫穷国家的农业代表极其愤慨地批驳了关于这类谷物将会减少贫穷和饥饿的说法。
二、科学政治:风险定义
在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氛围之下,大部分政府都被基因工程以及它对经济增长和进步的承诺所吸引。生物技术(生命形式的重组)具有了高技术领域所共有的迷人的和超先进的吸引力。印度时报 (The Times of India)的某社论(2001年3月23日)说:“如果信息技术到来,生物技术还会远吗……以基因为基础的生物技术成为新经济的新的年轻英雄。”
在被种植或者出售制作食品之前,转基因农作物必须经过官方批准。在美国,三个调控机构,即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环保局(EPA)和农业部(USDA)负责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各方面的检查工作。尽管基因工程的支持者暗示,拥有三个检查部门必定意味着十分严格的标准,但是Pollan(1998)却表明,在它们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并从中获利是多么的容易。另外,在生物技术里,存在于实验室、联合委员会、调控机构以及政策之间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运动现象是十分惊人的。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前商务代表Mickey Kantor加入了Monsanto的委员会,而同时Monsanto公司的化学实验室主任Margaret Miller离开实验室加入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同年,George W.Bush任命1995~2000年Monsanto公司的副主席Linda Sisher担任环保局的代理行政官。
上述关系铺平了公司转基因生物得到官方支持的道路。后来的美国管理部门都和生物技术公司密切合作,从而设计出在本质上把制定转基因生物政策的责任交给生物技术公司本身的规则系统。由公司来定义需要调查的风险,并执行那些获取批准所需的研究。
我们都知道核能、杀虫剂和BSE(“疯牛病”)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一开始被宣称完全安全的产品或加工工艺,经常被证明具有复杂的、长期的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最近在欧洲机构中比较流行一种风险评估的可选择模式(alternative paradigm),即预防原则:在任何可能存在长期和复杂影响的地方,在一项加工工艺或产品被宣称是安全且可采用之前,所有的风险必须得到彻底研究。这种安全比后悔好的方式是需要花时间的,而且和那些自由商人或公司所喜欢的定义风险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在国际上关于食品安全包括转基因农作物的讨论中,美国代表一致认为预防原则以及它所代表的科学,有碍商业行为。
生物技术业界已经成功地让美国管理部门确信,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可以通过少许实验、少量样品,仅仅需要数月甚至几个星期就可以得到充分检验。正如生物学家Michelle Marvier对此进行的仔细分析,“(他们)的做法是强烈倾向于不发现任何影响,即使影响是真实存在的。尽管不太容易看穿,这种方法在本质上类似于抛掉数据,除非数据能够产生出预期的答案”(Marvier,2001:160~167)。
独立的研究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但是由于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公司范围内做的,发表的科学数据都是压倒性的偏向转基因公司。当一名泰国的分子生物学家质疑由国家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Biotec)发布的肯定Monsanto公司转基因豆荚安全性的报告中所用方法的时候,该中心的发言人承认支撑他们研究的很多文件都是Monsanto公司提供的。他说,“我们的能力、资金以及技术有限,很难进行自己的独立研究。借助一些可利用的文件是必要的”。正如Arnad Pusztai所揭示的那样,当政府支持的苏格兰研究团队发现了表明吃转基因马铃薯有可能伤害老鼠的事实时,对其不利的结果,即使是初步的或假设性的,都是不受欢迎的。Pusztai曾在一个电视访谈里提到这件事,并进而质疑现在的研究在评估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风险时是否是足够的。三天之内,Pusztai被停职并被禁止言论;他的数据被没收,而他的工作被皇家学会组织的一个匿名委员会宣称为毫无价值。
大部分进行转基因农作物研究的公众科学家 (包括Pusztai)原则上支持转基因农作物,但是他们比公司里面的同行们倾向于对存在的风险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并且主张进行长期的详细测试。许多参与过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早期转基因农作物调查的科学家反对它们未经进一步测验就获批准,尽管这些科学家的观点在最终报告里不会反映出来。虽然生物技术的游说者大声斥责,声称如果黄金水稻的上市被延误一个月,将会使五万个孩子处于失明中,但是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机构相信,在黄金水稻可以安全地进行田野实验之前至少还需要进行5年的实验室研究。
三、基因改造食物(Frankenfoods):失控的消费者
1994年,首批转基因农作物在美国获得批准,当时生物技术的游说者们针对广大消费者和农民发起了一场公开活动,他们最小化了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并强调转基因作物的好处。说服美国农民相对较为简单,运动十分成功。转基因农作物被宣称比普通作物需要更少的危险化学制品,而且能保证更高的产量:它们能降低农民的健康危险和他们的投资风险。实际上,产量并非总是更高,成本也可能会增加,市场还可能会崩溃,但很多美国农民依然青睐于转基因品种带来的好处(Anderson,1999; Bray,2002)。
相比之下,要说服普通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就更为复杂。起初,基因工程的说服者害怕人们也许会担心转基因食品的“自然性”问题,甚至担心它在道德层面将会引起的困惑。例如,当北极大比目鱼的基因被嫁接到西红柿上时,将导致素食者对于是否能吃西红柿感到犹豫;而如果人的基因被嫁接到猪身上,吃熏肉的人是否就会成为食人族呢?有关信息在新闻和网络上得到广泛传播,它将生物技术看成是农业进化史中的下一个逻辑步骤。如同经验丰富的人类学家,基因工程支持者们指出了人工物品的自然性和天然物品的非自然性。正如一位专栏作家所言:“对于面包、葡萄酒或者小猎犬而言,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实际上,我们人类自身也没什么东西是‘自然’的。”
至于有可能引起的健康危害,大众得到保证,转基因食品已经过了虽然快速但却严格详尽的测试。这些食品肯定是安全的,因为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了它们。更好的是,转基因食品的第二代很快就要为消费者的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例如马铃薯在油炸时吸收的油更少了,蔬菜含有更丰富的维生素,谷类食物没有麸质了。1999年,面对转基因农作物发生的信任危机,DuPont为了重新获得消费者的支持,通过投放广告表明公司正在开展“寻找有助于预防乳癌的食物”的基因工程研究。
实际上,美国公众起初并没有表现出对转基因食品的疑虑,这也许是因为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已经在吃转基因食品。同时,反诽谤法(类似于针对Oprah Winfrey的起诉,他对汉堡包的健康性提出了质疑)有效地钳制住了记者们的言论,这些人正试图通过深入调查,探究基因工程技术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但是,在欧洲、日本、印度和非洲,却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英国迅速被授予“基因改造食品”称号的东西被认为既不安全也不健康;然而抗议者所提出的风险定义,已远远超出生物技术工业力图强加的狭窄范围了。转基因生物已不仅仅是对个体而言安全或不安全的一种食物形式,也不仅仅是其长期风险很难被了解的一种环境威胁,而是公司主义权力和控制力全球化形象出现的某种象征和表现。
尽管政府和大的农场主最初都支持采用转基因品种,但是公众的观点很快就集中地反对他们,而媒体的参与确保了基因工程问题戏剧性地再次引起了每个人的关注。当生物技术游说者们迫切要求快速获得对转基因生物的支持时,这种行为在欧洲却被广泛解释为对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国家主权的霸权主义侵犯。当政府支持该方面的秘密实验,或者不顾反对公然批准这种行为,并以此威胁民众时,抗议者很快就给这一行为贴上了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标签。来自英国莱斯特的一名27岁的年轻教师帕特,参与了1999年7月发生在牛津郊外的农作物踩踏事件。他宣称:“对于推行这项技术的公司和政府,我感到非常的愤怒。他们根本不听民意,他们不知道风险……我们是故意践踏这些农作物,这在向政府表明:‘请听听我们的声音。你如何敢站在公司而不是你的选民那一边’”(Vidal,1999,italics added)。
通过电子邮件、网络和西雅图国际聚会,随后的反转基因者们组织形成了一个包括消费者群体、激进绿党、老年人和青少年、印度卡纳塔克邦稻农、巴西无地农民、法国绵羊养殖主、日本家庭主妇等在内的强有力联盟。他们的行动方式包括举行政治抗议,破坏转基因农作物,呼吁长期研究以及简单地拒绝去消费。强势的北方消费者联盟积极影响了农场主的抗议,这些人之前即使是在国家范围内都很难找到有效的反对方法,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有所作为了。日本和欧盟共占美国农产品出口市场 36%的份额。消费者对含有转基因成分食品的协同抵抗,以及他们坚决表示必须知道哪些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导致超级市场、食品工业和政府的决策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同时也对生物技术公司和美国农民产生了戏剧性的冲击,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还为误传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风险为Monsanto盖上了遮羞布。
面对如此坚决的抵抗,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转基因食品的种植和消费;全世界共有35个国家现在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转基因标签法。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几乎所有的超级市场连锁店都拒绝采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其中有很多地方还开始禁止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动物类产品,包括鸡蛋、奶制品、鱼和肉等。日本的大豆加工厂商为了满足消费者坚持不用转基因大豆的要求,不再向美国而是从英国进口大豆。1999年,美国的玉米、大豆出口市场崩溃,生物技术工业濒临倒闭。从那以后,生物技术工业又重新整合力量,当下正致力于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开战,以期赢得美国公众的支持。
四、美国今天的转基因生物:我们要闭上嘴,默默食用我们的转基因菠菜吗
大约是在去年的时候,美国公众开始对转基因食品感到不安。2000年9月的新闻披露,Aventis公司生产的一种仅用于动物饲料的转基因品种——StarLink玉米,在人类食用的脆皮玉米饼(Taco Bell shells)中被发现了。随后的测试发现StarLink玉米在很多玉米类食品中都存在,并且有些消费者还发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他们认为这是食用StarLink玉米成分所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被迫开始对这些食品进行检测。主动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措施,Aventis公司到目前为止已花费大约10亿美元用以回收这些受到污染的食品,并且很快提出要求准许人类食用StarLink玉米转基因成分。尽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明显支持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签,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依然宣称贴标签既不具有科学上的必要性,在法律上也不可行。可见,美国在关于转基因农作物问题上,同样存在着“民主赤字”。
美国反转基因组织通过介绍欧洲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措施,以唤起美国消费者的意识:“Kelloggs公司现在已给欧洲市场的转基因脆玉米片贴了标签——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能给转基因食品也贴上标签呢?”这是加利福尼亚政治利益研究团体(CalPIRG)在2000年夏天开展的电子邮件运动中所说的。由于担心消费者的反冲,一些美国食品公司已经禁止在他们的产品中使用转基因原料。例如,麦当劳在它的法式炸薯条中已不再使用转基因马铃薯,Gerber公司也在他们的婴儿食品中清除了转基因成分。
生物技术行业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行动,使得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关于转基因食品积极形象的正面报道。公共关系公会的公开宣传者常常被冠以生物技术信息顾问之类的名头,似乎他们是作为公众利益组织在传播客观的信息,但实际上却都只是工业宣传的工具而已。单是CBI就有2500万的5年期预算。反击行动包括广告和网络宣传,以及免费印发关于生物技术的小册子等,所有这些宣传都将转基因农作物描绘成绝对的奇迹,并乘机狠批有机农业和绿色和平组织缺乏社会责任感。
生物技术游说者们的一个核心策略,就是谴责抗议者的主张“感情用事”,带有“政治性”而不是科学性。人类学家也许会欣赏这种笨拙的家长式的大众科学观:“爸爸,我的盘子里有基因么?”(SDCMA,2001:13),以及当下公关闪电战中赤裸裸的情绪化色彩。媒体充斥着关于强壮牛仔和可爱的亚洲宝宝的华丽画像,认为他们的生活将(或者,如果我们认真阅读限制性附属细则,也许)会因转基因农作物而发生改变。
最近,有一两篇报纸文章温和地批评,当前的转基因食品只对农场主有利,而对消费者无益;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生物技术公司必须在转基因食品上下更多的工夫,让它们更有营养或者有助于预防疾病(奇怪的是,这些作者从来没有提过转基因食品的真正获利者是生物技术公司)。实际上,这一类型的基因工程更为复杂和不确定,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费用,这正是为什么那些华丽的广告总是提到,转基因技术的好处在未来有条件的情况下能够实现。黄金水稻是第一种投机成功的产品,少数基因测序与专利方面的花费就为生物技术公司换来了无价之宝,通过精心掩盖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生物和公共机构研发的转基因生物在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生物技术公司将自己描绘成技术奇才和人道主义者。因黄金水稻的关系,生物技术公司的转基因农作物被罩上了大公无私的光环。实际上,尽管来自Syngenta公司的技术贡献与专利捐赠是创造和发明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但如果黄金水稻最终提高了亚洲穷人的营养标准,却恰恰因为它不是一项公司转基因生物,而是一项由公共机构研发、测验并由公费出资分发给农场主的转基因生物。
五、黄金水稻:为什么我们必须区分公共转基因生物与公司转基因生物
2000年,黄金水稻被宣布发明出来。它含有能生成β-胡萝卜素的水仙花基因,食用黄金水稻能帮助减少维生素A的缺乏,这在那些没钱获得丰富均衡饮食的穷人中较为流行。它由瑞士联邦技术协会的Potrykus和Beyer研发(或者说“发明”),该项目从欧盟生物技术规划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资助,旨在为农民百姓免费分发成果产品(Potrykus,2001)。
黄金水稻基本还处在原型阶段。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研发适合地区条件水稻品种的公共机构)的科学家认为,黄金水稻至少还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进入田野试验阶段。并且,所谓维生素的提高也未真正进入操作阶段,在目前,一个人每天需要食用9千克的黄金水稻才能达到人体每天所需摄入维生素A的剂量(Brown,2001b)。尽管黄金水稻的好处仍是个承诺而不是事实,生物技术行业已投入5000万美元用于商业宣传。尽管它是公共科研机构利用公共资金研发而成,但能研发成功还必须归功于包括Syngenta和Monsanto在内的生物技术公司捐助的70个专利。其中,Monsanto公司是无偿提供,Syngenta公司则在黄金水稻的商业种植方面保留了所有权(Fulmer,2001; Potrykus,2001; Shah,2001)。
在全世界范围内,今天很多人都将转基因生物视为“公司贪欲的同义词”,但是黄金水稻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喂养穷人、治疗盲人的转基因生物。最近,生物技术信息理事会在《纽约客》上发表了整版的广告,展示了一个女孩的5个侧面像,她依靠在棚屋的木板墙上,穿着脏兮兮的粗布棉睡衣,捧着饭碗正用筷子吃饭,她的母亲呵护抚爱着她:
生物技术研究者说它是“黄金水稻”,因为颜色,因为机遇……生物技术的发现,从医药到农业,正在帮助医生治疗我们的疾病,帮助农民保护他们的农作物,帮助我们的母亲照顾孩子,让他们更加健康(New Yorker,2001)。
黄金水稻对于生物技术公司而言是一项精明的投资。少数基因序列和专利就为他们换来了证明自己是技术奇才和大公无私的人道主义者的机会。那些反对转基因农作物的人可能因此会被斥责对饥饿和疾病麻木不仁。在对不接受转基因食物的风险进行描述时,Syngenta公司十分夸张地宣称,黄金水稻的上市只要被延误一个月,就会使五千万亚洲贫困儿童处于失明中(Pollan,2001)。
2001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愤怒地表示“黄金水稻在公关方面的利用走得太远了”。(Pollan,2001)尽管同意转基因水稻在抵抗营养不良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他还是表示:“我们并不认为黄金水稻能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的问题”(Pollan,2001)。评论家公正地指出,类似于黄金水稻的技术可能只是简单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和资源从贫困的需要上转移到对贫困的社会和政治根源的关注上。然而,因为对解决营养不良、公害和疾病,或气候灾难等问题至少能做出部分贡献,黄金水稻这一类型的研究仍然有重要的潜力。
看起来,一些环保主义组织,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在原则上已决定反对所有的转基因农作物,甚至对那些由公共科学家设计出来服务于穷人的农作物试验,也不准备放弃反对意见。绿色和平组织对黄金水稻(在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之后做出)进行谴责的决定,这激怒了Potrykus,他做出了反驳,认为黄金水稻“将会免于控诉和限制,它将经由国家机构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穷苦农民用于当地的使用和贸易……它还能满足急需,能在丰收后重新播种,不会减少生物多样性,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威胁,并且只有当确认对消费者没有任何危害时才会给予供应”(Potrykus,2001)。尽管任何农业革新都不能保证没有社会风险或未曾预料的后果出现,Potrykus的观点表明他和他的同事们已将绿色革命的社会、政治教训放在心上,他们已非常谨慎地尝试着设计一种不受“贪欲”影响、不存在环境风险的转基因作物。
很多在公共机构从事转基因农作物研究的科学家在原则上都支持它们,尤其是当这些农作物被免费分发给农民以及设计用来降低农产品风险时更是如此(例如抗旱或耐涝的谷物、抗枯马铃薯或抗病毒木薯)。尽管其他植物学家强调老式杂交育种比基因工程的环境风险更小,而且只要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也能取得同等的效果(Berlan and Lewontin,1998; Kloppenburg,1988),公共服务性基因工程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有一些特征通过杂交育种是不可能获得的,例如黄金水稻果实和叶瓣中的β胡萝卜素(Conway,2000; Potrykus,2001)。而且,黄金水稻的IRRI计划表明,公共机构的科学家比生物技术公司里的科学家更关心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问题,他们更愿意选择长期实验,也即是预防性的研究方式(Conway,2000; Pimentel,2000; Pollack,2001)。
但是,只要我们继续不对公司转基因生物和公共转基因生物进行区分,我们还将无法对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做出合适的考量。一方面,这意味着我们落入生物技术公司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它还可能使得公共机构里的科学家在改善农作物培育方面的严肃研究变得更加困难。
很显然,将公共基因工程和公司基因工程视为一个事业整体是为了生物技术公司的利益,它暗示所有的转基因生物都是免费用来解决饥饿和疾病问题的,似乎Monsanto等公司更乐意帮助穷人而不是增加他们的股额。生物技术信息理事会是一个工业宣传工具,其当前的5年运作预算达到2500万 (Rosset,2001:23),但是它的名头听起来却像是一个传达客观信息的公共服务性组织。苏格兰的一家转基因公司联合协会赞助了14万本“华丽的宣传册”,这些“为转基因技术大唱赞歌”的小册子被分发给学校(Edwards,2001)。然而,不是只有生物技术公司搞这些花样。作为“公共研究机构科学家联合组织”的圣地亚哥分子农业研究中心也印发了一份漂亮的宣传册,它详细列出了转基因农作物的诸多好处,却对利润以及技术公司的存在只字不提,可是它非常直接地攻击了有机农业和绿色和平组织(SDCMA,2001)。
不幸的是,生物技术的游说者们将转基因农作物统一描绘成金色,我们的反转基因联盟又常常将它们完全描黑。这种状况排除了实际行动者和公共机构科学家合作开发公共转基因生物潜力的可能性。如果反转基因联盟能在公司转基因生物和公共转基因生物之间做出区分,他们就能把大部分政治精力用以支持公共科学家改进转基因风险试验的程序和范例,并支持他们将由生物技术公司垄断的专利重新转回到公共领域。而且,如果我们能对采用公共转基因生物与公司转基因生物的差别做出权威性说明,就能争取到很多美国大众,这些人中很多都是通过生物技术游说者的宣传才意识到转基因生物问题的。
最后,生物技术游说者们将转基因农作物说成是由大公无私的科学专家生产的,且这些人有充分的责任感去确定和严格测试转基因生物可能存在的全部风险,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转基因产品能获得诸如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之类机构批准的原因。尽管如果有人对转基因公司施加给消费者的控制或它们的法律特权提出异议,这些公司关于生命形式或基因序列的所有权以及收回投资收益的权力就常常会引发争议,但转基因生物设计目的和公司目标之间的联系还是被美化了。
类似于笔者的这些反对者很清楚,生物技术游说者们的科学是高度偏见的科学,大多数转基因农作物被精心研制出来以增加公司的权力和利润,同时却以牺牲民众权力、国家主权和贫困农民的生存权为代价。我们认为,转基因生物的潜在危害是多方面、复杂化的,当前的试验还不充分,美国的管理还只是个笑谈。显然,我们都十分愿意说服美国公众用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农作物。“但是又该如何看待黄金水稻呢?”笔者的学生问道。“难道我们不需要转基因农作物去挽救世界于疾病和饥饿之中吗?”要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在笔者看来,我们就必须在公共控制的基因工程和公司控制的基因工程之间做出重要的区分,并且还必须坚持关注新技术的社会维度和政治维度。
收稿日期 2007-0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