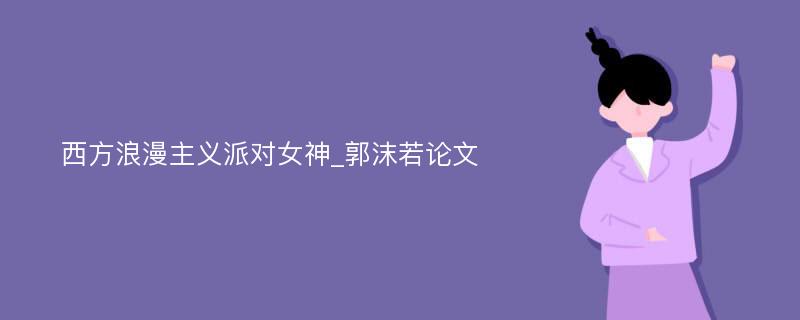
西方浪漫派之于《女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派论文,之于论文,女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4—0136—04
一
从首篇《女神之再生》起,涤荡一切、勇于反抗的挑战精神就象一条奔涌不息的巨大洪流贯穿于《女神》的始终,并成为它最高亢的音调,最浓郁的氛围。《女神》的主人公是一个个人反叛者,郭沫若赋予了它一种罕有的精神气质,他不仅被内心中巨大的冲击力所鼓涌,要借助于风光雷电之力摧毁整个宇宙、整个现实世界,而且一种创造的渴望正蠕动于其灵魂深处,促迫他上下求索,战则不息,驾驮日月星辰,创造“华美”、“芬芳”的理想世界。显然,这是诗人心目中的一个叛逆者和偶像破坏者的形象,在他身上直接透露着诗人自己的情感与理想,是诗人自我内心世界的外化。
对自我作用的肯定,对个人力量的崇信与弘扬,这些都显现出一种强烈的个性感觉正在增长,这是旧的封建秩序处于解体时期所特有的现象。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束缚禁锢人们合理发展的传统思想观念受到了冲击,被重新反思与批判。而经过这样一个反思和批判的过程,首先觉醒的一代先驱者从封建传统的桎梏中挣脱而出,变成了一个“新人”,一个反叛者。同时,他们在不断涌入的西方各种各样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接受了自由、平等、民主和个性解放等观念,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传统社会势不两立,自我崇高的精神天性远远超出庸庸污浊的现实社会,因此,他们崇天才,尊个性,重自我,要独立,把个人置于一切之上,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和出发点。郭沫若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篇中对自我和个人力量的讴歌正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和日益增长的个性意识。其特征是:坚韧不拨的决心,不屈不挠的意志,气腾腾而血沸沸的热情,以及在斗争中英勇无畏和不妥协的精神。
郭沫若在《女神》中所创造的这一强有力的“个人”形象无疑首先是那个解体时代的产物,同时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有直接联系。因此,当我们单取《女神》中抒情主人公不畏世俗,反抗挑战的一面时,我们首先见出的是“拜伦式英雄”的痕迹。拜伦是郭沫若最倾心的浪漫派作家之一,从自述中可以看到,拜伦及其创作引起了郭沫若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甚至把他看作自己精神上敢作敢为的直接先驱和带头人。在这里,这种自认的承接关系首先体现为拜伦关于自我和个性的观念及其作品中呈现出的冲破一切罗网,顺应自我内心欲求的反抗倾向被郭沫若所接受。拜伦一生创作丰富,思想倾向尤为复杂,但是其作品中“拜伦式英雄”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蔑视世俗,天性崇高,极端重视个人的精神追求及其内心表现。《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同名主人公(他是拜伦的化身)由于厌倦了百无聊赖、平庸乏味的上层贵族生活而开始了自己精神上的人生漫游。虽然偶尔在往昔的陈迹中他能找到与自己精神相通的历史英雄并为之身心摇荡,然而这一切都如过眼云烟,现实社会却依然是奴颜卑膝,自私卑下,一团颓败污浊之气。因此,他愈来愈痛感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与现存秩序及其价值观念处于对立冲突之中。但是,他不退却、妥协,而是怀着满腔的怒火和挑战精神向社会复仇、抗议,遗世而立!《曼弗雷德》和《东方叙事诗》同样表现出这一倾向,只是这些作品中的“拜伦式英雄”比哈洛尔德更激烈,他们彻底地抛弃平庸的日常事物,抛弃束缚人的精神追求的一切东西,而更加尊崇独立自由的个人及其大胆的热情,傲世独立,行踪诡秘,其结局往往失败或死亡。“拜伦式英雄”的这一趋向标示出他们与现实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一种崇高的精神天赋与现存事物的平庸渺小之间的矛盾。这种倾向在西方浪漫派文学中颇具普遍性,不仅体现于雪莱、海涅(均为郭沫若喜爱并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家)等积极浪漫派作家的创作中,而且在施雷格尔兄弟、霍夫曼和“湖畔派”诗人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突出的展示。
郭沫若在其诗情爆发时期正沉浸于浪漫主义的氤氲氛围中,因而在《女神》中印下“拜伦式英雄”的足迹是十分明显的。除了《天狗》、《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等明显的例子外,在一些抒写对未来的理相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的诗篇中也有所体现,诸如《湘累》、《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等。《湘累》其旨在展现一个怪诞狂傲的灵魂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及其悲剧遭际。这是一个既富有血性而又冰清玉洁的灵魂,具有激昂的热情,不可遏止的意志,无限的精力,他遍身缠绕着香花美草、莲佩荷冠,他象扬子江一样怒吼咆哮,倾泻着长期郁积于胸的愤懑,“疯癫识倒”,为自身的被放逐而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凤凰涅槃》中的“凤凰”在自焚的炼狱过程中“更生”,这是一个华美而神圣的创造过程,然而却遭到了那些岩鹰、孔雀、鸱枭、家鸽、鹦鹉、白鹤的嘲讽。这群凡鸟对这幕壮烈肃穆的悲剧的戏弄,正体现着一个骄傲狂妄的精神个性对丑恶而鄙俗的尘世的拒斥、蔑视,并以此显示这幕悲剧的悲壮性和崇高性。所有这些,均朝着一个总的趋向推进:一个傲然自负、充满活力的“个人”对整个传统的摈弃,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所以在这里,《女神》中的抒情主人公虽然充满着浓厚的个人倾向,但它显示出一个刚刚从封建束缚中走出来的民族其冲破一切因袭,争取复兴寻求新生的不可遏止的愿望和力量!
在这些诗篇中的诗人自我形象大都富于热情,激情洋溢,其情感似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这种情感的炽烈与昂扬又把诗人与惠特曼扯在了一起。这使我们看到了郭沫若“拜伦式英雄”新的一面,酷爱自由、为民族振兴赴汤蹈火的一面。惠特曼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与启迪已为人们所熟知。郭沫若自称有过一个惠特曼阶段,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雄深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注:见《郭沫若谈创作》。)在这里,当然首先是惠特曼灵活自由,不拘一格的诗风和表达情感的诗歌形式给了诗人以勇气;但是惠特曼于郭沫若之间更内在的联系恐怕还体现在惠特曼关于自由、民主尤其是关于民族解放的观念使郭沫若感到心心相印,更切其心腑。进步的浪漫主义者始终将民族的利益置于一个神圣的地位,比如众所周知的拜伦之于希腊人民的独立与解放,歌德之于德国的复兴等等。但是,他们的“公民精神”有时却沾染了贵族式的傲慢色彩,因而个人主义倾向、我行我素的倾向也渗透其中。在公民精神和对民族新生的关注这一点上,惠特曼表现的最充分,最突出。这与他处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深受美国人民强烈的寻求联邦统一的愿望和情绪的感染相攸关。《草叶集》中也有歌咏“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作品,如代表作《自己之歌》等,但同时其中更多的诗章是借助自我情感的抒发表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呼声,如《桴鼓集》及其续编《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时》。《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时》是一篇悼念林肯的哀歌,但作者在个人的哀思中抒发了对美国辽阔的原野和诗人故乡曼哈顿的风物,以及战时生活的感怀与眷恋,这些与国家、民族、人民生死相连的形象不但渲染而且加深和扩大了诗人的悲怆之感,诗篇主题的悲剧意味更浓厚。惠特曼自称为“宇宙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流贯着一股渴望民族复兴、统一的情感热流,并且《草叶集》的“我”始终召唤未来,奔向未来。
《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煤》、《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诗篇,都分明受到《草叶集》的影响。这种影响使郭沫若的抒情主人公一方面仍然具有“拜伦式英雄”的以自我为中心,力拒世俗,为冲破封建樊篱而不屈不挠的挑战精神,而且他的“个人性”的表现也同样充分而凸出,这种个人性与时代性民族性始终如水乳般胶着在一起,因此,这个“个人”俨俨是新生民族的代言人。《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中对“葱俊有进取气象”的祖国的钦慕眷恋之情,以及《女神》中对太阳、日出、早晨、春日、山岳河川等美好明朗事物所倾注的挚情厚意,无不是郭沫若从一个“更生了”的个人的角度唱出的对一个正在新生、复兴的民族的颂歌,这是一首狂放豪迈、勃勃生机的赤子之歌。因而,《女神》中的抒情主人公也和惠特曼一样,召唤着民族的未来,而其自身即是一个从旧秩序中脱胎而出的“新人”——一个因为拥有未来而欢欣跃动的“新人”!
二
应该看到,对旧的世界《女神》中的抒情主人公有一种超乎其上的高傲姿态,爆发出鲜有的冲击力、破坏力;然而对新的世界新的时代这个主人公虽然充满渴望,他所瞩望的新的世界在其心目中却是朦胧混沌的,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他还捉摸不到未来世界的影像。这使他感到痛苦,感到孤独,在其强悍骁勇的个性气质中潜存着深刻的软弱无力的因素。《女神》自我形象的这种矛盾性质体现了郭沫若当时的精神状态及烙刻在诗人身上的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过渡时代的印痕。这种情绪面貌和心理状态体现于《女神》中,即是抒情主人公柔弱、郁闷、感伤、悲哀的倾向,这给《女神》在总体的雄丽基调上染上了一抹“忧郁”的色调。这种“忧郁”与“雄丽”是并存于《女神》中的,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
郭沫若前期创作中的这种感伤主义倾向,是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息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美感上的“忧郁美”是西方浪漫派的“专利品”。恰尔德·哈洛尔德终生抱定悲观和厌世主义倾向:“尘世上的荣誉,野心和斗争”,“都不能用那尖刀,在他心坎上刻下深痕”。在谈到拜伦本人时,海涅写道:“他们因他忧郁而怜悯他。难道上帝不也很忧郁吗?忧郁正是上帝的快乐。”(注:《巴黎通信》第四十四封。)雪莱则说:倾诉最哀伤的思绪的才是我们最甜美的歌。惠特曼的天性中有个“巨大的悲剧因素”(注:盖·威·艾伦:《孤独的歌者》。),这甚至影响到他个人的爱情生活,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流露出一种无法排解的忧愁与伤感之情。郭沫若把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概括为“主情主义”,其内核为:崇拜个人的内心世界,极端重视个人的情感方面。然而维特短促的一生一直处于忧伤、苦闷之中,情感脆弱,郁郁寡合,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无血色的苍白的忧郁的象征或化身。可以说热衷于忧郁的情调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艺术特征。朱光潜指出:忧郁对于浪漫主义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世纪病”,“大多数浪漫主义者都是个人主义者,所以都各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世界的幻想。世界并不总是那么柔顺,于是他们就起来反抗。就像小孩子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发脾气一样,浪漫主义者们也是远远躲在一角,以绝望和蔑视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他们不胜惊讶地而且满意地发现,在忧郁情调当中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意味。这种意味使他们自觉高贵而且优越,并为他们显示出生活的阴暗面中一种神秘的光彩。于是他们得以化失败为胜利,把忧郁当成一种崇拜对象。”(注:上引见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
郭沫若在《女神》及其他前期作品中表现出的感伤主义倾向,其产生的心境与西方浪漫主义是一致的。于是,在《女神》中出现了歌颂悲哀、歌颂死亡、歌颂厌世者的主题,诸如《夜》、《死》、《密桑索罗普之夜歌》、《死的诱惑》等等。“密桑索罗普”意为厌世者,据郭沫若原注此诗是呈现给《莎乐美》的作者王尔德的,后来郭沫若说,《密桑索罗普之夜歌》“是在痛苦的人生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是自己惨淡的血液(注:《创造十年》。)。
满怀着改革的热望,蓄积着创造的激情,郭沫若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以一种摧枯拉朽、锐不可挡之势开始了向整个旧世界的挑战!然而整个旧的社会势力如此强大,整个传统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他反抗,他战斗,无论如何也难冲破封建罗网;他苦闷,他彷徨,人生中的幻灭和哀伤使他时常悲叹和哭泣,悲观忧郁,自艾自悼,被一种巨大的怀疑精神折磨着,痛苦不堪!于是他放下了沙场勇士手中嘹亮震耳的军号,又拿起了悲观厌世者手中的芦笛,弹奏了一曲曲缠绵悱恻、意懒情倦的哀歌。这就是那个强有力的个人唱出的歌?当然,应该指出,郭沫若前期创作中的这种“忧郁”倾向反映了“五四”一代先觉知识分子的情绪和感受,而且他绝不陷入一己的哀伤中而不能自拔,恰恰相反,他的忧郁正是其改造现实的热望被现实的冰冷浇灭后产生的。因此,在情感类型上,郭沫若诗作中的“忧郁”美与西方进步的浪漫主义者有更直接的联系,而与那种耽溺于往古(郭沫若较少回到远古和中世纪中去),专事于人生“夜的方面”、充满阴暗神秘色彩的保守浪漫主义者有一定差异。
三
郭沫若前期作品中浪漫主义主人公忧郁感伤的心理倾向是他们与现实接触、进而牴牾、矛盾、无所适从的直接结果,即他们发现自我作用和自我价值在强大的现实异己力量面前不仅很难实现而且太软弱无力了。于是作为一种逃遁,或者作为一种现实的反抗,他们回归到自然中去,在大自然温暖而有力的怀抱中达到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肯定与张扬,达到对平庸卑俗、腥臭污秽的现实世界的超越,这时候,这个抒情主义公又与自然拥抱在一起,自然成为他精神上的寄托和理想之塔,以至于最终归宿。于是,我们看到,在郭沫若的前期创作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成为他着力表现的基本母题之一。
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和艺术表现,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揉和在一起,而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其直接来源是西方浪漫主义哲学运动和在此基础产生的浪漫主义文学。郭沫若说:“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思想接近了。……我因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注:《学生时代》。)歌德对他接受泛神论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泛神论思想和自然观,他指出:“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而等其生死。人到一有我见的时候,只看见宇宙万汇和自我之外相,变灭无常而生生死存亡的悲感。”他认为自然是唯一神之所表现,自然便是神之庄严相。所以他对于自然绝不否定。“他肯定自然,以自然为慈母,以自然为朋友,以自然为爱人,以自然为师傅。”(注:见《文艺论集》。)不难看出,西方浪漫主义者关于自然的认识和观念成为郭沫若自然观的基本前提。在自然观上,西方浪漫主义者大都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直接启迪。他的口号是“返归自然”,其内质为:回到大自然和人的自然状态中去。这个口号几成为浪漫主义者的共同原则。同时德国浪漫派哲学运动(此采用朱光潜的说法)也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谢林指出:“人所以能够了解自然,就是因为它类似于人,是一切精神活动的表现,其中有理性和目的。”(注: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大自然的“美”成为现实的“丑”的对比,他们以此表达自己对现存秩序的否定和对所谓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的厌恶。因此,崇拜自然首先体现了浪漫主义者的反封建、反资产阶级文明及其整个观念和意识的总体趋向,即通过自然崇拜寄寓自己的情怀,并在自然中达到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以此张扬个性,维护“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的人生信条。与此密切相关,自然也成为浪漫主义者“受伤了的灵魂”的精神安抚和慰藉,自然成为他们的终极归宿和目的。因此,在浪漫主义者那里,自然不仅成为抒发个人的理想的最好依托,而且更是他们忧郁感伤情绪的最好体现,大自然只是在蒙上一层晚云的纱幕或者变得一片荒凉的时候,才最使他们入迷(以德国浪漫主义最为典型)。这两种倾向均与浪漫主义者在资产阶级“现代文明”中找不到自己的“根”相联系,它显示着解体时代一群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
人与自然之关系和泛神论思想在郭沫若的前期创作中基本上体现为两大倾向:首先是借助泛神论在自然中强化和加深其“个性解放”的思想,即在自然中重新达到自我肯定甚而至于自我扩张,并以此与整个封建制度和传统观念对个性和情感的抑制相抗衡相对立。上引郭沫若关于泛神论思想的一段话即是这一思想的最恰切注脚。这种倾向在郭沫若那里就是要求人们适性任情,有一个赤裸裸的纯真的个性和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对一切既成道德、宗教、一切戒律准绳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破坏力,体现了郭沫若冲破封建束缚,弘扬个性和自由的人生追求。这时候,郭沫若作品中的自我要效法自然,以自然为楷模,在自然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启悟中增强信心和勇气,所以,自然成了其作品中抒情主人公自我力量的延伸和外化。
其次,自然又成为这个抒情主人公的一种逃避。这时候,这个主人公对自然的态度是亲切的,爱恋的,“自然与之以无穷的爱抚,无穷的慰安,无穷的启迪,无穷的滋养”(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见《文艺论集》。);“我已几天不见夕阳了,/那天上的晚红,/不是我焦沸着的心血吗?/我本是‘自然’的儿,/我要向我母怀中飞去!”对自然这种亲恋的、视同情人的态度,对诗人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是一种最甜美最宁馨的精神安慰,他愿意在大自然慈母般的怀抱中,在爱人的爱抚下,忘却尘世所加予他的伤害、痛苦。同时,诗人这种态度的产生毫无疑问起因于内心所感得的焦虑和悲伤,亦即一种忧郁情绪,正是这种过分悲哀的情绪使他太觉痛苦难耐,催迫他隐遁于自然中。因此,本质上,诗人忧郁的倾向与其对自然的态度是相通的,二者在这里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郭沫若《女神》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体特征即如此,其核心为:在自然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得其所在的神性状态中见出人生的自然状态与人的情感的自然状态,其思想基础依然是郭沫若所崇信并张扬的“个性解放”。
这种对田园生活、远古生活和儿童生活的憧憬同时也是西方浪漫主义热衷的题材,在纯朴的民俗风土中深藏着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郭沫若在这里又与自己的先驱者站在一起,这种思想上的共鸣,就象一条看不见然而也拧不断的纽带,把他和这些出类拨萃、才气横溢的天才人物联系起来。
收稿日期:1999—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