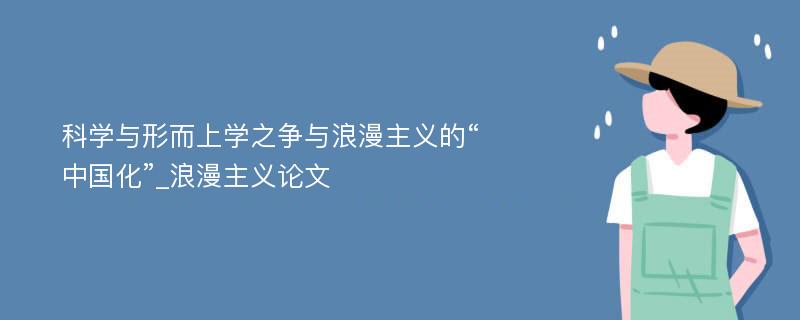
科玄论争与浪漫主义的“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异质文化的交流是一种冲撞、化融的过程。当本土文化接受、容纳来自异域的某一形式或概念时,都将“本能”地使它产生变异,并予以同化。20世纪初,中国文坛在接纳西方浪漫主义概念时,亦有这样的“中国化”的进程。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号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的第6项要点为“科学而非想象的”,自此,科学这们“赛先生”与民主——“德先生”便一道成为“五四”精神的代表。当时,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激进派,不遗余力地宣扬、传播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实践性的方法、导向,而且还成为一种带有政治性、社会性的价值信仰。对科学主义的推崇、膜拜,蔚然成风,它以主潮的地位覆盖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包括文学界)的每一个领域。
当外来的科学观念演化成几近于宗教性热潮时,本土的传统观念的守护者便自然地展开狙击。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中国赴欧观察组成员的梁启超返国之后,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对科学主义的功用产生怀疑:“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作为清末以来鼓吹西方文化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忽然转向,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对科学万能的倾向提出质疑,要求重新审视精神的价值。其大旨是:人生观的特点在于主观、直觉、综合、自由意志、单一性这五点,而科学的客观性、逻辑法、分析方法、对因果律的推崇等,恰与之对立,故科学不能提供人生观。同年4月,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予以反诘,他称张君劢等为“玄学鬼”,意即沉溺于虚幻之境中。丁文江等认为,传统精神、直觉、美学、道德、宗教感情等,实则为虚幻的玄学,只有科学精神才能对人生观的树立起积极作用。因科学能使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这场论战迅疾地在中国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张利民1996年在《科学与人生观》一书“重版引言”中归纳道:“随着论战的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论战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也著文参战,主要支持了科学派反对玄学派,可称之为‘唯物史观派’。通过这场论战,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思潮:现代新儒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初步展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时,对这场论战并没有作出谁赢谁输的判决,但从论战后的中国文化思想界的总体趋势来看,科学派取得了极大的胜利,玄学派基本上消隐了。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以科学的原则来导引新人生观,来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主张,获得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普遍认同与接纳。因此,不管从怎样的高度上来评价这场论争的意义,都不会显得过分。它对于中国社会其后发展的影响异常深远,在文学界则表现为导引写实主义的盛行及本文所要论析的浪漫主义的“中国化”。
从笔者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看,中国主要的现代作家并未直接介入这场论战,但在间接上多为波及到,而且影响颇深。因篇幅关系,无法多加征引。现关键的问题是这一“科玄论争”如何渗透、影响、导引了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流派的选择与重塑。
对此,郁达夫的《文学概说》中关于自然主义的一段论析有较明显的脉络可寻。他认为,近代人崇尚科学精神,“科学的精神所要求的,是实在的事实。”运用到人生问题上去,“由个性综合而成的社会生活,和使社会成立的环境的状态,就成了研究人生问题的重心。这一种倾向,渐渐的推广开来,结果文学界也感受了这一种习惯,以此为根据,文学上的表现法(自然主义)也就发生了。”郁达夫认为,科学精神的推广将促使自然主义(在当年的概念近似于写实主义,而后发展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中国兴起。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谈得更清晰、具体:“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它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科学有关。……进化论,心理学,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男女问题,……都是自然派的题材,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因此,中国现代作家对写实主义(而后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认同,与这场科玄论争之后唯科学主义精神(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的盛行是分不开的。
逆向审神,唯科学主义的推崇却阻隔了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原汁原味地为中国文学界所接纳,使它产生了“变异”。茅盾在《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一文中,有段话很值得深究:“可惜时代太晚了些,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这里,浪漫主义的“别的原素”究竟是什么呢?这就必须回到对西方浪漫主义原初的本质定性的探询。西方浪漫主义思潮源自卢梭,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以偏激与尖刻震惊了当时的思想界,其批判矛头指向了正在兴超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促成这一文明的科学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辉煌了现代文明,但同时也带来它的负面效应: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的泛化让人的价值与尊严沦落,技术思维的隘化使人的生存诗性丧失等……。这一异化的现实使人文精神转向低迷,也促发了人们的警觉与思考。以卢梭为源端,历经康德、施勒格尔,直到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他们对与科学主义一体化的“现代性”的批判,对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探索,汇成了一股浪漫主义的哲学、美学思潮,其波及面从18世纪末延续到了20世纪末的今天。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归纳道:“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也可以说,浪漫主义思潮的发端与质的定性,是源于对科学主义与工业文明,以及“现代性”的抗衡。
但中国20年代初的这场科玄论争却压抑了新儒学派对人文精神的强调,使科学主义上升到万能的、“新的宗教”的地位。显然,中国文学界若要引进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其反科学主义的要质便成为茅盾所指出“不适宜于今日”的“别的原素”,予以剔除;其对生命的本真完美与异化分裂,个体生命的存在有限性与超越的无限性,感性生命的经验与神性的超验等命题的探询,便成为凌虚蹈空的“玄学”,予以否定。西方浪漫主义被异化了,“中国化”了,它的反科学主义要质,它对“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要义,它回归自然的本真性等,均被扬弃、排斥了。余下的只是与中国古典美学“诗缘情”接轨的主情主义和文学创作的一般心理能力——想像这两大成分。在而后的时日里,由于马克思主义日渐成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文学艺术作为政治斗争的辅助工具,它必须正确地科学地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因而“理想性”又作为一项重要的成分注入了中国浪漫主义的概念中。可以看出,它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原初的内质有了一定的距离,产生了变异,即“中国化”了。
如果上述浪漫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能确立的话,那么困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些命题便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答。例如沈从文在《水云》中说:“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为什么他会孤寂地自称为“最后一个浪漫派”呢?这难道不正是他因为对所崇奉的西方浪漫主义真质已被扬弃所发出的感慨吗?因此,他不无感伤地写下了与上述马丁·亨克尔界定浪漫主义的内涵完全一致的一段话:“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这首诗当然是“玄学”的、形而上的,带有终极性追寻的、属于心灵的“诗”,例如《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