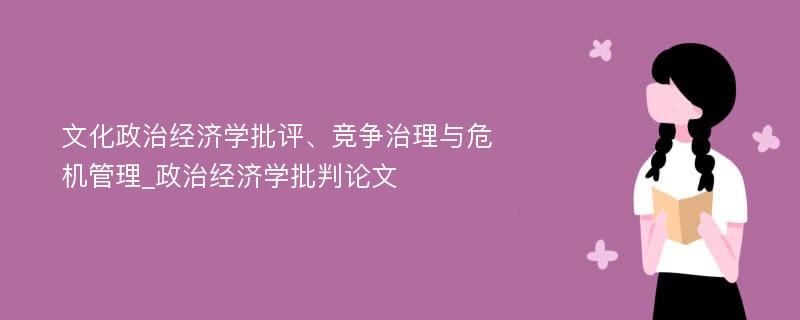
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竞争式治理与危机管理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竞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6)04-0099-008 通过继承和发展散见于马克思著作中不成系统的政治思想与国家学说,从而对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批判,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术旨趣与理论使命。在20世纪70年代,以普兰查斯与米利班德关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工具论之争为契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重新检视并创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任务,并由此激发了二战后整个西方学界国家理论的复兴。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理论较多地停留于内部争论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批判,未能很好地回应诸如“多元主义”、“民主精英主义”、“合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挑战,也没有充分地参与诸如“国家能力”、“治理”等新理论关注点的探讨。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在西方世界一片福山式“历史终结”的狂欢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日益边缘化。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以2002年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杰索普出版《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了新的复兴。杰索普早期致力于梳理马克思国家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各派国家理论的思想资源与方法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1982)一书中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须整合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接合方法(articulation)。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归位》中,他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通过超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并借鉴卢曼的自生成系统理论、法国调节学派的调节(regulation)理论、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提出了“策略关系方法(strategic relational approach)”的综合性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西方政治学与国家理论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杰索普逐渐转向利用策略关系方法并以一种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的方式,通过整合、空间尺度(scale)理论与治理(governance)理论,建立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理论”,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与重构进行了批判分析,主要成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调节方法及其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归位》(2007)。这些论著有力地回应了各种来自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挑战,并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关于全球化与国家、国家建构、治理理论等议题的热烈讨论中给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具有较强现实解释力的批判分析。 2008年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管理与治理失败的全面检讨与反思。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资本主义固有危机倾向的判断,并重新激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与现实批判。2013年,杰索普出版了合著《文化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的文化归位》,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并通过竞争式治理概念的引入推进了关于治理失败与元治理的分析,最后对当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及其危机管理的危机给出了有力的批判性解释。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不仅为我们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也对我们思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籍以批判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理论传统与思想资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清晰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形式对应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应地国家作为总资本家的代理人,其管理方式的变革也对应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所谓自由、平等、民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与交换关系的政治表达,试图以法律的平等来掩盖资本主义内在的剥削与不平等;国家可能表现出非统治阶级工具的特征而更多地作为一种相对的自主性力量或维系政治力量相对平衡妥协的粘合剂,但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资产阶级管理委员会的本质,其目标是为资本积累提供政治统治、经济调节和社会管理的支持。 不过,正如波普尔所评论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分析从根本上说都是“本质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政治、法律与国家并不具有相对于经济的原初重要性。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总体之本质的精辟分析,但对分析具体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却助益不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复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一方面以破除经济决定论与国家工具论的桎梏为目标,另一方面试图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中引入“制度主义分析”。比如,以霍洛维、巴维等人为代表的“资本逻辑学派”所发展出来的国家理论“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以及存在于国家、经济与市民社会之间复杂联系的真知灼见”②。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则通过“结构的多元决定”框架给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的独到见解与批判。此后,奥康纳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的分析、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分析、奥菲关于“福利国家的矛盾”的分析、法国调节理论学派关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与国家调节危机的分析,都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引入更具体的制度要素或范畴,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推进和深化,并在新的现实中给出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解释。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杰索普也充分认识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须给予制度重要的理论位置,必须关注制度如何运转、如何再生产、制度实体与制度的治理、制度与制度间的关系、制度与系统的关系及系统环境的控制等议题。③而要实现这一理论目标,既要接受“马克思的前学科(predisciplinary)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发”,又要以“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的方式利用社会科学家广泛的学识和研究”。④基于这种方法论自觉,杰索普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理论》中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根本,通过整合制度主义、话语理论、调节理论与自生成系统理论,提出了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建。在200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中,杰索普又充分整合和发展了治理理论、空间尺度理论,提出了治理失败与元治理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理论,并据此分析了西方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与重构趋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 在2013年出版的《文化政治经济学》中,杰索普则进一步提出了对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所谓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将文化分析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关注由文化中介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与意义的生产过程。借助这一个理论概念与分析工具,能够提供对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与镶嵌于其中的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更有力解释和批判,因为社会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意义的生产、循环与交换所达成的。⑤与制度分析的引入一样,文化分析的引入是为了深化和推进而非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换言之,随着资本主义运行系统及其关系再生产的日益复杂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理解与批判必须相应引入新的分析要素与范畴,这既是丰富与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路径,也是进一步深化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本质与运作逻辑的理论要求。资本主义是一个“生态系统”,它主要由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与宗教等系统构成,“这些系统会自我维系、自我组织和自我再生……但它们的共存与共同演化则有赖于彼此的相互依赖”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既具有独立的意义又具有整体的意义。 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之一的葛兰西就已经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hegemony)的诸多洞见,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而言国家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比对政治社会的“强制权”更重要,“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⑦,资本主义与国家统治的生产与再生产实际上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葛兰西的影响下,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进一步揭示了“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地位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关键作用。⑧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也由此被视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策略,以至于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的理论代表拉克劳和墨菲甚至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与国家理解为“话语”的建构,权力关系、政治实践与社会斗争都是话语领导权的争夺。⑨ 杰索普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主张接受话语理论的一些有益分析,但反对将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简化为“话语还原主义”;同时,既要充分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分析,又要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具体分析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积累方式的多样性相适应的文化功能,而且对文化的理解要扩展至包括思想、知识、理论与科技等要素在内。⑩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第一,它强调文化演化机制塑造社会结构的作用,特别是统治与领导权的生产;第二,它强调应对“问题”或“危机”的个体、组织与社会的学习机制;第三,它强调领导权的巩固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取决于结构、话语、技术与制度四个重要因素;第四,它强调经济与政治的想象与设计是一种由物质现实限定的、由文化或话语所中介的意义生产。(11) 杰索普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仍是遵从葛兰西主义传统,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领导权进行分析,但主要关注于资本主义的积累策略与文化策略的“相互塑造”,如战后西方福特主义积累方式(规模生产与规模消费)对应于通过福利国家形式建构的福利主义文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福利供给塑造国民对国家的依赖,反过来又通过社会的福利主义文化来支撑国家的合法性;其次,通过整合“话语理论”的一些观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始终存在着话语领导权的争夺或反领导权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它们既来自统治阶级内部也来自于哈贝马斯意义的生活世界之中,话语领导权的争夺会侵蚀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与意义的再生产,从而破坏资本主义积累策略、国家形式与文化领导权的结构一致性,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第三,与过去强调资本主义的多样性(varieties)不同,今天的资本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多变性(variegated),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复杂化与多变性使其积累策略的制度化与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反过来相对稳定的积累策略也成为了积累方式演化的阻碍,这一困境导致了借助国家形式与文化领导权来中介的“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出现混乱;第四,当前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正在从福特主义的工业生产转向后福特主义的知识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因此对经济生产来说资本主义需要将学习与知识转化为生产绩效,对领导权而言需要建立可以指数化的文化政策范式,对国家调节以及通过国家的中介或组织起来的治理而言需要建立起个体、组织与社会的网络式学习机制。(12) 二、从治理失败与元治理到竞争式治理 利用文化政治经济学方法,杰索普通过引入“竞争式治理”的概念,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治理失败与元治理”理论。治理作为与传统的统治相对的范式,它代表着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政治运作与政府管理的想象与实践。治理强调包括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在内的“多中心”合作共治,在结构上通过多元主体的网络式伙伴合作,在运作上通过多元参与、协商与谈判,在关系上强调平等的互动与反思性沟通,在资源上强调基于多元主体的自组织之上的共享与整合,从而达致“善治”目标。 从表面上看,“治理的兴起反映了传统公共行政面临着重大挑战,诸如经济发展及其全球化,消费者、纳税人和公民的要求越来越高,信息管理和传播领域的技术进步,前所未有的社会复杂性与多样性等等”(13)。但从根本上说,治理话语的出现表征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市场万能到市场失灵、从市场失灵到政府理性、从政府理性到政府失败的危机应对历程,而治理则作为一种新的总体性解决方案被寄予了殷切的厚望。无论是关于国家能力与国家失败的国家建构理论,或是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理论对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之间伙伴合作的推崇,还是试图超越“左与右”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激情实践,都表达出西方社会对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认识与恐慌,以及试图通过治理来探寻不完美的市场与不完美的政府之外的完美机制的信念与理想。 在“治理与善治”甚嚣尘上时,杰索普利用其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以及源自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并论证了“治理失败的风险”,对日渐占据主流的“治理崇拜与迷思”给了一记当头棒喝。其在1999年发表《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一文,成为了治理研究中被广泛引用的权威文献。杰索普指出,对治理的理解必须放置于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积累策略与协作形式之中。广义的治理包括无秩序的交换(自发调节的市场)、等级性的控制(强制协调的国家)、自组织的治理(水平网络与伙伴关系)三种形式,前两种治理形式通常单纯强调市场力量或者国家力量,后一形式则强调市场、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网络式伙伴合作,当前所热烈讨论的“治理”实际上就是狭义的第三种治理。(14)事实上,三种治理形式及其协作关系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之中,不过在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与积累策略影响下存在着主导性的治理形式与治理力量,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治理、福特主义时代的国家治理以及当前的自组织治理。(1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都是广义的治理失败。就狭义的治理而言,同样也存在着失败的风险。治理失败的风险主要产生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治理的成功取决于多元参与主体的目标一致,要达到目标一致本身已经极其困难,而在治理的动态演化过程中会存在目标冲突,当目标一致性无法维持时,治理就有失败的风险;第二,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如市场力量、国家与公民社会事实上有着源自于其本质的不同运行逻辑,在治理过程中,某一治理力量的运行逻辑会有侵略或统治其他运行逻辑的倾向,当不同运行逻辑发生冲突与龃龉时,治理就可能失败;第三,当今的资本主义运行系统日益复杂化,系统的复杂性从根本上内含了不可治理性,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尽可能简化复杂性、降低噪音和干扰,但这种简化本身可能因对复杂性的把握不足而导致治理失败。(16) 要应对市场失败、政府失败和治理失败,需要在组织间的协作中引入反思性“元治理”。元治理亦即“治理的治理”,其根本目标是为各种治理力量的协作关系、参与过程、合作网络提供宏观的制度安排和行动规则,以达成各种治理力量与机制的相对平衡。与认为国家在治理中需要角色弱化的主流观点不同,在元治理中国家扮演着首要的角色,其责任是为治理建立环境与框架,使自身成为多元治理主体的协作平衡点,而非制定和主导具体的治理安排与策略。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建立治理体系的规则秩序,从而使伙伴合作关系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律化;建立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对话平台,在决策网络中鼓励充分的策略博弈,从而形成集体行动的统一目标;建立信息交换与反馈机制,允许在治理过程中反思性地修正目标,从而维持共同目标的一致;建立治理主体间的学习网络,互相深入理解彼此行动理性与认知模式的差异,从而加强基于谅解与宽容团结;充当“上诉法庭”,当治理主体发生目标争议、利益冲突和行动纠纷时进行协商调解,并优先维护“弱势方”的利益和参与机会。(17)不过元治理自身也具有失败的风险,因为“不存在对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实现完全或总体控制的情况——治理必然是不完全的,它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失败”(18)。尽管存在着治理与元治理失败的风险,但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未来仍旧依赖于治理与元治理安排的有效构建。 无论是指出“治理的要点在于:目标定于谈判和反思过程之中”,还是强调元治理的反思性信息交换与反馈、组织与治理主体间的学习网络,杰索普的治理理论都隐含着对“文化”与“意义生产”要素的追求。因此,在其新近关于治理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理性、意义、知识、学习等概念被赋予了更加明显且重要的地位。杰索普认为,较之基于计算模式、规则设置与行动规范的“制度安排”,策略活动者的认知与反思理性、主体间学习与理解的“文化机制”对于治理的成功更具有关键的影响;较之于基于共同利益的治理目标的统一与维持,基于意义的生产与复制的治理目标一致性更具有稳定性,通过话语的过程与机制来建立经济秩序与文化领导权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利于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成功提供支持。(19) 作为治理失败与元治理理论的补充,杰索普进一步提出了“竞争式治理”的概念,它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它指向的是资本主义总体的经济想象与积累策略竞争以及作为经济“调节”的治理方式竞争。(20)杰索普的治理理论始终立足于资本主义结构限制下的积累策略、政治策略与领导权运作的分析框架,三者的结构一致与协同运作是确保资本主义的积累增长、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基础。事实上,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到福特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想象与积累策略都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统治地位之上。这种积累方式的明显统治地位,不仅保证了经济想象与积累策略选择的一致性与稳定性,而且通过“经济的文化化(culturalization of economy)”与“文化的经济化(economization of culture)”的双重过程不断得到复制。就治理而言,这有利于维持资本主义“历史集团”的目标统一,也降低了资本主义经济调节与治理的复杂性。但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出现了日益多元的竞争性经济想象如工业经济、金融经济、知识经济等,从而在资本主义“历史集团”内部产生了不同积累策略为争夺积累方式统治权的激烈竞争。(21)对于资本主义的治理而言,这种因经济想象不同产生的积累策略竞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为资本主义提供不同的治理方案选择,从而也拓展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它又破坏了资本主义积累策略、政治策略与(文化)领导权的结构一致性,或者说积累策略的竞争导致了政治策略与领导权的竞争,竞争对目标统一的侵蚀增加了治理失败的风险。(22) 第二,对于狭义的治理即自组织的网络式治理而言,竞争式治理则更多的是从应对治理失败出发。它强调具有不同目标与策略的行动者在治理过程中通过选择性的恰当话语表达与意义交换,在彼此之间重新建立起治理与协作的语境,通过承认之前政策或治理策略的失败并修正出新的政策或治理策略,从而实现基于“妥协的不稳定平衡”之上的利益联盟。(23)竞争式治理既允许利益目标不同的组织与行动者充分表达其治理策略和利益主张,又鼓励不同的组织与行动者反思性地学习与研讨不同的治理策略,最终将治理建立在知识竞争和学习演化的结果之上。因此,竞争性治理实际上就是建立起一种基于理论与知识领导权生产的政策范式。其中,知识分子、智库、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应当扮演更加重要的治理角色。(24)不过,在理论与知识领导权的生产中,始终会遭遇到反领导权(counter-hegemony)的斗争,而且无法避免出自意识形态的理论偏执,从而导致基于学习失败(learning failure)、学习危机(crisis in learning)的竞争式治理失败。(25) 三、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危机管理的危机 2008年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马克思《资本论》与资本主义批判的重新审视。在此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更新与发展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总体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首先与资本过剩积累相关,当前的危机与过去的危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固有周期性危机的判断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与解释力(26);其次,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增长范式与政策范式的必然结果,危机再次证明了“自由市场是经济生活瘫痪的基础”这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终极批判。(27) 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稍有不同,杰索普并不满足于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进行简单重复与阐释。杰索普指出,资本主义本质上具有无法避免、无法克服的周期性危机、调节性危机,以及最终通过资本主义国家形式所中介和总体化表现出来的系统危机。与其说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表现为全球金融危机,还不如说全球金融危机是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一个面向的表达或率先爆发。 首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内在不完美的经济制度,其经济活动呈现出周期性危机独自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自我修复的特征。事实上,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是在从工业经济的积累方式占统治地位走向工业经济、金融经济、知识经济争夺积累策略统治权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既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主义积累方式造成的积累过剩危机,也是其与福特资本主义争夺积累策略领导权导致的危机。福特资本主义建立在空间相对固定的、规模生产与规模消费的实体工业经济之上,而金融资本主义则建立在空间流动性超强与快速的货币及其衍生产品的生产之上,两者在运行逻辑上有着相异的要求。当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尽管表现出金融经济与货币资本积累的强烈特征,但总体上仍然建基于工业经济之上,所以金融经济的领导权地位对工业经济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并最终由金融危机导致了实体经济危机。(28)虽然“资本积累非常需要这样一些竞争性策略,从而在试错之后采用”(29),但显然金融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策略失败了。 其次,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一整套标准、机制和机构来实现”(30)国家调节。调节从根本上说是针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危机管理,然而调节或危机管理本身可能成为危机的根源。事实上,竞争与统制相结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自我调节与国家调节相结合,一直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客观功能所需,但是这种结合本质上是矛盾的,它们之间运行逻辑的不同会造成结合的失败,这是资本主义调节的一种固有的、无法根除的危机倾向。此外,国家调节与干预机制的作用发挥需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内获得稳定性,而一种稳定而有效的调节机制的形成本身也是一个将可以给出的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方案组合起来的复杂过程。比如,从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受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保证“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与积累结构稳定的重要“妥协性安排”。(31)但是当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与积累策略发生变化,而旧有的、已经稳固化的调节机制不能适时变革从而形成新的有效调节机制时,那么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的调节性危机。(32)今天的资本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建立在思想、知识和信息之上的新经济,“一个结果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仅受产权和竞争约束的个人追求财富会把经济引向资源有效利用——现在对经济政策的引导比在旧经济中更为糟糕”(33)。如果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自我修复过程中,一种新的稳定而有效的调节机制无法及时被创建出来,那么危机的周期将更长、自我修复将更困难。 因此,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仅是积累方式的危机,也是资本主义调节与危机管理的危机,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塑造、交互表达的关系;全球金融危机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积累策略与(去调节化的)调节策略的危机,也是当前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新调节策略的构建或创新危机。(34)除了继续强调市场失败、国家失败和治理失败之外,杰索普还特别指出了当前资本主义调节性危机的“文化失败”因素,具体表现为调节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知识危机及其政策范式失败。换言之,当今的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确立“新经济”积累体制的发展过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调节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政策范式逐渐失灵,而在为应对“新经济”所需的调节与危机管理创建之时又出现了理论与知识的匮乏。(35)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时也给出了相似的判断,资本主义正面临着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市场行为与国家调节行为的不可控性,特别是能够控制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学出现了理论与实践危机。(36) 第三,资本主义的稳定运行取决于积累策略、政治策略(调节与治理方案)与领导权三者的结构一致性,而这种结构一致性的生产与再生产通常是通过某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中介和维持,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危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集中表达。战后西方近三十年的“黄金时代”得益于资本主义建立起与福特主义积累策略相适应的政治策略即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并通过福利主义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维持了三者的结构一致。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结构一致性逐渐被打破,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陷入了深刻的系统危机之中:(1)经济危机,产生于从规模生产、规模消费的福特主义增长方式向灵活生产、知识创新的后福特主义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传统积累策略的失灵与新积累策略的未确定;(2)财政危机,产生于经济危机扩大与福利开支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3)政治危机,包括福利国家的僵化、低效、无能与官僚主义以及凯恩斯式国家干预与调节策略的失灵;(4)话语危机,既包括对福利主义的反对,也包括资本主义危机管理策略的话语权争夺,如新保守主义、新共同体主义、新自由主义、新社会民主主义等;(5)全球化的侵蚀,包括民族国家对本土跨国资本与跨国公司的控制力减弱,亚国家的地区与区域合作主义对中央经济控制力的挑战,超国家的国际机构规制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冲击。(37) 当前资本主义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危机的延续与深化——在全球化的后福特主义经济中它终将衰落,也表征着试图重构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失败以及新社会民主主义与新保守合作主义等策略的无能。(38)在杰索普看来,资本主义的未来应该走向在全球化与后福特主义经济范式中确立起知识经济的统治地位与积累策略而非金融主导的积累(finance dominated accumulation),并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体制(Schumpeterian Workfare Postnational Regime)。这种体制在增长方式上强调知识创新,在再分配上强调社会政策服从于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需求,在调节空间上强调全球的、跨国的、民族国家的、区域与地方的协调合作,在治理模式上强调自组织治理与国家的元治理(39),在文化领导权上强调建立一种“学习性社会”和知识消费文化。(40)杰索普指出,这样一种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缓慢且困难重重的过程,在其建立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资本主义危机,在其建立之后也无法克服资本关系内生的结构矛盾与危机。 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不仅对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推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与系统性危机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此外,杰索普关于治理、元治理与竞争式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其竞争式治理强调允许多元治理主体表达利益差异并提供竞争性治理策略,强调多元主体基于相互谅解、理解、学习与讨论之上的治理策略选择,强调知识与理论的治理作用以及知识分子的治理参与、知识竞争等,都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与实践具有相当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①戴维·米勒:《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8页。 ②Jessop B.,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52. ③Jessop B.,Institutional(Re)t urns and the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33(7),2001,p.121. ④Jessop B.,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1. ⑤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viii. ⑥Jessop B.,Regulationist and Autopoieticist:Reflections on Polanyi's Account of Market Economies and the Market Society,in New Political Economy,Vol.6,No.2,2001,p.217. ⑦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425页。 ⑧参看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35页;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2-264页。 ⑨参看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⑩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4. (11)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p.23-25. (12)参看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Chapter 2,5,6,7. (13)何子英:《杰索普国家理论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14)参看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载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5)Jessop B.,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52,216. (16)参看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载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2、75页。 (17)Jessop B.,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242-243. (18)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载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9)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p.35,79,166. (20)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173. (21)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183. (22)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p.243,248. (23)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317. (24)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p.282,321. (25)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410. (26)弗雷德里克·博卡拉:《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27)西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 (28)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p.416-417. (29)Jessop B.,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205. (30)米歇尔·于松:《资本主义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183页。 (31)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 (32)Jessop B.and Sum,Ngai-Ling.,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6,chapter 11. (33)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1-592页。 (34)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406. (35)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395. (36)参看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九、十章。 (37)Jessop,B.,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81-94,174-177. (38)Sum,Ngai-Ling and Jesscp.R.,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434. (39)Jessop,B.,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p.250-254. (40)Sum,Ngai-Ling and Jessop,B.,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3,p.429.标签: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危机管理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