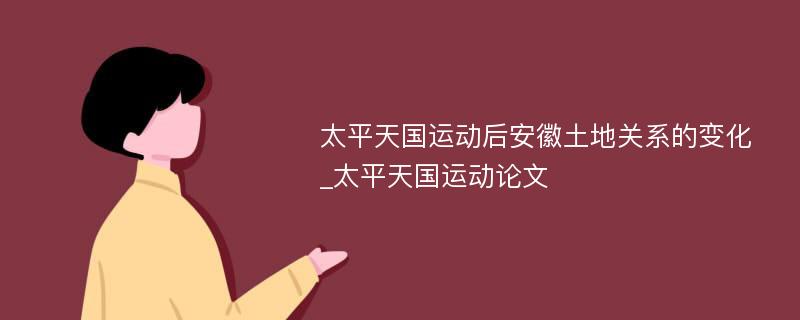
太平天国运动后安徽土地关系的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安徽论文,变动论文,土地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湘军的地雷轰开天京的城墙,焚烧天王府的火光照红天空,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宣告了悲壮的命运结局。然而,这场被称为当时中国社会“大爆炸”(马克思语)的太平天国运动如同战争的炮火留给那个时代的余响并未消失,中国大地在经历大海波滔潮来潮去的洗礼之后已非往日的模样。本文以太平天国建立最早、历时最久的根据地安徽省为例,着重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后安徽农村土地关系的新变动,管窥中国最大规模农民运动强烈的历史震撼。综括点滴,不妥之处祈请同仁指教。
一
战局底定,地主阶级反攻倒算,开始了新的土地兼并过程,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最凶残的湘淮军官僚地主,利用政治特权,在安徽大肆兼并土地,大土地所有制在皖北很快重新建立,土地耕种者复又沦为佃农。
淮军将帅的家乡安徽省是军功人员的集中地。所谓军功,是指由于参加军事组织镇压人民起义而获得官爵品级。据不完全统计,淮军出任提督以上官职的就达153人。〔1〕其中仅李鸿章在合肥东乡一隅的田地“当占全乡2/3,为数约在50万亩以上。”〔2〕刘铭传广置田地, 在六安、苏家埠有上千亩,麻埠一带山场、土地南北数十里、东西数山头,富敌西乡,有“骑马不踏外姓路,马饥不吃外田草”之说。〔3〕李鸿章、刘铭传等捐置义庄动辄数百、数千亩。
跟随淮军将领作战的也大异于昔。刘铭传在《刘氏宗谱·义庄序》中写道:“子弟有随军从事者,多名成业就,家室一新。”这些人勇于作战,也肆意劫掠,又因战功多得奖赏,积累了不少财富,他们在家乡霸占田产购屋置地,迅速由贵而富。涡阳人马玉昆以捻军投淮军,得总兵记名衔,“有心计其农业为一时最”,〔4〕原籍合肥的卫汝贵“有租1200余石,田78石”,〔5〕随同李鸿章司文牍的周馥, 自称“置田千余亩,皆苦瘠。……其膏腴沃壤,则大有力者,余不能也。”〔6〕千余亩尚嫌不足,其他大有力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有690 多军功地主的庐江县,战后“十室九空,田归富户,富者愈富,贫者愈贫。”〔7〕这里的“富户”指的就是军功地主,即那些总兵、副将、参将、 游击以下各级武官,他们以劫掠冒饷购并土地。“田归富户”这是土地兼并的新趋势,反映出近代土地集中的特点。
李鸿章、刘铭传等驰名中外的洋务派领袖在家乡大置田产,实行的却是中世纪的“领主制”。他们在乡村皆修有“土圩子”,每个圩子占地数十亩,外环深沟高墙,内设炮台,所住佃户兼卫士、炮手、轿夫,完全为佃奴性质,“地主至佃户婚丧等事有权过问,并有刑罚权,俨如古代领主之对农奴。”他们委托“仓房”(俗称二地主)管理自己在乡村的房宇、田产。〔8〕
就省内而言,军功人员主要集中于皖北各州县。庐州府属合肥、庐江、舒城等和安庆府怀宁县,军功地主每县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数十人,合计在两万人左右。〔9〕军功人员除了自己派军队占田, 地方官府也帮同他们争夺土地。地方当局“为土民定租额,为客民编门牌,于是土民悦、客民畏,遂以无事”,〔10〕这样,从他乡来垦种土地的客民无法在军功人员集中地区占有土地,这里的农民基本上是在新的租佃关系下从事垦辟,合肥县佃农比例高至70%以上。〔11〕
皖南出现的少数地主是湘军驻防武官和一些富豪。将官方长华领兵到建平,看到一块好地方,就强令士兵修筑占地2800亩的永新圩。〔12〕宁国府属南陵县地广大稀,因遗民们不愿多占地土负纳税义务,本地“仅以有三千余亩者为最多”,以致地价低廉,“乃有他处豪富,多量购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有田多者达二三万亩。〔13〕
新兴地主阶级的涌现是在太平天国沉重打击腐朽没落的豪族世家之后产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如急风暴雨式地打破原有的不平等社会现实,太平军所过之地,官吏、世家及依附于清政权的地主武装尽在锄灭之列,倍受扫荡的官僚地主随即衰微。原礼部尚书龚鼎孳的遗裔,是皖江望族,富贵甲庐州,“名儒循吏,……乡贤名宦,……膺方面者代不乏人”,经战争冲击,“室家荡析”,族人星散,世宦首户反成淮军将领的僚属。 〔14〕据《两江忠义传》统计, 长年战争中一门死亡者共有1433家、9574口。〔15〕其中安徽一省占数过半。70年代后安徽门系阀阅随之以新起姓氏为主。
新兴地主阶级与旧式地主毕竟有所区别。李凤章(李鸿章五弟)极力剥削地租,到天津、上海等地建厂,〔16〕李鸿章本人在上海、武汉、汉口典当和钱铺100多处,在招商局、电报局、 滦煤矿等占有很大股份。许多地租收入由他们引入城市,成为民族资本积累的一部分,这种状况虽然使农村经济萎缩,却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
战后皖南农村荒凉残破,人口骤减土地废耕,为增加财政收入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地方当局在宣城、南陵、旌德等破坏严重的地方展开大规模的荒地垦复活动,其目的是要广大垦民在封建租佃关系下垦辟土地。然而,随着招垦中客民的源源而来,农民与地主(主要是土著居民)进行一场争夺土地的斗争,地主阶级力图重建土地关系并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出现了为他们始料不及的后果。
首先,战后初期皖南严重缺乏劳力,荒地面积很大,地主招佃甚难,封建关系的重建受到限制。曾国藩于1864年承认,安徽用兵十余年,纵使城池克复一两年,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17〕即便后来招到一些外来垦荒佃户,若业主稍加追索,则席卷而逃,另向别主领田开垦,已熟茺田复又抛荒,直到1896年,石埭“未垦之地尚十之四”〔18〕,究其原因,当地人称“久荒之地,土脚不活,初垦之土,所收仅偿工本。……凡外来均是贫民,未得其利,先受其累,故弃而他徙,熟田所以复荒也。”〔19〕田多佃少的矛盾使业主不得不产生许多空地,对他们来说,田地“一经垦熟,即须征赋”,熟而复荒的农田,使业主不仅无利可图,且常有赔粮之忧,一般老百姓无力垦荒,“稍有力者类皆别谋生计,视田业为畏途”,〔20〕这样有的地主或贱卖土地,或放弃土地。战后十余年,全省仍有荒田八万余顷,约占原有耕地面积的1/4。〔21〕“无从招佃”使旧的租佃关系的恢复不能进行下去。
第二,地主和富农要确认田地的旧有产权,十分困难。长期战争使“向存鱼鳞册、黄册荡然无存,即民间田产契据亦多半遗失”,〔22〕垦民报垦土地是否属于业主,已无从稽考,于是招民开垦就存在荒地是否还有原业主的问题。然而,田地一经垦民占垦,“田亩经界,变改旧形,客民择肥而开,务成片段,致有一家而兼昔时数姓之田,数人而分旧日一家之业,纷杂错乱,莫可究诘。”〔23〕业主回归引起所有权的词讼,官府无案据可稽,业主也无杜典契卷为据,因而官方“莫从判断,即勉强讯结,亦不能证实判定,以箝其口。”〔24〕尽管回乡地主中不乏“自称原主,串同局董书差”者,仗势欺凌垦民耕地,使垦民空费经营,转致为人作嫁事时有发生,亦不能排斥垦民对地主认田活动的否定,出现业主返乡后“田为人有,力不能争,讼不能胜”的现象, 〔25〕形成土地关系中的混乱、松动状况, 这就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增加提供有利的条件。
第三,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农民斗争精神得到激发,加之战后客籍垦民人多势强,地主认田夺地活动,遭到垦民的顽强抵抗。皖南曾是太平军出入频繁的地区,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而受运动直接影响的广大农民反抗精神大增,地主阶级称战后“民俗刁顽,目无法纪”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垦民不再像以往对地主那样吞声恭顺,而敢于对地主的剥削行为进行抗拒,至于州县交界山区的客佃,“既不纳赋,又不缴租,”官府和绅紟皆无能为力。〔26〕在招垦过程中江苏客民不少是逃荒之人,在原籍“本有田可种者,”而来安徽各州县的绝大多数为破产农民,他们远道“挈室而来”,带有家眷农具,为子孙计而“有愿受一廛之志”。〔27〕他们当然不肯返乡地主指认田屋,于是手执农器与地主作坚决斗争。在这种情势下,地方官府不得不采取从权变通措施,土地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
第四,地方官吏为增加贪污渠道,扩大赋额,“有意庇客压主”,不利于原主认田。广德州初定垦荒章程时规定“无主承认者亦以一半给垦户作为已产,一半充公”,〔28〕宣城等不少州县也采取价卖荒地与客民为业的方式,以保证粮赋征收,官吏、董保“借买卖公田一事高下其手,从中渔利”。〔29〕官府在办理买卖土地过程中总是力图扩大荒地面积,于是“虑土民多认田亩,则充公田少卖价无多。于是四乡同日齐丈,使业主奔走不及,又不准其托人代认;而祠庙、公田、祭田一概充公,不准充认”,结果“土民有田者,十分之中仅认一二”,〔30〕那些因“四乡同日齐丈”而“奔走不及”者田地皆被划入荒田,而由官价卖。仅广德州卖田制钱十余万千,委员、董保薪水除外,滥支滥用,最后只余五六万千。在这里,地方官吏的私利在于旧主不能认业,利用“无主者以价充公”的规定,使之“归公”转而归入私囊,于是发生“庇客而压主”之事。
此外,当时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影响到地主阶级的认田夺地活动。垦民开辟大片荒野,十分辛苦,“予等来时蔓草荒烟绝无人迹,田尽草莱,屋皆荆棘,予等既费其财,又劳其力,开垦多年,始得田皆成熟”。〔31〕战后逃亡地主陆续归来,令客民或交价购买地产,或按季交租,欲坐享其成,连巡抚裕禄在奏述宣城等地垦务时也不得不说,“此令客民认主交租势有难行之情形也”。〔32〕垦民拒不交还所耕之地,当时报刊舆论认为是在情理之中,《沪报》光绪九年二月二十八日(1883年4月6日)上载:“客民不远千里,扶老携幼而来,费数年胼胝之勤,始获辟成沃壤,孰肯俯首听命,让而归诸无据冒认之业主,”有人还在《上海新报》上发表评论说:“天下无此易事。”〔33〕垦民对回乡地主认地坚决斗争,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上述诸种因素使得地主经济的恢复难以实现,却为劳动农民获得小块土地提供了可能。皖南不少地区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大规模垦荒过程中出现一大批小土地所有者,这是土地关系变化的另一种趋向。
皖南小土地所有者的大量产生来源于下列两种途径:一是低价购买荒地。在垦民争耕地的过程中,土客力量的对比决定土地争夺的结果,客民争夺土地既猛烈又持久,引起地主阶级的恐慌,地方官府认定皖南首要之事在于“和民”,于是“屡次因客民交租势难实行,始有土民买卖之议”。〔34〕土地买卖意在调整土客之间关系,主要体现在巡抚裕禄拟定的买卖土地章程,〔35〕其中规定:由客民“买田以承粮”,土民“卖田得价,别营妥实之田”;土地价格“每熟田一亩,定为本洋一元四角,熟地七角,荒田三角,荒地二角”;垦户买田“有主者价皆给主,无主者以价充公”。十余年间,皖省不少州县沿用此法在土客之间进行“和辑”。价买的土地大约有三种:(1)无主荒地:广德州曾以较低价格官卖土地,得制钱十余万千,成交土地当在20万亩以上,占全州耕地的67%强。〔36〕地价较低,且原垦户有优先购买权,因而购买者主要系垦荒农民应属无疑。(2)客民拒交地租而迫使地主出卖。 广德客民至光绪初年,有两三年未交租者,当业主向官府具控的时候,官府“并不追究,反当堂劝令业主卖田。于是客民效尤,纷纷抗租,以为勒卖之地”。〔37〕(3)土客争执产权之地。 宁国一带对此从权处理,“熟田令客民备洋一元四角给业户,即发买契,永为世业”,买卖虽带有强制性,土地产权之争却获得某种解决。当然上述价买办法对于客民说来虽遭受不小的损失,毕竟迫使地主阶级作出一些让步,而获得了小块土地。这是垦民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
二是客民向官府认垦或自己占垦无主荒地而保有这些土地。1869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奏定章程,今后“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官给印照,永为世业”。〔38〕有的学者分析招垦章程的条文内容后认为,农民并未从这个章程规定中获得土地,这不过是一纸空文。〔39〕这个看法是否符合他省的实际情况此不作论,但它不大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是显而易见的。清末的一份报告指出,“皖南各州县,前经发逆乱后,土著无多,客民侨寓,置产纳税,历数十年”。〔40〕全椒县“咸丰乱后,客商星散,土著十不存三、四,田多而人少。故十数年来,邻县如合肥、潜山等客民,多侵入其间,或佃田,或垦山,颇获厚利”,〔41〕建平县(广德州属)1877—1878年间查出新垦土地2.36万亩,其中无主地有2.32万亩,占全部新垦地的98%,〔42〕垦民名义上对这些土地没有拥有权,但垦种无主荒地,“官吏无以穷诘”,实际与拥有这些土地并无二异。
皖南客民通过价买或垦种无主荒地两种途径获得土地的数量,尽管各地情况不一,从一些州县看不在少数。
广德州:70年代在州官李孟荃主持下, 20 多万亩土地以每亩熟田600文荒地300文的价格转卖。1878年州属建平县知县汤鼎臣呈报垦荒情形时说,河南湖北等省客民十多年来已“置有田产坟墓,查出烟户粮差,俱已有名,”又说“土客民多有已垦田地隐匿有报”。〔43〕
宁国府:1881年知府桂某在垦民反对认主交租情况下,由垦民交价承买,领田交价在垦务所(垦农垦局下设)办理。土地买卖实行后“土客熙融,各有恒产”。〔44〕
徽州府:来此垦荒的桐城县农民“竭力开垦,多致小康”。〔45〕
池州府:道光前“业农者终岁勤劬,而不获一饱,”同光年间“落落数十家,躬耕堪以自给。”〔46〕
这些记载反映了垦民的经济状况,也说明了佃雇农向自耕农的转化。地主阶级受到太平天国运动重创的皖南地区,客民获得小块土地的情况极为普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地兼并渐趋激烈,地权日益转向地主富农之手, 但到二三十所代皖南自耕农半自耕农数尚占全部农民的52 .1%,苏南昆山等地(22.4%)与之比较有相当大的差别。〔47〕
三
战后安徽土地关系中出现的又一种新变化是永佃制的大发展。
永佃制是佃农有权“永久”性地耕种地主土地的租佃形式。在一般租佃关系下,地主对佃农可以随时撤换或收回土地自种,永佃制却不同,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又称田底权)与佃农对土地的耕作权(又称田面权)分离。清代前期永佃制流行于皖南和皖中沿江一带,徽州、宁国、广德、太平府和安庆府是比较集中的地区,乾隆以后人口激增,土地供求矛盾开始尖锐,田面权也成为地主的兼并对象,如黟县一家汪姓地主在1830—1850年置买田产的文契言明“大小买田”者17宗,只有3 宗田地属地主和佃农分别占有产权耕种权,〔48〕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前地主对佃农的增租夺地相当猖獗。
战后永佃制再次迅速产生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一方面人口稠密的地带一变而为“有土地而无人民”的旷野,地主阶级为摆脱地租无收的困境必须调整支配佃农的方式,吸引农民前来就垦,只好放宽条件,除延长垦荒免租期限、降低租额,许给佃农以永佃权。另一方面,佃农开垦荒地需要花费相当多的劳力和工本,“若开垦后而无长期耕种之保障”,佃农不很情愿,因为广大土地上农民可择地而耕,只有在农民获得永久佃种土地的保证后,地主招垦活动才能实现,地主“特让以田面之权,令其永久佃耕,以安其心”。〔49〕
因此,垦荒过程中形成的永佃权可以说是佃农垦荒报酬的转化形态。芜湖县有一半以上的佃农拥有永佃权,舒城、桐城等县“几全有永佃权”〔50〕。从桐城、庐江到皖南贵池就垦的农民,人数占到当地总人口的80%左右,“或佣,或贩,或无业之难民”,到后与地主说合,承垦地主荒地按桐庐习惯,从而获得永佃权。徽州府属绩溪、歙县、休宁等县,当地地主“多以经商为主,不赖租谷度其生活”,地主招佃往往“初三年免缴租谷以后租额亦皆减轻,且予以永久佃种之权”,〔51〕地主用永佃权将佃农系在自己大地上,自己专心于经商致富。此外,尚有佃农直接通过价买方式获得永佃权的情况,如黟县山多地少,客民涌入后“欲佃不得,于是纳金于田主,田主收其金,则此田永远由其承种”。在休宁,农民将出卖的土地佃回耕种交租,谓之“卖租”,其契约称“卖租契”(卖地自己不耕种的叫“卖田契”),不过这种卖田留佃的形式在安徽远不如湖北、浙江普遍。〔52〕
据统计,皖省永佃权比例居内地各省份之最高位,达44.2%,江苏稍次之,第三位浙江省只有30.6%,〔53〕拥有永佃权的佃农较多是战后安徽农村租佃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永佃制下,地主不能任意增租,或以撤佃相威胁,广德州凡属永佃田,业主“不能起而自种”,〔54〕永佃农比一般佃农在生产活动上有较多的独立性,甚至佃权的辗转让渡,地主也无权干预,一些地主阶级的辩护士因而叫嚷,由于实行永佃制,“田土悉被佃户把持,不能操纵由我。故顽佃有所挟制,遂致租霸产,百般刁狡,”以致“地主受非浅”。〔55〕尽管永佃权只是一种耕作使用权,土地所有制性质并未改变,但地主租额受到限制,佃农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同时佃农身份地位的变化反映土地关系中封建宗法关系进一步松懈。
总之,战后自耕农和永佃农(主要在皖南)数量大增,是农民大起义历史作用的具体体现。由于拥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已经开始侵入安徽,特别是70年代订立的《烟台条约》明确规定芜湖为通商口岸后,面对商品和市场的刺激,他们的产品自给程度日渐降低,资本主义渗透农业的进程大大加快,19世纪末兴办农垦公司的热潮一定程度上就是顺应这一形势的产物。“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较平均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56〕皖南土地关系的变化因之衔接前所未有的时代内容,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温床。
注释:
〔1〕王尔敏:《淮军志》页137,图表七。
〔2〕〔3〕《合肥市文史资料》(2),页135—136。
〔4〕〔5〕〔6〕〔12〕〔13〕〔18〕〔49〕〔50〕〔51〕〔52〕〔55〕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页181—184,161— 162,109—110,252。
〔7〕卢钰等:《光绪庐江县志》卷12,页4。
〔8〕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与租佃制度》(1963 年),引自《合肥史话》页33—34,黄山书社1985年版。
〔9〕光绪《续修舒城县志》卷31,军功300人以上;民国《怀宁县志》卷6,军功411人。
〔10〕〔14〕〔19〕引自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页267,378,382,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合肥佃农比例高,这里水稻种植面积较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5〕《皖政辑要》(稿本),第3册。
〔16〕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页265,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17〕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1,页75。
〔20〕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7,页6,光绪十八年(1892)版。
〔21〕《清实录》(德宗朝)卷110,页9,伪满洲影印版。
〔22〕姚锡光:《吏皖存牍》卷上,页29,光绪三十四年(1908)版。
〔23〕〔24〕〔26〕〔32〕〔34〕〔35〕裕禄:《办理皖南垦务片》,《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3,户政十,光绪二十三年(1897)版。
〔25〕〔27〕《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1881年5月16日)。
〔28〕〔29〕〔30〕〔37〕〔43〕〔54〕丁宝书等:《广德州志》卷56,光绪七年(1881)版。
〔31〕〔33〕《上海新报》同治九年四月初五日(1870年5月5日)。
〔36〕〔4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下),页815,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8〕马新贻:《马端敏公奏议》卷7,页53, 光绪二十年(1894)版。
〔39〕茅家琦:《晚清史话》页79—8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0〕《东方杂志》卷6,宪政篇。
〔41〕江克让:《民国全椒县志》卷4,页1。
〔44〕《益闻录》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九日(1881年1月8日)。
〔45〕萧穆:《敬孚类稿》卷6,页11,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
〔46〕周赟:《玉山诗集》卷2,页14。
〔4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页305,三联书店1957年版。
〔48〕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页209—215,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5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页254,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56〕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页272,三联书店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