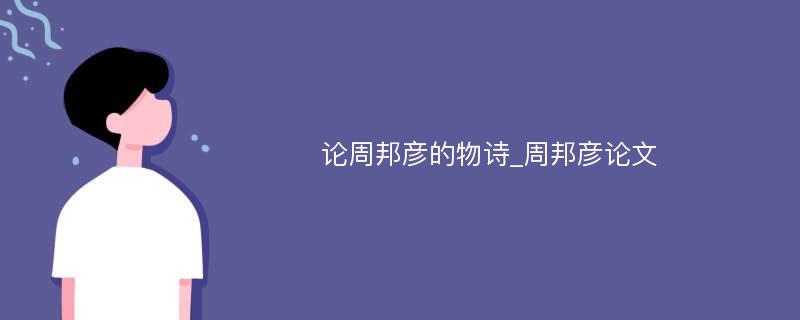
论周邦彦的咏物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周邦彦论文,咏物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咏物词,晚唐五代即已有之。如温庭筠《菩萨蛮》(玉纤弹处真珠落)咏泪、李煜《一斛珠》(晓妆初过)咏佳人口,为宫体咏物之作;司空图《酒泉子》(买得杏花)、牛峤《望江南》二首咏燕及鸳鸯,则属睹物生感,感物而咏物的词作。另有毛文锡咏物词十一首,所咏涉及舞马、牡丹、海棠、柳等,多属应制供奉之作,以铺陈刻画吟咏对象之外在形貌为主,代表当时咏物词创作的一种主要类型。至北宋柳永、晏殊、欧阳修等人步入词坛,咏物词声势稍张。柳永创作了七首体物颇为工致的咏物词,其中有三首以慢词体制出之,开宋人慢词咏物之先河;晏、欧咏物词多达四十余首,主要是作者闲暇游赏之际的感物之作。晏、欧咏物词较之毛文锡词,特重意趣之传达,而不纯以体物为能事,是北宋前期咏物词的创作典范。虽然如此,但就当时词坛大势观之,咏物词所占比重实微不足道。
苏轼和周邦彦是咏物词发展史上的两个关键人物。苏轼“以诗为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拓展了词的题材类型,深化了词的情志内涵。他不仅创作了一些优秀的咏物词,还与朋旧、同僚和师友一起以咏物相唱和,具有开风气的重要作用。稍后于苏轼的大词人周邦彦在咏物词创作中亦投注极大心力,对前人多有突破,大大深化了咏物词表现艺术。周邦彦咏物词较之前此出现的咏物词,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发展。第一,创作主体的深度介入。这既不同于早期咏物词人与物、物与情的间离,也不同于苏轼物我浑融的人格化的咏物词,而是一种创作主体与客观对象之间的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周邦彦咏物词能感人至深,与此有密切关系。第二,周邦彦咏物词打破旧的咏物词创作运思程式,在章法结构上有较大突破。第三,周邦彦在咏物词表现手法上对前人亦有较大突破。下面试分别予以论述。
一 创作主体的深度介入
创作咏物词,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苏轼之前的大多数咏物词,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处于一种间离对峙状态,要么是在外在因素促动下被动创作,因而我是我物是物(如毛文锡);要么是我因物生感,感物而咏物,我之情由物所触发,但我之情非物之情,我与物之间的交流是单向的、一维的,在这样的作品中,物往往沦为传达作者情意的媒介,而不是作品表现的主体,多少有点脱离咏物之本旨(如晏殊、欧阳修的一些咏物词)。
与前人相比,苏轼的最大突破在于使物具有了“人”的情感与生命,开创了一种人格化的咏物词。试以《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为例略作说明: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在这首词中,作者不是站在旁边作客观的观察摹画,而是用心体察物之性情、神理。作者把杨花比拟成闺中思妇,赋予杨花以思妇的情感和生命,因此在作品中,物即是人,人即是物,物与人融合无间,物成了人格化的对象,反过来也可以说“人”化入了物。
但是必须指出,此词中的“人”显然不是作者自我,而只是一个虚拟的形象——思妇;作者是站在外面观照、吟咏杨花的,创作主体外在于表现对象,作者自我的情感意绪并没有呈现在作品中,故若以境界论观之,此乃“无我之境”也。
这种“无我之境”在周邦彦咏物词中已很难见到。他的咏物词常常表现自我深刻的人生体验,寄寓浓挚而沉郁的情感意绪,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一样成为咏物词所要表现的共同“主体”。
周邦彦咏物词以表现“常人之境界”为主。王国维云:
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者为多。(注:参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11册。)
所谓“常人之境界”,是指执着于“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这类人之常情的表现所形成的境界。周邦彦词,以常人之境界为多,这即是说在清真词中,“情”所占的分量极重,是深于情者也。这种情绝不是虚情、矫情,而主要是作者有着深切之体验,有着切肤之痛、曾深刻激荡作者心灵的至深之情。这种情不仅表现于清真情(即悲欢离合)词、羁旅行役词中,而且大量渗透到他的咏物词中。如果说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人艳词”,那么周邦彦就是将“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打并入咏物词中。因此在周邦彦的词中,咏物词不单纯是为了咏物,而是更多地借咏物以传达主体自我的深切的刻骨铭心的悲欢离合之情,羁旅行役之感。“我”咏物,“我”观物,我之意绪、情感投射于外物之上,故“物物皆着我之色彩”,所创造者既为“常人之境界”,更是“有我之境界”。更进一步,“我”还要直接站出来与物进行交流、对话,创作主体不再是简单地浅层次地咏物、观物,而是深层次地介入其中,“我”与“物”一样,成了作品表现的“主体”(主要表现对象)!因此,如果说东坡在咏物词创作上的突破,还没有有意识地撼动“物”作为咏物词的主体性地位,属革新而不犯本位的话,周邦彦的咏物词则通过主体的深层次介入,对“物”的绝对主体性发出了挑战。试看下词:
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六丑·蔷薇谢后作》)
这首词又题作“落花”。这并不是一首简单的“惜花惜春之作”,而是一首寄寓作者主体自我强烈的情感、意绪的咏物名作。此词以情语开篇,“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数句交待时序,传达出作者春晚客居异乡的落寞情怀,奠定全词情感基调,使作品一开始即带上强烈的感情色彩;“愿春”三句进一步强化我之无可奈何的情怀,“愿春暂留”,我之祈求可谓微矣,然“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甚至不给我以喘息、回味的机会。于是我的思绪因春晚而虑及窗外之花,“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是想象花之遭无情风雨摧残而落,以“楚宫倾国”喻花而出以一“葬”字,表达作者对美好事物被摧残的惋惜,已然逗出了下文的“追惜”二字;“乱点”、“轻翻”,想象落花令人怜惜之况味;惜之者谁?蜂也,蝶也,以及落寞中的“我”也!下片由此生发,我来到岑寂的小园,在残花下徘徊良久,为花事阑珊而叹息,物与“我”之间随之开始了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是长条之恋人;“残英小、强簪巾帧,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是人怜未落之残花(花事已尽,虽有残英,而全无盛时之情致,殊可怜也);“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是寄望于已落之断红(担心断红随水而逝,那红叶题诗的美丽传说会因此前缘难续)。三层意思,吞吐回环,总不出“怜惜”二字,而作者主体自我身世之感、落寞之怀,也蕴于其中。故陈廷焯评此词云:“下文(“夜来风雨”以下)反复缠绵,更不纠缠一句,却满纸是羁愁抑郁,且有许多不敢说处;言中有物,吞吐尽致。”(注: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词话丛编》(唐圭璋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87页。)黄蓼园云:“自叹年老远宦,意境落寞;借花起兴,以下是花、是自己,比兴无端,指与物化。”(注:黄苏《蓼园词评》,参《词话丛编》第3095页。)都是指此。
《花犯》(粉墙低)更是如此。此词题曰“梅花”,实借咏梅将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生况味融入词中。黄升评此词云:“此只咏梅花而纡徐反复,道尽三年间事。”(注:黄升《花庵词选》卷七,南京图书馆藏抄配汲古阁本。)黄蓼园云:“总是见宦迹无常,情怀落寞耳。忽借梅花以写,意超而思永。”(注:黄苏《蓼园词评》,参《词话丛编》第3085页。)而词中,“去年胜赏曾孤倚”、“今年对花最匆匆”等句,则是作者亲自诉说与梅相关之情事,梅似乎成了“我”之身世、情感、意绪的见证!《大酺·春雨》之咏雨,陈洵评云:“虫网吹黏,铅霜洗尽;静中始见,总归趋‘幽独’。”(注:陈洵《海绡说词》评语,参罗忼烈《陈洵〈海绡说词〉说周清真词校录》,《词曲论稿》(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7年版)第127页。)《红林檎近》(高柳春才软)咏雪之“那堪飘风递冷”、“冷落词赋客,萧索水云乡。援毫授简,风流犹忆东梁”诸句,也是作者的直接诉说;《倒犯·新月》看似刻意咏物,然自“何人正弄、孤影蹁跹西窗悄”以下,句句关合一段往事,一段别情,于结句并引申一种无限凄凉的人生况味(料异日宵征,必定还相照。奈何人自衰老);而《兰陵王·柳》则似乎来得更彻底,除第一段外,二、三段甚至整个就不再说柳而专说别情,成为宋代咏物词中杰出的异类。可以说,创作主体的深度介入,既是周邦彦咏物词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周邦彦对咏物词创作观念的一次严峻挑战。
这种创作主体的深度介入必然导致咏物词创作运思方式与结构特征等方面的新变。这种新变主要发生在咏物慢词的创作之中。
二 周邦彦咏物慢词的运思方式与结构特征
慢词的大量创作始于柳永,以慢词咏物,亦由柳永开其先河。由于慢词体制较小令为复杂,驾驭起来难度颇大,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慢词咏物者并不太多(注:周邦彦以前宋人所作咏物词约三百三十首,慢词五十四首,占16%,周邦彦咏物词二十三首,慢词九首,约占40%,他也是北宋创作咏物慢词最多的词家。),由于艺术上的不成熟,为稳妥起见,咏物慢词在运思方式和结构模式上多借鉴前此其他咏物文学中相同题材的作品,往往按一种很传统的方式进行创作。即日本学者宇野直人所谓“拟古的姿势”(详下)。下面试以柳永《望远行》咏雪及苏轼《水龙吟》咏笛为例略作说明。为直观起见,此处用表格将《望远行》呈现如下:
词文
时间流程
空间位移——视野转换
长空降瑞,寒风剪,淅淅瑶花初下 雪始降(所见 天空——仰视
第一节
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迤逦渐迷鸳瓦之景象) 城中—市井——平视
好是渔人,披得一蓑归去,江上晚来堪画雪中(所想象 城外—江上——俯视
第二节
满长安,高却旗亭酒价之景事) 城中—酒肆——平视
幽雅,乘兴最宜访戴,泛小棹,越溪潇洒雪中(所想象 城外—山中——平视
第三节
皓鹤夺鲜,白鹇失素,千里广铺寒野之景事) 城外—原野——俯视
须信幽兰歌断,彤云收尽,别有瑶台琼榭雪晴月出(所 城中—雪景——平视
第四节
放一轮明月,交光清夜见之景象)
天空——仰视
上表清晰地显示了柳永此词的结构。从结构特征来看,这首词明显分为四节,每节又依空间之位移与视野之转换,分别描绘两个场景。作为一首早期的咏物慢词,这种结构特征是非常鲜明甚至可以说是匠心独运的,宇野直人认为这首词的结构具有“稳固的均衡感和舒畅的流动感”(注:参宇野直人《柳永论稿》(张海鸥、羊昭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02页。),我认为有一定道理。宇野直人接着又从历代咏雪诗的发展探讨了这首《望远行》成立的条件,认为此词的运思方式具有拟古性(注:宇野直人称这种拟古性为“拟古的姿势”,实即本文所说的创作运思方式。)。并进而分析其原因,即“出于一种稳妥的思路,进一步说,他将已经定型的正统手法引入慢词创作,可能是觉得传统的咏物方式会使慢词这种新形式获得人们易于接受的安定感”(注:参《柳永论稿》第311页。)。具体而言,这首词是以时间的流程为运思活动的主要线索(即从雪初下一直写到雪晴月出),空间的转换通过视野的移动也穿插其中(即雪由初下到月出的过程中天空、屋宇、江山、原野、台榭所呈现的不同景象,以及联想到一些与雪有关的典故),构成作者运思活动的另一条线索。
这种运思方式一方面与六朝咏雪诗以及唐人咏雪律诗有着明显渊源关系,即宇野直人所谓“拟古的姿势”,另一方面也与作者的基本创作观念有一定联系。这首词创作意图相当单纯,咏雪即是本旨,除此之外并不刻意寄托或承载主体自我情感、意绪或对宇宙对人生的深切感受或深层领悟。这就是说作者虽然咏物,但主体自我并不深层次地介入到咏物之中。这决定了作者创作运思活动必然围绕吟咏对象本身展开。其《黄莺儿》(园林晴昼春谁主)咏黄莺、《受恩深》咏菊与此略同。
苏轼的一些咏物慢词亦取此运思方式,张端义《贵耳集》论东坡《水龙吟》咏笛云:
东坡《水龙吟·笛词》八字谥:“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质也;“龙须半剪,凤膺微涨,玉肌匀绕”,此笛之状也;“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此笛之时也;“自中郎不见,将军去后,知辜负、秋多少”,此笛之事也;“闻道岭南太守,后堂深、绿珠娇小”,此笛之人也;“绮窗学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此笛之音也;“为使君洗净,蛮烟瘴雨,作霜天晓”,此笛之功也。(注:参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四库全书本)。张侃《拙轩词话》所引略有差别(参《词话丛编》第195页)。)
张氏的这段分析看上去似乎有点匠气,却也不无道理。此词咏笛,作者从笛的自然、社会属性入手,从八个方面展开对笛的描述,每节咏一事,创作运思既奇特又稳妥,结构复严谨整饬,有条不紊,也算是苏轼咏物词中的优秀作品。细读之下,我们总觉得此词的构思和整体结构似曾相识。其实这首词和柳永《望远行》一样,也有一种“拟古的姿势”,只不过柳词直接从咏物诗来,苏词则更多借鉴了咏物赋的写法。我们知道,汉魏咏物赋中,音乐赋是一个很重要的门类,萧统《文选》赋类即录有音乐赋多篇,如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等。试以《长笛赋》为例。此赋围绕笛的几个方面展开,首先铺叙笛材所自,突出其所禀天地之精气;次叙伐竹制笛,突现其精工合度;次叙乐师之吹奏,突现笛声之精妙;次叙笛之功用,突现其感召力……;王褒《洞箫赋》、嵇康《琴赋》等机杼略同。很显然,苏轼的这首《水龙吟》咏笛,在创作运思上对这些音乐赋是有所借鉴的。这说明北宋咏物慢词在很长时间内都具有拟古的倾向,尤其是同类题材的继承和借鉴,实在是很自然的事。
以上两首词应该说是柳、苏集中的咏物佳作,也是宋代咏物慢词中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就各自题材而论),它们之所以取得成功,似乎与这种“拟古的姿势”有一定关系。事实上,这种具有“拟古性”的运思方式的优长之处正在于容易驾驭,不致离题,比较适宜于初学者或草创时期的尝试性创作,但其不足之处则在于缺少变化,具有程式化的倾向。
这种运思方式和结构特征的“拟古性”,在周邦彦的咏物慢词中已很难见到。由于主体的深度介入,周邦彦的咏物词带有很强的主观感情色彩,心理、情感成为咏物词所表现的重要内容,创作意图上的兼及物我,必然鲜明地体现于作品运思和结构之中。试看其另一首咏物名作《花犯·梅花》(注:由于此词涵义深永,结构独特,为节省篇幅,聊以笺注体发明之。):
粉墙低(梅花开放之处),梅花照眼(本是我看见梅花,却说梅花映照我的眼帘,著一“照”字,姿态可人),依然旧风味(“旧”字寓无限感怆,映入眼帘的梅花依然还是旧时之风味,自然勾引出作者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之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此三句正面写梅花,而用一表示心理情态的动词“疑”字,令人发无端之想,下文即就此生发)。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宴喜(此二句应前之“旧风味”,而所谓“冰盘同宴喜”者,前日之欢洽情事也)。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此三句写旧日雪中赏梅时梅花之情态,“可惜”是可怜可爱之意,亦是欢洽情事之一也)。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此三句与“去年”境况相对比,既无前日之从容闲雅,故虽然相逢,却仿佛有无限愁恨,我心既“有恨”,而花亦“著我之色彩”,无端“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此三句写此时我所见梅之情态,实为强化梅花之“愁悴”,而我心亦随之惆怅万分也)。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此二句感慨极深,言梅子将老之时,我正漂泊于“空江烟浪”之上,无心亦无缘“脆丸荐酒”引发出前尘如梦,往事俱非之憾)。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此二句将思绪拉回到所咏之物上,收束全篇。言己身虽漂泊无端,情怀寥落,但尚“梦想”那一枝梅花潇洒溪畔,似人之不负前约,著一“梦”字将各种复杂的心绪幻化无痕矣)。
这首词作者用意颇深,咏梅而“道尽三年间事”(黄升语),“总是见宦迹无常,情怀落寞耳”(黄蓼园语)。在这首词中,物与我互相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我睹梅而生思,另一方面我之所思所感深深投射到梅花之上,使梅花著我之色彩。因此我之所思所念所感(即作者的心理流程)成为作者创作运思的主要线索。这与前举柳词之以时、空之自然流程和苏词以物之性状为线索的运思程式相去甚远。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周词在结构上体现出与柳永、苏轼咏物词截然不同的特征。
前文曾经提到,柳永《望远行》在结构上是具有“稳固的均衡感和舒畅的流动感”,这种结构特征的形成,实基于其以时空之自然流程为线索的创作运思程式,苏轼《水龙吟》咏笛亦复如是。柳、苏咏物词在结构上所具有的稳固性、均衡感及整饬感,在周邦彦咏物词中似乎很难看到,代之而来的往往是错综复杂腾挪跳跃的结构特征。周词的跳跃性正是其以心理流程为线索的创作运思方式的直接反映。以《花犯·梅花》为例,时空的跳跃与心理意绪的跳动互相交错,物与我的呈现对流互动。这种跳跃性鲜明地体现在一些关键字句上:“照眼”是现在花作用于我——“旧风味”是我之心绪因花而动——“霹痕”是花此时之性状——“疑”是我被花勾起的遐思——“去年”情事是“胜赏”、“宴喜”——“今年”情事是“有恨”、“愁悴”,皆因花及人,因人念花——“相将见”、“人正在”是念及后日——“但梦想”是寄望梦境。作者在观照对象(梅花)的触发下思绪万千,观照对象成为创作运思的触发点,心理意绪成为作品表达的核心内容,心理流程则是作品的内在线索,这颇有点类似于现代艺术中的意识流手法,兴于物而达于情。他的另一首咏物名作《六丑》在运思方式和结构特征上也与此有相通之处。
由于作者在咏物词的创作中主要以心理流程为运思线索,而随着环境、情势的变化,作者心理、意绪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咏物词之中。这使周邦彦咏物词的结构从整体上也体现出富于变化的特点。《兰陵王·柳》作意全在写别情,故除首段切“柳”外,以下两段完全宕开,已经有点越出咏物词的基本轨范,如陈洵云:“托柳起兴,非咏柳也。”(注:陈洵《海绡说词》评语,参《词曲论稿》第117页。)对此词是否咏物持保留意见,陈匪石云:“愚谓以‘柳’命题却说别情,咏物而不说物,专说与物相关之事,此亦兴体作法。”(注:参陈匪石《宋词举》(金陵书画社1983年版)第73页。)《大酺·春雨》意在揭出心理之“幽独”,故“通首俱写雨中情景”,层层渲染,吞吐有致,回环往复。至于《玉烛新·梅花》、《水龙吟·梨花》似乎没有太受特定心理情绪的支配,只略用些意思,故显得平稳妥帖,与前人的许多作品有相似之处。
三 周邦彦在咏物词表现手法上的突破
和前人相比,周邦彦在咏物词创作手法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即对对象物的表现由静态观照发展为动态呈现;在表现吟咏对象时将传统的拟人手法与审美移情作用相结合而成“拟情”的表现手法,丰富了咏物词的艺术表现手段;将咏物诗中禁体物的表现手法借鉴到咏物词中,从而开创了词中的“禁体物”体。
第一,从静态观照到动态呈现。
前人咏物,多取静态之观照,即使所表现的对象本身是活动的,作者也往往截取片断进行不同画面的组接,通过画面的转换来体现出运动感,以柳永《望远行》(长空降瑞)咏雪为例,该词由四组八个画面联缀而成,从整体上虽然具有一种流动感,但每个画面相当明确而清晰,除第一节通过几个动词直接描写雪下落的情状外,余皆静态观照,流动感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画面的切换来完成的。清真之咏物,当然也不乏此例,不过他更注重对物作动态的呈现。
周邦彦咏物词的动态呈现表现为两种形态。
其一,对于对象物本身的动态进行表现。周邦彦对于外物的感觉、观察能力颇强,他善于捕捉对象物的瞬间动态,并用富于情态的语句将这种动态表现出来,其咏雪云“那堪飘风递冷,故遣度幕穿窗”(《红林檎近》),咏柳云“蠢蠢黄金初脱后。暖日飞绵,取次粘窗牖”(《蝶恋花·柳》),咏梅云“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花犯·梅花》),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其名作《六丑·蔷薇谢后作》中的名句“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更是将带刺的青枝勾牵衣袖的一刹那的动态以及残花插巾颤颤袅袅的微妙动感细腻而精切地表现出来。
其二,由于创作主体自身始终出现在词境之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交流形成一种动态,从而使其咏物词富于动态美。这一点是周邦彦咏物词独特性之所在。试看下词:
霁景、对霜蟾乍升,素烟如扫。千林夜缟。徘徊处,渐移深窈。何人正弄、孤影蹁跹西窗悄。冒霜冷貂裘,玉斝邀云表。共寒光、饮清醥。淮左旧游,记送行人,归来山路窅。驻马望素魄,印遥碧、金枢小。爱秀色、初娟好。念漂浮、绵绵思远道。料异日宵征,必定还相照。奈何人自衰老。(《倒犯·新月》)
如前所述,此词似刻意咏题,然细味之自有一段别意自有一段人生况味蕴蓄其中,创作主体的动作和心理流程成为此词表现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对于新月的表现,完全与创作主体的动作、心理(即人物的动态)表现融合在一起。此词前六句正面写月,“何人”以下至歇拍写“月下独酌”,全从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句而来,本身具有很强的动作性,其中“何人正弄、孤影蹁跹西窗悄”句,将李诗中的一个简单的“影”字演绎成一组微妙的具体的动态化过程,孤影之蹁跹见出月光之荡漾;以下“冒”、“邀”、“共”、“饮”诸字,既是主体一连串的动作,月亦随主体之动而得到呈现,因为主体动作的对象正是新月。下片追忆“月夜送客”情事,化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但重点放在对人生短暂与青春易逝的感怆,一切感念皆从“望”月生发开来。由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交流,物之动态与人心之动态结合起来,从而使周邦彦咏物词在整体上体现出跌宕多姿的特点。他的另几首咏物名作《六丑》、《花犯》等也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第二,从拟人、移情到拟情。
所谓拟人,是指把物当作人来进行描写,通过赋予物以人的某些特性,从而达到形象鲜明的艺术效果。这种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极为常见,专以物为表现对象的咏物之作更是如此。试看早期咏物词中的一些词句:
东风催露千娇面,欲绽红深开处浅。日高梳洗甚时忺,点滴胭脂匀未遍。(柳永《木兰花·海棠》)
芙蓉一朵霜秋色。迎晓露、依依先拆。似佳人、独立倾城,傍朱栏、暗传消息。(晏殊《睿恩新·木芙蓉》)
江南柳,烟穗拂人轻。愁黛空长描不似,舞腰虽瘦学难成。天意与风情。(王琪《望江南·柳》)
上面三例—咏海棠—咏木芙蓉—咏柳,分别从颜色、姿容和形态的角度把所咏之物比作佳人,确实能产生形象鲜明的艺术效果。但是不得不指出,上述几例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即除了展现作者的表现技巧外,实在看不出有太多的意蕴内涵,都显得过于浅露,缺乏深度。
所谓移情,是指创作主体在观照外在事物时,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投射到对象物上,使对象物变得具有了生命和情感。比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王维的“花迎喜气犹能笑,鸟识欢心亦解歌”(《既蒙宥罪旋复拜官感圣恩窃书鄙意并奉简新除使君等公》)等诗句中,花、鸟皆因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意绪的投射而具有了情感。这种表现手法虽然精妙,但由于带有过分强烈的主观色彩,往往容易失真,因而并不太适合一般的咏物之作。苏轼等人多有此类作品,如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中的孤鸿,便可看作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在心物交感的一刹那将自我主体的情感、意绪或体验投射到物之上,物我因而融合为一;朱敦儒《卜算子》(旅雁向南飞)亦复如是。东坡、希真这两首咏雁之作,固属宋代咏物词中的精品,不过必须指出他们太注重个体情感意绪的表达,而对于物的表现稍显单薄,作者虽然赋予了物以人的情感和生命,但那究竟不是物而是人的情感和生命的投射,吟咏对象固然获得了一种象征的意味,同时也变成了创作主体情感意绪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物之为物的主体性。
由此可见,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在传达形象的鲜明性上颇见功效,然失之浅;审美移情作用在创作中的介入有力地弥补了这一缺陷,但在体物上又稍显不足。而若将二者结合起来,或许能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清真咏物词即是如此。试举数例析之:
(1)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花犯·梅花》)
(2)素肌应怯余寒,艳阳占立青芜地。(《水龙吟·梨花》)
(3)亚帘栊半湿,一枝在手,偏勾引、黄昏泪。(《水龙吟·梨花》)
(4)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六丑·蔷薇谢后作》)
(5)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六丑·蔷薇谢后作》)
(6)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客。(《兰陵王·柳》)
(7)舞困低迷如著酒,乱丝偏入游人手。(《蝶恋花·柳》)
(8)记得长条垂鹢首,别离情味还依旧。(《堞恋花·柳》)
第(1)例,“有恨”、“愁悴”,本皆指人的情绪、情感,在这里兼指梅花,即我苦于行役,故与梅花匆匆相对,我有恨,梅花亦似有恨,我愁悴,梅花亦“依依愁悴”,故既以花拟人,又移情于花,是拟人与移情的结合。第(2)例“素肌应怯余寒”,从字面看是写佳人不禁料峭春寒,实写梨花渐渐绽开,似怯于料峭春寒。第(3)例花枝而“勾引”词人几点清泪,则梨花俨然有情。第(4)、(5)例为清真词中最著名的名句,“长条”者,蔷薇谢后之青藤,“故惹行客”,即此藤在微风中袅袅颤动,如向行客招摇致意,“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作者于此残春,凭吊已残之蔷薇,无限伤离意绪萦绕于心,而此时长条却袅娜摇曳,俨然如有情之人,不愿我轻易离去,物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我之情感、意绪,于是物之形象、情态已为呼出,我之情绪亦借此传达。“钗头颤袅,向人欹侧”句,虽系虚想之辞,亦与此同一机杼。以下(6)、(7)、(8)例虽不似(4)、(5)两例那样能激起人心灵的颤动,也颇能体现拟人与移情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的精妙处。这种把拟人与移情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我称之为“拟情”,这种表现手法自清真之后,成为咏物词创作中屡试不爽的艺术表现手段。
第三,新的尝试——从体物到禁体物。
诗有“禁体物”一体(注:参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载《被开拓的诗世界》(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词亦有之,如元吴师道《吴礼部词话》云:
杨孟载作禁体雪词,后阕云(略)。予谓友词既禁体,于法宜取古人成语,匀之句中,使人一览见雪,乃为本色。(注:吴师道《吴礼部词话》,《词话丛编》第365页。)
所谓禁体物,是相对于体物而言的。体物,即“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外部特征,是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基本手段之一”,其基本特征即陆机所云“期穷形以尽相”,刘勰所云“文贵形似”、“巧言切状”者也。体物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咏物文学的主要表现手段。杜甫的出现改变了“体物”定于一尊的局面,而开启后世禁体物诗的法门,自杜甫的诗《火》(楚天经月火)起,经韩愈、欧阳修至苏轼咏雪而提出“白战不许持寸铁”的创作主张,与体物相对的禁体物的表现手法发展成熟。在《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一文中,程先生和张老师对苏轼禁体诗之所禁者归纳如下:一是直接形容客观事物外部特征的词;二是比喻客观事物外部特征的词;三是比喻客观事物及其动作的词;四是直陈客观事物动作的词(注: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被开拓的诗世界》第86页。)。这些限制说到底就是不允许对客观事物作正面的直接的描写,而只允许从侧面甚至不从物的角度去表现对象,而且还要达到“瞻言”知物(《文心雕龙·物色》谈六朝诗风时有“瞻言以见貌”之说,说法与此相似但停留在事物的外貌,与当时文贵形似的诗风相一致,仍属体物、尚巧似的阶段》的艺术效果。这种限制对诗人提出极高的要求,一般作者驾驭不了,故欧阳修、苏轼之后,创作禁体者虽不乏其人,但取得的成就却相当低下,这种在诗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体式,却在词(尤其是咏物词)中获得了全新的艺术生命。周邦彦即是词中“禁体”的开创者。
试看周邦彦的咏物名作《大酺·春雨》:
对宿烟收,春禽静,飞雨时鸣高屋。墙头青玉旆,洗铅霜都尽,嫩梢相触。润逼琴丝,寒侵枕障,虫网吹粘帘竹。邮亭无人处,听檐声不断,困眠初熟。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行人归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车毂。怎奈向、兰成憔悴,卫玠清羸,等闲时,易伤心目。未怪平阳客,双泪落、笛中哀曲。况萧索、青芜国。红糁铺地,门外荆桃如菽。夜游共谁秉烛。
此词咏春雨,稍稍留意便会发现,全词除“飞雨时鸣高屋”、“听檐声不断”点到雨外,几乎没有对雨作正面的描写,而且即使是这两句也只点其声,未写其形。许昂霄《词综偶评》称此词“通首俱写雨中情景”,或许是对此词咏春雨而未对春雨作正面描写心存疑窦的表白。此词依我看颇合诗中禁体物一体的标准。首三句“飞雨时鸣高屋”正面切题,但没有直接描写春雨的形态:“墙头”三句写新竹经雨之后,竿上之嫩粉洗尽,显出无限清新,则非春雨莫属,故是通过竹呈现春雨;“润逼”三句,体察入微,触人心弦,“润”者,雨也,“寒”者,春也,“吹”而且“粘”者,微风吹拂雨丝也,皆非写春雨而句句非春雨当不得;“邮亭”三句,再以“檐声”示意雨,而“困”字则暗合“春”意;下片“流潦妨车毂”,暗切雨;最后数句“青芜国”、“红糁铺地,门外荆桃如菽”,更是非春雨莫可当。基于此,我认为此词当属词中禁体。
由于诗中禁体,即东坡所谓“白战体”,在北宋诗坛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此词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周邦彦在追求词的艺术表现技巧的过程中对于诗歌新法的引进,是一次大胆的但意义非凡的创造!周邦彦之后,词中禁体之名在宋代虽未曾被人拈出,但姜夔、吏达祖等许多著名词人皆有禁体名作传世(如姜夔《齐天乐》咏蟋蟀、史达祖《绮罗春》咏春雨、《东风第一枝》咏春雪等),这与周邦彦的开创之功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的。
在一些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咏物词亦有过人之处,比如典故、代字的运用,对于字句的雕琢锤炼,下字运意能虚实相生等,这与他对于词的一贯的艺术追求有着密切关系,是周词的共有特点,学界对此论之已详,不再赘述。
(收稿日期:2000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