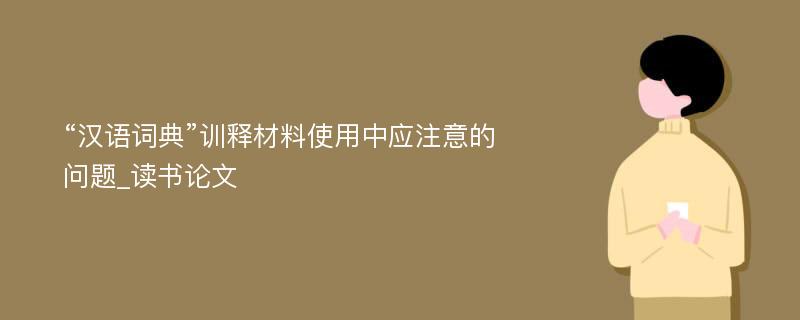
语文辞书利用训诂材料应避免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书论文,语文论文,材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辞书,特别是大型语文辞书,在解释字词意义时利用训诂材料很有好处,也十分必要。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即如何科学地利用训诂材料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科研课题。本文仅以《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字典》与《大词典》)为例,从“避免”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笔者以为,语文辞书利用训诂材料,应注意避免出现以下问题:
一 单字为训
“单字为训”指的是只用一个单音节词解释词义。这在古代传注训诂及辞书训诂中十分常见,其典型格式为:“某,某也。”如,《诗经·鄘风·柏舟》:“之死矢靡它。”毛传:“矢,誓;靡,无;之,至也。”《尔雅·释诂》:“朝、旦、夙、晨、晙,早也。”即是。由于用来解释的词是单音节词,出现在书面上是一个字,因而称之为“单字为训”。单字为训的优点是简明扼要;缺点则是释义常常不够明确:因为一个汉字往往可以记录不止一个词,而一个单音节词又往往具有不止一个义项。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人解释词义经常使用单字为训的方式,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新编的语文辞书还是仅仅满足于照抄古书中单字为训的现成训诂材料,就不很好了(当然,对于个别的使用了意义单纯的单音节词作解释词的单字为训,我们也不一概反对)。下面是取自《大字典》与《大词典》中的例子:
(1)《大字典》“底”字下义项③:“致。 《玉篇·厂部》:‘厎,致也。’《书·皋陶谟》:‘朕言惠,可厎行。’孔传:‘其所陈九德以下之言,顺于古道,可致行。’《孟子·离娄上》:‘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赵岐注:‘厎,致也。’”(第一册第70页)
(2)《大字典》“依”字下音项(二)义项②:“安。 《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朱熹注:‘依,安也。’”(第一册第153页)
(3)《大词典》“淩”字下义项①:“乘。 《楚辞·九章·哀郢》:‘淩阳侯之汎滥兮,忽翱翔之焉薄。’王逸注:‘淩,乘也。’”(第5册第1341页)
(4)《大词典》“滑[2]”字下义项②:“治。《庄子·缮性》:‘缮性于俗,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陆德明释文:‘滑音骨,乱也。崔云:治也。’郭庆藩集释引俞樾曰:‘此当从崔说为长。’”(第5册第1478页)
(5)《大词典》“招[2]”字下义项①:“举。《国语·周语下》:‘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韦昭注:‘招,举也。’《汉书·陈胜项籍传赞》引汉贾谊《过秦论》:‘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颜师古注:‘邓展曰:”招,举也。”苏林曰:“招,音翘。”’《后汉书·班固传上》:‘招白间,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李贤注:‘招,犹举也。’”(第6 册第511页)
以上5例,都是照搬古书旧注,采用单字为训的释词方式。 因用作解释词的单字(单音节词)都具有不止一个义项,其提供给读者的信息是不明确的。如例(1)的“致”,在所举《尚书》、 《孟子》例子中究竟是“精致”义,还是“情致”义,还是“招致,致使”义,还是“达到,实现”义,还是“获得,得以”义,或是别的什么意义,读者懂者自懂,不懂者查了《大字典》后还是不懂。(注:笔者以为此“致”在所举例子中似可解释为“得以”。)例(2)的“安”, 究竟是指“安定,安宁”(形容词),还是指“安置,安顿”(动词);例(3 )的“乘”究竟是“乘机”的“乘”(介词),还是“乘坐”的“乘”、“驾御”的“乘”(动词);例(4)的“治”究竟是“治理, 整治”义,还是“惩治,处治”义,还是“治疗,医治”义,或是别的什么义,读者也都无法从如此这般的解释中得到明确的答案。至于例(5), 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我们注意到《大词典》所举书证,《周语下》“招人过”的“招”,其释为“举”,是“举出,列举”的意思;《过秦论》“招八州”的“招”,其释为“举”,是“攻克,占领”的意思;而《班固传上》“招白间”的“招”,其释为“举”,则是“拿起,举起”的意思。(注:白间:李贤注以为:“盖弓弩之属”。《通雅·器用·戎器》也说:“《御览》引《风俗通》:‘白间,古弓名。’”)这种使用一个多义字来总括、兼释不同词义的做法是很成问题的。(注:这种做法《尔雅》已见,前人称之为“二义同条”。如《释诂》曰:“台、朕、赉、畀、卜、阳,予也。”其中释“台、朕、阳”的“予”,是第一人称代词的“予(yú)”;释“赉、畀、卜”的“予”,是动词“给予”的“予(yǔ)”。
二 释以文言
今天编的语文辞书,是给今天的人看的,解释词义理应用现代汉语。如果不用现代汉语而用文言,或者文白夹杂,不但会增加读者阅读理解的难度,有时还可能引起误解,因而是应该避免的。新编语文辞书之所以会存在“释以文言”的现象,往往是因为在利用旧有训诂材料时忘了将原来的文言词语翻译成现代汉语。例如:
(1)《大字典》“俞”字下音项(一)义项③:“然,应允。 《文选·扬雄〈羽猎赋〉》:‘上犹谦让而未俞也。’李善注引张晏曰:‘俞,然也。’”(第一册第155页)
(2)《大字典》“即”字下义项②:“就;接近;靠近。 《尔雅·释诂下》:‘即,尼也。’郭璞注:‘尼者,近也。’五代徐锴《说文系传》:‘即,犹就也。’《诗·卫风·氓》:‘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郑玄笺:‘即,就也。’《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邢昺疏:‘就近之则颜色温和。’”(第一册第316页)
(3)《大字典》“刘”字下义项⑧:“好貌。后作‘瀏’。 《集韵·有韵》:‘瀏,好也。或作刘。’《诗·陈风·月出》:‘月出皓兮,佼人刘兮。’陆德明释文:“刘,本又作瀏。好貌。’”(第一册第359页)
(4)《大词典》“闤”字下义项①:“市垣。 《文选·张衡〈西京赋〉》:‘尔乃廓开九市,通闤带闠。’薛综注:‘闤,市营也。’晋·崔豹《古今注·都邑》:‘闤者市之垣也。’”(第12册第173页)
(5)《大词典》“顾”字下义项⑾:“乃。 《战国策·赵策一》:‘秦被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而小弱顾能得之强大乎?’诸祖耿集注引王引之曰:‘顾与乃同义。’”(第12 册第359页)
以上例(1)用来作解释词的“然”,例(2)用来作解释词的“就”,例(3)用来作解释语的“好貌”,例(4)用来作解释语的“市垣”,例(5)用来作解释词的“乃”,便都是文言词语。其实例(1)“然”义即是“应允”,用一“应允”已经解释清楚,加一文言词“然”反生混乱。例(2)“就”即“接近;靠近”,也可省去。例(3)“好貌”改用现代汉语可说成“美丽的样子”。例(4 )“市垣”可改说成“市场的围墙”。例(5)“乃”可改说成“却;反而”。 这样改成现代汉语以后,即使普通的读者也都可以见文知义了。
三 错套义项
汉语一词多义极为常见。语文辞书在解释词义时利用训诂材料,稍不留心,就有可能误会古人本意,而将甲义错释为乙义。例如:
(1)《大字典》“与”字下音项(一)义项⑤:“允许。 《论语·述而》:‘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朱熹集注:‘与,许也。’《史记·五帝本纪》:‘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司马贞索隐:‘与,犹许也。’《资治通鉴·汉武帝绥和元年》:‘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胡三省注引颜师古曰:‘与,许也。’”(第一册第251页)
(2)《大字典》“惓”字下音项(一)义项①“同‘倦’。 疲劳;劳累。……《太玄·玄文》:‘仰天而天不惓,俯地而地不怠。’司马光集注:‘惓,与倦同。’”(第四册第2318页)
(3)《大词典》“崇”字下义项⑤:“重复。 《书·盘庚中》:‘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孔传:‘崇,重也。’”(第3册第843页)
例(1)“与”字该义项下所举3条书证,注家皆释为“(犹)许也”。然而所说的“许”,意为“赞许;推许”,(注:其中书证之二,司马贞索隐在“与犹许也”之后紧接着又说:“言万国和同,而鬼神山川封禅祭祀之事,自古以来帝皇之中,推许黄帝以为多。”所言“与犹许也”之“许”,即“推许黄帝以为多”之“推许”,甚为显然。)《大字典》误解为“允许”,大误。例(2 )《太玄·玄文》“仰天而天不惓,俯地而地不怠”二句,“惓”“怠”对文同义。此“惓”虽诚如注家所言同“倦”,不过是取“懈怠,懒惰”之义,(注:《大字典》“倦”字下义项②即为“厌倦;懈怠”。(第一册第183 页))而非“疲劳,劳累”之意。郑万耕先生曰:“惓、怠,皆懈惰之义。”(注:见《太玄校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2月版。 )可谓的论。《大字典》所释非是。例(3)《书·盘庚中》书证, 孔传释“崇”为“重”,然据其下串讲句意所言:“今既失政,而陈久于此而不徙,汤必大重下罪疾于我,曰:‘何为虐我民而不徙乎?’”则“重”非取“重复”义,而是“大大地,重重地”的意思。陆德明《释文》:“重:直勇反;又,直恭反。”也把音zhòng(直勇反)放在首位。周秉钧先生译该句作:“而耽误政事,长久居住在这里,先王就会重重地降下罪疾”,(注:见《文白对照十三经》本周秉钧注译《尚书》。)甚是。《大词典》错套义项,释此“重”为“重复”,不确。
四 不辨能(指)所(指)
这里所说的“能指”,是指词在贮存状态下的一般概念;这里所说的“所指”,是指词在进入语境后的特殊体现。比如“人”这个词,它在贮存状态下的一般概念是“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注: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这个概念可以涵盖男女、老少、古今、中外、贤愚、美丑等等各式各样的人,这是能指。而在具体的语境中,它有时可以特指某一类人,如:《左传·文公十三年》:“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人”特指有才能的人,杰出的人;《孟子·离娄上》:“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人”特指在位的小人。这是所指。传注训诂中常见的随文释义,属所指义。一般来说,语文辞书里的词义,只列能指义,无须也无暇为各种随文释义的所指义设立义项。不辨能指、所指,随文释义,随文设义,势必义项庞杂而无当。例如:
(1)《大字典》“夜”字下音项(一)义项③:“凌晨, 天快要亮的时候。《周礼·春官·鸡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郑玄注:‘夜,夜漏未尽鸡鸣时也。 ’”(第一册第285页)
(2 )《大字典》“场”字下音项(一)义项⑤:“鹿栖息的处所。《小尔雅·广兽》:‘兔之所息谓之窟,鹿之所息谓之场。’《诗·豳风·东山》:‘町疃鹿场。’孔颖达疏:‘鹿场者,场是践地之处,故知町疃是鹿之迹也。’”(第一册第462页)
(3)《大字典》“山”字下义项②:“特指‘五岳’。 《书·禹贡》:‘奠高山大川。’孔传:‘高山,五岳。大川,四渎。’《国语·周语中》:‘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韦昭注:‘山川,五岳、河海也。’南朝宋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晷纬昭应,山渎效灵。’李善注:‘山,五岳也。’”(第一册第759页)
(4)《大词典》“子[1]”字下义项③:“专指女儿。《诗·大雅·大明》:‘缵女维莘,长子维行。’毛传:‘长子,长女也。’”(第4册第163页)
(5 )《大词典》“孤”字下义项③:“特指为国事而死者的子孙。《管子·中匡》:‘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尹知章注:‘孤,谓死王事者子孙。’”(第4册第212页)
以上例(1)“凌晨, 天快要亮的时候”是“夜”在《周礼·春官·鸡人》该句中的所指义,它并没有超出“夜”的能指义“指从天黑到天亮的一段时间”(注:见《大字典》“夜”字下音项(一)义项①。)的范围,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另立此一义项。例(2 )“鹿栖息的处所”也只是“场”在“鹿场”这一具体语境中的所指义。《小尔雅》虽言“鹿之所息谓之场”,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场即鹿之所息”的结论。再说孔疏称“场是践地之处”,似也并不局限于鹿。例(3 )“特指‘五岳’”也是“山”在所举各例中的所指义。试想,如果我们见到《左传·宣公二年》“宣子未出山而复”,因而又为“山”立一义项“特指温山(在今河南省修武县北五十里)”;见到苏轼《凌虚台记》“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因而再为“山”立一义项“特指终南山”;见到苏轼《石钟山记》“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因而复为“山”立一义项“特指石钟山”;见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因而更为“山”立一义项“特指褒禅山”,没完没了,谁胜其烦?例(4)、例(5)所引旧注,也都属于随文释义,相应义项为所指而非能指,并宜省去。
五 混淆(能)指(立)意
一个词除了有能指义、所指义之外,还可能有命名之义——孙雍长先生称之为“立意义”。(注:见《训诂原理》,语文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29页。 )通常语文辞书所要解释的词义是词在贮存状态下的一般概念,即词的抽象指谓,也即我们所说的能指义(解释名义、探求语源的专门辞书除外)。由于古人解释词义,往往并不区分能指、立意,而采用同样的训释方式,因此今天我们编写语文辞书,在利用旧有训诂材料的时候,就存在着一个避免误将立意义当成能指义的问题。以下是两个反面的例子:
(1)《大字典》“干”字下音项(二)义项①:“捍卫。 ……《诗·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毛传:‘干,扞也。’”(第一册第406页)
(2)《大词典》“履”字下义项⑿:“礼。 《易·序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王弼注:‘履者,礼也。’”(第4 册第55页)
以上例(1)“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是一个判断句, 宾语“干城”只能是名词性而不可能是动词性,因而“干”解释为“捍卫”是错误的。后世注《诗经》者多释“干”为“盾”(注:朱熹《诗集传》:“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捍外而卫内者。”),甚确。“干”在古代是常见物,其所指谓,人人皆知,因而毛传但释其立意义,旨在通过解释“干(盾)”的命名之意来揭示“干”的功用。《大字典》不明就里,误以为能指义,非是。例(2)“故受之以履”的“履”是卦名, 今人注本一般都加上书名号作“《履》”。王弼注“履者,礼也”,其意也在解释履卦得名之义。因为履卦“象征小心行走”,(注:见《文白对照十三经》本黄寿祺、张善文注译《周易》卷一《履》译文。)符合于礼,故取名“履”。《大词典》显然也把立意义与能指义混淆了。
六 断章取义
语文辞书利用旧有训诂材料,必须注意吃透原文,完整领会作者本意,千万不可断章取义,冤枉古人。反面的例子如:
(1)《大字典》“任”字下音项(一)义项⒃:“立功。 《周礼·天官·大宰》:‘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郑玄注:‘任,犹倳也。’孔颖达疏:‘倳,犹立也。……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第一册第123页)
(2)《大字典》“其”字下音项(二)义项⑤:“极,甚。 《韩非子·初见秦》:‘是故秦战未尝不尅,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王先慎集解:‘《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极大,为下“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势,若作其,则文气平实。其当为甚之残字。’”(第一册第246页)
(3)《大字典》“名”字下音项(一)义项⑦:“大。 ……《书·武成》:‘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孔颖达疏:‘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第一册第583页)
(4)《大字典》“崩”字下义项⑩:“厚。 ……《谷梁传·隐公三年》:‘厚曰崩。’”(第一册第781~782页)
(5)《大词典》“届”字下义项①:“行动不便。 《诗·小雅·节南山》:‘君子如届,俾民心阕。’俞樾《群经平议·毛诗三》:‘言君子所行如不便于民,则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之心闭矣。’”(第4 册第27页)
(6)《大词典》“決”字下义项⒁:“果断。 ……《文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耻辱者,勇之決也。’李善注:‘勇士当于此果決之。’”(第5册第1017页)
以上例(1)郑注释“任”为“倳”, 孔疏谓“倳”犹“立”,所释“任”义只有“树立,建立”之意而不及功业,今《大字典》释为“立功”,当从孔疏下文“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一句得来,实则孔疏该语在于串讲句意,并非专释词义,引作“任”有“立功”义之依据,完全是断章取义。例(2 )王氏集解明明是说“‘其’当为‘甚’之残字”,《大字典》竟引以为“其”有“极,甚”义之证明!例(3)据孔疏实难得出“名”有“大”义。 “山川大乃有名”既不等于说“大,名也”,更不同于说“名,大也”。“名、大,互言之耳”则是说此处“名山大川”采用了“互文相足”的修辞手法,(注:互言即互文,也称“互义”、“互体”、“互辞”等。贾公彦《仪礼疏》曰:“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云互文。”)“名”不专修饰“山”,也修饰“川”;“大”不专修饰“川”,也修饰“山”。“名山大川”等于说“名山大山,名川大川”。因而并不能作为“名”可解释为“大”的证明。例(4)所引《谷梁传·隐公三年》书证, 其前后文字是:“(经)三月庚戌,天王崩。(传)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李维琦先生译其传文作:“高的(坍了)叫崩,厚的(毁了)叫崩,尊贵的(死了)叫崩。说天子死为崩,是因为他尊贵。”(注:见《文白对照十三经》本李维琦注译《春秋谷梁传》。)由此可知,“厚曰崩”一句是传文作者在解释何以天子之死称“崩”时提到的可以称之为“崩”的几种情况之一。《大字典》完全不理会前后文,单独截取“厚曰崩”三字来证明“崩”有“厚”义,极为不妥。例(5)且不论俞说是否符合诗意, 但说不能从中得出“届”有“行动不便”之义,则是无庸置疑的。例(6 )《大词典》以李善注证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耻辱者,勇之決也”之“決”为“果断”义,实际是截用李注“勇士当于此果決之”中之“果”来解释,显然也是断章取义。
七 以讹传讹
前代训诂材料至论固多,谬误也属不少。因此利用之前进行一番认真鉴别、取舍,十分必要。否则极易以讹传讹,贻误读者。例如:
(1)《大字典》“占”字下音项(一)义项⑦:“照顾;问候。 《后汉书·楚王英传》:‘英至丹阳,自杀……以诸侯礼葬于泾。遣中黄门占护其妻子。’李贤注:‘占护,犹守护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谦部》:‘犹候问也。’”(第一册第93页)
(2)《大字典》“保”字下义项⑤:“安。 ……《诗·小雅·楚茨》:‘神保是饗。’毛传:‘保,安也。’郑玄笺:‘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第一册第160页)
(3)《大词典》“作[1]”字下义项⑿:“耕作。《书·尧典》:‘平秩东作。’孔传:‘岁起于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 ’”(第1册第1245页)
例(1)《楚王英传》之“占”实为“苫”字省文, 而用同“赡”。“赡护”意谓赡养看护。李贤注误。例(2)“神保是饗”,“神保”是一个词,已成公论。王国维说:“神保、圣保,皆祖考之异名。”(注:见《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高亨曰:“古人认为神是人的保佑者,所以称神为神保。”(注:见《诗经今注》。)毛传、郑笺并误。例(3 )《书·尧典》“平秩东作”句之释义当以周秉钧“辨别测定太阳东升的时刻”(注:见《文白对照十三经》本周秉钧注译《尚书》。)为的论。“作”义指“起来,升起”。孔传所言,总嫌牵强。
八 义证不符
语文辞书引用训诂材料,目的是为了证明释义有其依据。如果引用的材料不能支持释义,就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甚至还有反作用,因而也是必须避免的。例如:
(1)《大字典》“倚”字下音项(一)义项⑨:“佩带。 《礼记·曲礼下》:‘主佩倚,则臣佩垂。’郑玄注:‘倚,谓附于身。’”(第一册第173页)
(2)《大字典》“域”字下义项⑤:“居处。 《孟子·公孙丑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磎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朱熹注:‘域,界限也。’”(第一册第451页)
(3)《大字典》“蹶”字下音项(一)义项④:“急遽貌。 ……《庄子·在宥》:‘广成子蹶然而起。’陆德明释文:‘蹶,惊而起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司马贞索隐:‘《埤苍》云:“蹶,起也。”’《礼记·曲礼上》:‘衣毋拨,足毋蹶。’郑玄注:‘蹶,行遽貌。’”(第六册第3738页)
(4)《大词典》“勾[1]”字下义项①:“弯曲。《尚书大传》卷五:‘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勾领。’郑玄注:‘勾领绕颈也。 ’”(第2册第174页)
(5)《大词典》“域”字下义项⑦:“谓划分区域而居。 《孟子·公孙丑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磎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赵岐注:‘域民,居民也。’”(第2 册第1114页)
以上例(1)郑注称:“倚,谓附于身。 ”“附于身”准确的理解应是“贴靠身体”。《曲礼下》此二句的意思是:“主人(身体直立)腰佩贴靠着身体,那末臣子就要(上身前倾)让腰佩悬垂下来。”《大字典》引作“倚”有“佩带”义书证,真不知从何谈起。例(2 )朱注“界限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界定限制”,就是“划定圈子,无使逾越”,与“居处”义也风马牛不相及。例(3 )所引陆德明释文“惊而起也”、司马贞索隐“起也”并不能说明“蹶”有“急遽貌”义,不如但留《庄子》、《史记》书证,不用注文。至于《礼记》书证,郑注既云“行遽貌”,则又当作同一音项下义项③“疾行,跑”之例证才是。例(4)郑注以“绕”释“勾”,与“弯曲”义也不相符。例(5)释义大体正确,而赵注并不含有“划分区域”之意,无助于证义,不如删除。
九 同证异解
对于同一书证中相同位置上的同一个词的意义,不同的训诂家或许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其中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字典、词典作为语词解释典范之书,利用旧注必须择善而从,不能“兼收并蓄”。相同的书证不应该有不同的解释,同证异解必须避免。如:
(1)《大字典》“衡”字下义项⑧:“北斗第五星。 ……《汉书·天文志》:‘衡殷南斗。’颜师古注引亚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第二册第847页)
又义项⑩:“北斗杓三星,玉衡的省称。……《史记·天官书》:‘衡殷南斗。’张守节正义:‘衡,斗衡也。’”(同上)
(2)《大词典》“均[2]”(音yùn)字下义项①:“古代校正乐器音律的器具。《国语·周语下》:‘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韦昭注:‘均者,均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轻浊也。’”(第2册第1059页)
同书“钧”(音jūn)字下义项④:“调节乐音。……亦指调节乐音的标准。……《隋书·律历志上》:‘景王铸钟,问律于泠州鸠,对曰:“夫律者,所以立钧出度。”钧有五,则权衡规矩准绳咸备。’”(第11册第1220~1221页)
例(1 )《汉书·天文志》与《史记·天官书》的同一句话“衡殷南斗”,《大字典》分别用在不同义项之中,并分别引用晋灼之说证明其中的“衡”指“北斗第五星”,张守节正义证明其中的“衡”指“北斗杓三星,玉衡的省称”,令读者无所适从。其实晋灼说确凿可取;张守节正义非是,相应义项必须删除。(注:说见王彦坤《〈汉语大字典〉指瑕》,《暨南学报》1998年第2期。)例(2)《国语·周语下》与《隋书·律历志上》两处内容实同,“均”、“钧”文异而通,而一音yùn,一音jūn,释义也别,实不应该。
上述九个问题,并不仅见于《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一些利用训诂材料较多的大、中型语文辞书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影响了辞书的质量,给读者带来困惑、不便,以至误导。本文提出来,目的在于引起学界注意,使日后出版的语文辞书避免或者减少出现同类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