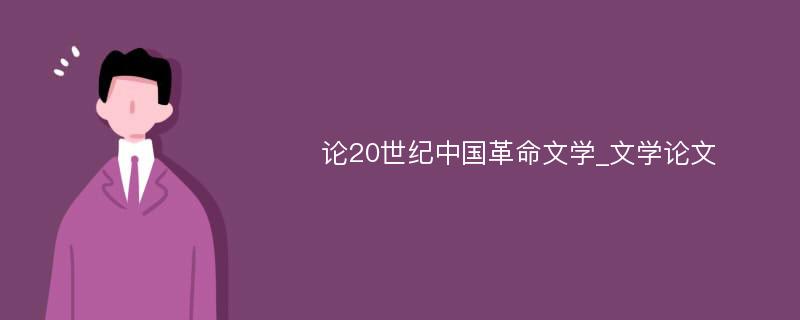
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革命文学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美学趣味、风格与范式的文学形态。从20年代末到60年代,革命文学经历了一个发生(萌芽)、发展(成熟)与终结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革命文学以其新锐的前卫品格,发出过炫目的光彩,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炫目”过后是消退,革命文学的走向终结,同样是毋须讳饰的历史事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距离之后,重新检点这笔文学遗产,或许能做到客观与公允,这也许正是本文学理上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一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中,革命文学是一支具有相当急进色彩的文学力量,它在文学领域不断地进行着急进文学实验,探索着革命文学的发展之路。蒋光慈是最早从文学实践领域开拓无产阶级诗歌流派的诗人,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莫斯科吟》中热情歌咏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我将我的心灵献给你罢,/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蒋光慈诗的革命内容,适应了特定时代的审美需求,因而具有着特殊的政治审美的艺术魅力,在向往红色革命的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产生了巨大影响。红色的30年代,左翼作家先锋性的文学实验推进了革命文学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戴平万《村中的早晨》画出了“新的农民的姿态”,这样的人物和辛亥时代的阿Q形成了尖锐的对照,“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革命怎样的在农村里发展着。”(注:编辑部:《编辑室消息》,载《拓荒者》第2期,1930年2月17日。)丁玲的《水》冲决了“革命+恋爱”的文学堤坝,把艺术的眼光投向了人民大众,以进步的阶级意识写重大现实题材,成为新小说诞生的标志。冯雪峰把这类小说的“新”质概括为:作者取用了重大的现实的题材;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注: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载《北斗》2卷1期,1932年1月。)。从文学发展的意义上把《水》与后来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联系起来看,所谓“新的小说”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新模式”,这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40年代国统区涌现出一批新型文学作品,诗歌方面的马凡陀山歌,戏剧方面的《升官图》,小说方面的《虾球传》,“它们在风格上一致地表现着一种新的倾向,那就是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发展。”(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有了根本的变化,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新的趣味,并反映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过程”(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赵树理是这一新文艺方向的杰出代表。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也富有创造性。作品发表后,茅盾评论说:“……它是一个卓越的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算过分。”(注:茅盾:《再谈方言文学》,载《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当长诗在香港出版,收入周而复主编的“北方诗丛”时,编者称它是“从西北高原上出现的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是“人民诗篇的一个里程碑”(注:周而复:《〈王贵与李香香〉后记》,《新的起点》,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长诗将鲜明的时代色彩、革命内涵与民歌形式融合在一起,显示出新诗在大众化革命化方面的新发展,为新诗创作开辟了新道路。5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文学界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达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尺度,其标志之一就是创造出梁生宝这一“新人”的典型形象。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虚构性艺术文本中,将历史人物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极富创造性地描述出40年代后期的战争。曲波的《林海雪原》在试验运用传奇体反映革命斗争方面,开拓了革命小说类型的新层面。梁斌的《红旗谱》也因艺术上的新颖创造被视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1958年,伴随着经济上的大跃进运动,革命文学开始了文艺上的大跃进,“开一代诗风”的“新民歌”写作正是为了构建一种新的革命文艺形态,《红旗歌谣》的编辑出版标志着这种写作试验的结果。“文革”时期,革命样板戏被认为是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主要形式,并赋予它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的历史意义,样板戏处于革命文学的中心地位。革命文学所进行的这些急进文学实验,表明它的不守陈规与追逐政治文化潮头的前卫姿态,这种姿态有效地激活了革命文学的生产机制,加强了革命文学力量与其他文学力量间的张力关系,给文学界以新鲜的刺激,给读者以新奇的审美感受。无产阶级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以及这一文化转变为物质力量占据上层建筑的中心统治地位,这一过程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革命文学以其急进实验行为与这一事件进程保持了一致,并通过自己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抒写出这一事件的现时性。
二
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最深刻的历史变动与心理变动,革命文学为了完成对这种历史变动的文学叙述,建构起一种叙述方式,这就是文学的宏大叙述。这一叙述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简洁的描述:在空间方面,展现革命的宏阔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中完成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在时间方面,注重革命历史感的抒写,这两方面都要围绕揭示革命的“历史本质”展开。
革命文学重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强调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认为只有“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才是“真的文学”,才是“于人类有关的文学”(注:郎损(茅盾):《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12卷7号。),因而要求文学作品应该表现时代背景,在宏大的空间场景中叙述革命历史的变动。叶紫是“左联”后期的革命青年作家,他的小说大部分都围绕洞庭湖畔农民生活展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风暴、红军的反“围剿”为重大背景,叙述几代农民走向觉醒的精神历程。《创业史》反映了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广阔的心理动向。《红日》以开阔的空间背景描写40年代的战争历史,画面的展现不仅涉及到战场,而且连结着日常生活。《红旗谱》以多卷本的结构描写相当宏大的历史画面。《红岩》的空间结构处理呈现为辐射形,由监狱延伸到城市和农村的革命运动场面。《青春之歌》描述“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之间的社会政治风云和事变,这一时代背景构成林道静人生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宏大叙述在长篇叙事诗中也有突出表现。蒲风的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作者有意识地尝试以诗来反映革命的壮阔内容,展现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胡征的《七月的战争》在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描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强渡黄河与鲁西南战役;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恢宏的艺术结构和雄伟的气势。宏大的背景可以是动态的,也可以是静态的;可以是事件式的,也可以是心理式的;可以是社会的,也可以是自然的。它的作用也是多重的,它可以是文学想象展开的场所,同时也构成审美的对象,造成一种史诗式的深沉效果。
宏大叙述落实在时间层面是革命历史感的抒写,在一定的时间长度内,描述革命事件的展开与人物的革命命运,这在革命文学所涉及的两类重要题材——农民与知识分子身上得到典型的表现。对于农民的描写,侧重从物质层面抒写农民经济上的翻身;对于知识分子的表现,侧重于展示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蔚为浩大的精神景观,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精神剧变使知识分子的人格升华到革命的境界。无论物质变动还是精神变动,这种历史过程在革命文学作家的笔下都充满剧烈的冲撞与矛盾,革命就是在这种冲撞与矛盾冲突中展开,经过一系列的历史剧变,革命的目标实现。与革命文学对充满变动的革命历史感的抒写形成对照的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另外一类作家并不以为历史总是充满革命的剧变,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历史变动掩盖下的历史沉稳的一面,这沉稳的一面才构成历史的永恒。张爱玲就曾经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张爱玲批评弄文学的人偏重于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她认为“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给人以兴奋,不能给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苦竹》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流言》。)张爱玲的作品并非绝对不涉及战争与革命,只是她处理的手段有个性,她往往把革命与战争作为背景来处理。《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安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范柳原与流苏的结局,仍旧是庸俗,他们只能如此,这种人生的安稳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张爱玲的《秧歌》对“1949年革命”的书写,与当时的革命作家以狂热的激情描写革命造成的政治巨变不同,张氏的着眼点是时代风云变化之下的土地与人群,她感悟着革命潮流底下的沉默的声音,不经意地将复杂的人性浓缩于一幅乡村日常场景中。沈从文的眼光也是投向历史变化后面的恒常因素,深思人类永恒的人性问题,在《长河·题记》中,沈从文说:“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注:沈从文:《长河》,开明书店1943年版,第1页。)此段旅行结束后写的《边城》,将一个处于从精神趋向物质、灵与欲之冲突中优美人性精神家园的困境描写出来。短篇小说集《阿金》出版时,沈从文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注:沈从文:《阿金》,开明书店1943年版,第2页。)这段话表明了沈从文的艺术观,他要在文学里供奉人性,要求自己的作品“受得住风雨寒暑,受得住冷落”,也就是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空间是时间的存在形式,时间是空间的展开,二者统一于革命文学的宏大叙述模式中。
革命文学的宏大叙述自有其形成的源流。30年代,茅盾的写作就具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宏大叙述的艺术趋向在此时已经形成。这一趋向在40年代有关战争与革命的叙事类文学作品中得到延续,50-60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将宏大叙述发挥到极致。宏大叙述的艺术形式借鉴了19世纪俄、法等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及20世纪上半叶苏联革命文学的艺术经验,这些艺术经验作为文学资源参与了宏大叙述这一艺术形式的构建。另一方面,宏大叙述也与革命作家强烈的时代意识、崇高的使命感和想充当“历史的书记官”的个人欲望密不可分。
三
革命文学是代表新兴阶级——无产阶级的文学形态,它要求文学写作“与整个的新兴阶级政治运动很密接的配合起来”,具体地“担负起对于新兴阶级解放运动的斗争的任务”(注:蒋光慈:《〈失业以后〉前言》,《中国新兴文学短篇创作选》,北新书局1930年版。),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革命文学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合法性书写,并参与无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建构。这样的文学思想对文学写作者的身份与态度提出格外的要求:文学家要以革命者的身份,采取介入革命生活的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也就是说,文学叙述必须以革命的话语展开。蒋光慈曾把革命党人与文艺家进行类比,“倘若一个从事实际运动的革命党人,当他拿手枪或写宣言的当儿,目的是在于为人类争自由,为被压迫群众求解放,那么我们的文艺者当拿起自己的笔来的时候,就应当认识清自己的使命是同这位革命党人的一样。”所以,在蒋光慈看来,所谓实际的革命党人与文艺者,不过名义稍有点不同,其实质作用没有什么差异,新作家应是“革命的儿子”,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创造者”,新作家的使命与一般革命党人所负的使命一样。蒋氏要求文艺的创造者“应认识清自己的使命,应确定自己的目的,应把自己的文艺的工作,当做创造时代的工作的一部分”,“以革命的忧乐为忧乐”,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真正地表现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捉住时代的心灵”(注:华希理(蒋光慈):《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4月号,1928年4月1日。)。历史地看来,在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发展史上,蒋光慈是革命文学的一位立法者,后来的革命文学经典理论(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文学家身份与态度的表述基本上延续了蒋光慈上述言论所提供的思路,尽管后来使用的语词有变化,但其思想的原创性起点是在蒋光慈那里。上述理路较为具体地落实在革命文学创作之中。从30年代的革命诗歌写作到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写作,作者总是以“阶级”(或“人民”)的身份出现,个人的身份被公共的身份所掩盖。作家柳青对《创业史》的写作做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注: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50年代,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生活,参与了当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他要以革命见证人的身份记录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过程。革命文学反对以个人话语方式展开的文学叙述,反对文学家以闲适的姿态、静观的态度对时代生活进行距离的观照,反对文学回到个人的内心世界。革命文学的主张受到其他文学力量的质疑。朱光潜就认为:“站在这个时代里面,想看清它的成就或失败以及它所应走的路向,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缺乏精神审视所必须的冷静与透视距离”(注:朱光潜:《我对于本刊的意见》,《文学杂志》1937年创刊号。)。朱光潜认为文学艺术“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也就是劳伦斯说的“为我自己而艺术”,作者“用意第一”“是要发泄自己心中所不能发泄的”,这一类文章永远是“真诚朴素的”(注:朱光潜:《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部徐先生》载《天地人》1936年创刊号。)。朱光潜的观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史的事实也表明,并不遵从革命文学美学规范的作家,同样创造出了具有经典品位的作品,如冯至的《十四行集》、张爱玲的《传奇》以及沈从文的《边城》。
革命文学崇尚“力”的风度,崇尚“阳刚”的美学规范,构成这种规范的审美内容是冲突,是暴力,是紧张,是沉重,是革命的坚强,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这样的审美崇尚在革命文学世界中得到生动而多样的显现。就题材形态而言,革命文学选取的题材都有很强的硬度,总是与火与血的苦难现实相连,远离冲淡平和、牧歌情调的清远之境,这样的境界即使有,也是作为革命生活的背景与陪衬出现。就情感维度而言,革命文学拒绝个人的感伤情绪,弃绝软性的个人情感,代之以刚性的革命情感。在革命文学中,革命者被赋予崇高的气节,他们是力的化身,是坚强的符号,他们能承担来自物质与精神两重压力的损害,而保持压力下的硬汉风度,这类特征在女性革命者形象的身上可以得到更为生动的映证。革命文学视野中的革命女性的阳刚化极为普泛,在这里,女性自身的性别特征已变得相当暖昧,或者说,女性的性别身份已趋向退隐,革命的阳刚之气成为女性性别特征的规定,革命性使得女性男性化,在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下,女性同男性一样,同样被“英雄”这一语词所符号化,获得一种“力”的审美效果。革命必然涉及多种政治力量的冲突,以及革命队伍内部不同力量的冲突和革命者心灵领域的斗争,这样的冲突与斗争转变为革命文学叙事,其图景就是革命力量最终征服反革命与非革命的力量,革命文学叙述关注的是通向结果的过程展开,即冲突过程中革命力量与反革命或非革命力量的较量,在此过程中完成“力”的审美。在多种力量冲突的过程中,革命文学抒写“力”的审美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革命方面虽然是现实的失败者,但却是精神上的胜利者,革命的对立面尽管是现实的胜利者,但精神上却失败了,革命者的浩然正气永远长存,革命者在悲剧性的处境中依然获得了力的崇高感,这是就精神的层面而言,革命的精神之力是不可摧毁的,这当然会起到激励人心的效果。革命文学追求“阳刚”的美学风格,是出于一种先在的革命政治理念,这一理念认定:革命力量是坚决的、勇敢的,革命者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可战胜的力量,革命文学的“力”的审美范式的形成正是对这一革命理念的适从。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充溢着浪漫的精神气息、浓郁的革命情调、积极乐观的向上情绪(与这种乐观情绪相对的感伤情绪是受到革命话语的严厉批判的),这或许与知识分子的个人气质有关。知识分子天然地具有浪漫的个性,他们对革命的想象和记忆,都充满着浪漫色彩,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文学的书写者,自然把知识者个人的精神特点带到文学中,但这种个人性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它更多地受制于集团意志和想象模式,革命文学的浪漫性归根到底是政治想象的折射。20世纪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本身充满着浪漫的实验色彩,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资源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尽管马克思经过缜密的论证,把人类思想史中的社会主义学说遗产由空想变为科学,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设定的最终目标依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革命的终极目标既然是未经现实兑现的,那么它就只能作为彼岸性的理想而存在,在此岸的现实革命实践与彼岸的未来革命理想之间,构成一种革命的时间过程,这一过程具有丰富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决定着政治想象的浪漫性。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建立解放区民主政府,创建民族国家,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带有某种实验意味。革命文学以空前的浪漫激情参与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实验。在革命政治话语里,革命被描述为:革命的明天是美好的,革命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崇高壮丽的事业,革命理想值得每一个人为之献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的目标一定能实现……,革命文学充满浪漫激情的理想主义就是这种政治话语的展开,或者说,是革命的政治想象诱导了革命文学浪漫特征的形成。
四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形成了自身的美学形态。革命文学作家积极的艺术探索,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尤其是革命文学紧密配合了政治革命的进行,在人民共和国的功劳簿上,有革命文学的一份。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充满遗憾地指出,革命文学在走向辉煌的途中,已经为自己埋下了陷阱,可以这样认为,革命文学的走向辉煌与走向终结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革命文学的步伐是由革命与文学两条腿迈进的,革命的一条腿变得越来越粗,文学的一条腿变得越来越细,最终结果是政治审美取代了艺术审美,革命代替了文学。1966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发表,标志着革命文学的终结。《纪要》指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要创造“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纪要》所表达的,是“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以来就存在的,主张经过不断选择、决裂,以走向理想形态的‘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这种思潮的“当代形态”特征,一是提出有关“革命”、也有关文学的更纯粹的尺度,一是选择上的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注: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三章《走向“文革文学”》。)。进入“文革”时代,革命文学的文学属性已丧失,革命文学已完全政治化,文本的生产、发展、阅读和批评都成为政治行为。
革命文学生命力的枯萎,与它后来的日益走向封闭有关。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革命文学被合法化为文学的正宗形态,凭借体制文化的力量,革命文学进行了文学资源的清理,这种清理既包括对革命文学之外的诸如现代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的拒绝,也包括对革命文学内部不同声音的批判。通过文学资源的清理,革命文学建立起一体化的革命文学知识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具有“纯洁性”,但也不可避免地把革命文学封闭起来,窒息着革命文学的生命。
文学生产的繁荣需要一个由各种文学力量组成的充满张力的文学机制,各派文学力量的对话有助于文学的生长。从革命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在30-40年代,革命文学力量与其他文学力量的对峙就已存在,朱光潜在1948年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一文中就对“左联”提出过批评,他说:“本来新文学运动的倡导大半是自由主义者,在白话文的旗帜下,大家自由写作,各自摸路,并无一种明显的门户意识。‘左翼作家同盟’起来以后,不‘入股’的作者们于是被尽编入‘右派’的队伍。左翼作家所号召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或普罗文学,要文学反映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在中国尚未成为事实,他们也只是有理论而无作品。”(注:《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朱光潜在这里自然是站在纯文学立场上批评“左翼”,维护自由主义文学。亦门在写于1949年的《“现代派”片论》一文中,把现代派诗人称为“变形虫”,把现代诗的盛行比喻为“流行性感冒”的“弥漫”(注:亦门(阿垅):《诗与现实》第二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第463页。),亦门指出,现代派的诗歌,“主要的思想倾向是形而上的”,“有的是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主要的艺术倾向是形式主义的”,关于现代派诗人的反抗、叛变,他认为,“第一,这种反抗或者叛变,在本质上仍旧是资本主义的。第二,但是他们所生长的年代,不幸却是资本主义底没落期,这不得不使他们有了大的痛苦,感到了最后的绝望”,因此,那种反抗的姿态,不过是一种“痛苦的姿态”罢了,“他们底诗中是这样熏腾着没落期的资本主义的圣餐底香气:颓废主义,伤感主义,神秘主义,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失败主义,逃避主义,……。”(注:亦门(阿垅):《诗与现实》第二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第465~467页。)对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诗人对现代派的接受,作为七月派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的亦门持批判态度,他说,现代主义“在中国,奇怪地,这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所移植的罂粟花啊。在旧美学的传统上得到了它底园圃,在欧风美雨中得到了它底温度和养分,和遗老遗少们交游而起了同化作用,和男女才子们结合而有了混血种(注:亦门(阿垅)曾把穆旦、郑敏作为现代派诗歌中男女才子的代表,参见亦门《诗是什么》,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而成为人生上的梦游倾向,和艺术上的技巧论倾向。”(注:亦门(阿垅):《诗与现实》第二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第467~468页。)40年代左翼文学界对文学力量的描述和划分有三类:革命作家、中间作家和反动作家。在革命文学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和冲突,如胡风实际上被看作是革命文学界的异端力量。从文学史的眼光来看,30-40年代文学界各派文学力量的对峙并不妨碍它们各自的发展,而且,各派文学力量也并不是绝对的水火不相容,相反,它们倒是在相互的冲突中形成一种张力关系,推动着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50年代,随着革命文学在政治上合法性中心地位的确立,革命文学与其他文学力量多元并存的局面不复存在,革命文学成为文学界统一的规范力量。规范的确立,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文学等级秩序关系的建立,表面上看来,新的文学秩序将革命文学力量提升到主流地位,有利于促进革命文学的生长,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新的文学秩序实质上是摧毁了革命文学赖以存活的健康的文学竞争机制,从而也就导致了革命文学的终结。
革命文学在处理政治工具本位、宣传本位与艺术本位的关系方面,也存在着尺度的偏狭。革命文学从未放弃过对政治本位的追求,把文学当作革命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追求马克思所批评的“席勒化”倾向。50年代,革命文学在参与为新政权建立进行意识形态合法化书写的过程中,艺术本位的色彩已日趋消失,政治工具本位与宣传本位的功利性诉求无限度地膨胀,直到“文革”时代文学的彻底政治化,革命文学的终结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历史事实。
从文学本位的意义上来看,革命文学形成了自身的一系列文学规则,这些规则结晶着革命文学作家文学探索的艺术经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不乏生命的活力,显示出革命文学的类型特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艺术规则在革命的“经典”化过程中,已经变成模式,走向凝固,缺少新鲜的发展,正是这些规则的教条化与公式化,束缚了革命文学自身。
革命文学走向终结的文化远因也是有迹可寻的。本世纪以来急进主义的“左”倾文化思潮对革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革命文学兴起时对五四文学的批判,直到“文革”时期对几乎所有文学经典的革命性“颠覆”,革命文学始终在对旧的文学传统与异己的文学力量进行着批判并与之决裂,在革命的旗帜下,不断地进行破坏,不断地进行立异标新的创造,企求文学的“纯革命”化,这种急进的文化行为导致了革命文学的灾难性后果。文学毕竟是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它不能割断与过去时代人类审美经验的关联,文学之树只有植根于人类艺术经验积淀的土壤才能永远常青,无根之树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