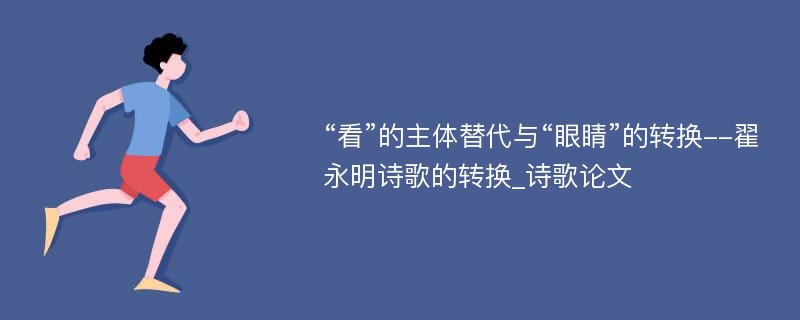
“看”的主体置换与“目光”的挪移——翟永明诗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主体论文,目光论文,翟永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09-0025-07 人是唯一不知道自己目光的人。 ——罗兰·巴特《埃菲尔铁塔》 画家何多苓笔下的诗人翟永明,给人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那双独一无二的大眼睛:黑白分明,目光专注、纯粹、犀利、神秘、执著而空洞,仿佛洞悉一切,又好似茫然无措。“人是唯一不知道自己目光的人”,[1]正因为不知道,所以人就一直在破译和追寻。“看”是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首要方式,“先于谛听的,始终是观察,是看,是隶属于眼睛的每一个细小的毛孔面对天下万物的全面打开,是对周遭世界的彻底扫描、逼视和吸纳。”[2]70对于诗人翟永明而言同样如此,用眼睛认知世界,用语言记录认知,用心灵捕捉诗意,用诗歌反观内心。纵观30年的持续创作,无论是1980年代、90年代还是当下,翟永明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念始终在“看”的行为统摄下,推进、变化、拓宽和深入。“看”是进入翟永明诗歌世界的一扇有效言说之门——“看”的行为本身一直存在,只是“看”的立场和“看”的维度发生了变化:诗人时而作为客体——“被看”,时而作为主体——“我看”,于主客体置换中,诗人的目光发生了挪移,诗歌表现空间与关注视点也随之发生变化和偏移。这一过程彰显着诗人不断成熟和自我修正的努力,同时也会给写作带来更多的困惑与难题。 系统爬梳翟永明的个人诗歌写作史就会发现,她的诗歌创作大致经历了“看我/被看——我看/我看世界”的变化,即诗歌的言说中心和基点由“我”到“世界”的位移。“我”由被关注者到关注者的变化过程,不只是诗歌言说中心的表层异变,而是表明了诗人对自我、对世界在认知上的根本性改变,由此诗歌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裂解。另外,虽然从表层看,翟永明的写作立足点从“看我”到“我看”的变化过程是历时性的,但是从内部发生肌理来说,这种变化又是共时的:虽然“被看”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翟永明早期诗风诗艺的形成,自1988年创作组诗《称之为一切》开始,“被看”立场也有逐渐被“我看”的观照视点取代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被看”焦虑的完全消逝和剔除。在《称之为一切》乃至后来的诗歌创作中,“被看”与“我看”两立场更多地扭结在一起,在诗人内心深处形成了争辩、盘诘与博弈,翟永明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也因此布满了“常”与“变”的盘根错节,并形成颇具个人特质的矛盾复杂文本——“正如你所看到的”。(翟永明《潜水艇的悲伤》) 一 被看/……看“我” 看我的眼睛,你在我瞳仁里看得到你自己吗? 我在您的瞳仁里显得那么小,我看不清自己。 ——让-保罗·萨特《禁闭》 假如不是借助于镜子,人对自我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它物或者自我想象来完成。而他人和它物的看法又是自我想象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对自我形象的体认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者”的态度和目光。“他者”的观察视点和“看”的角度对自我认同起着决定性影响。 1980年代,具有鲜明性别印迹的“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被推到文化的前台,写就了“女性诗歌”发展过程中最为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无可辩驳地把“女诗人”置于“被看”的场域之中。其他人都在“看我”,我成了“被看”对象,甚至是自我想象中的“惟一”对象,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翟永明。“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卞之琳《断章》),居于“被看”位置的诗人,不是作为单纯的风景被欣赏,而是要承受带有明显歧视和误解的巨大压迫感的目光:“那些巨大的鸟从天空中向我俯视/带着人类的眼神/在一种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预感》)。装扮成道德上帝和雄性权威的“巨大的鸟”,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由天空向大地的众生“俯视”。相对于“仰视”和“平视”,“俯视”这一行为本身就隐含着强烈的不平等色彩:我是“偶然被你诞生”的,“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独白》)。面对“雄性”和“权威”,诗人充满焦虑和不安,甚至还有恐惧:“我是一粒沙,在我之上和/在我之下,岁月正屠杀/人类的秩序”(《臆想》)。而且,“我”的不安感和焦虑感会随主观臆想不断自我强化,因为“你优美的注视中,有着恶魔的力量”(《渴望》)。“所有这些眼光全都落在我身上,所有这些眼光全都在吞噬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即是地狱。”[3]151在萨特的名剧《禁闭》中,三个因生前犯罪而被关进地狱监牢的人,在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里共同生活,没有黑夜,分秒不关闭的灯把三个人的所有隐私暴露在相互的目光中,三个人都痛苦不堪却又无处遁逃。诗人翟永明所遭遇的,正是“被看”的地狱。因为被置于“被看”的位置,“我”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者”,成为自我注视和他人言说的中心。诗人无法摆脱这种尴尬和焦虑的窘境,却又试图突围,于是便以两种看似无关实则有密切关联的姿态来疗治恐惧症和减轻焦虑:一种是对抗/反抗,即以“雄性”对立面“雌性”的身份,决绝地拒斥和解构“他者”冰冷的目光,以建造自我生存空间;另一种是自我体认和再造,诗人要在弥漫巨大误解的目光中,重新建构自我价值,以驳斥歧视消除误解,并舔舐伤口自我抚慰。于前者,诗人找到了适合自我生存的空间和时间恒量——黑夜;于后者,则发现了自我认同和获得存在感的突破口——滔滔不绝的组诗和独白的话语方式。 难道永远没有黑夜吗? 永远没有。 你永远看得见我吗? 永远。[3]152 如果不想被“看得见”,就要置身黑夜。在翟永明的诗歌中,“黑夜”既是现实中的时空概念,更是隐喻层面的心理事实。“如果你不是一个囿于现状的人,你总会找到最适当的语言与形式来显示每个人身上必然存在的黑夜,并寻找黑夜深处那惟一的冷静的光明。”[4]相对于白昼,“黑夜”更加隐秘,更加私密,也更适合自我言说。因为可以暂时摆脱“被看”的惊恐与不安。“黑夜”的另一特点是可以同时满足诗人保护“隐私”和实现“偷窥”的两种诉求:不是没有“被看”而是无法被他者看见。与此同时,黑夜中的“我”却可以悄悄观察处于白昼(包括灯光)中的他者。更为重要的是,“黑夜”之后便是“希望”和“永明”(与诗人翟永明的名字不谋而合),“今晚所有的光只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两个白昼之间夹着一个夜晚/在它们之间,你的黑色眼圈/保持着欣喜”(《渴望》)。于是,诗人酷爱“黑夜”,“黑夜意识”成为诗人创作早期最为醒目的标签:“我称之为‘黑夜意识’的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个人挣扎,以及对‘女性价值’的形而上的极端的抗争。”[4]于是在内心深处,诗人一直“渴望一个冬天,渴望一个巨大的黑夜”(《独白》)。 在“黑夜”中,由于暂时逃离了“被看”的窘境,诗人获得了无限言说与阐释的自信与空间,她以创世者的母性身份缔造生殖童话,并以世界拯救者的身份获得高高在上的认同感和优越感,“我创造了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世界》)。进而以女人的身份与母亲进行平等对话,以期获得臆想和幻想之外的力量与信心。然而,与母亲对话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从母亲那里除了获得生命之外,只获得了与生俱来的“劣势”性别,没有期待中的幸福和优势,而是从此“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母亲》)。岂止是我与不幸,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和母亲又何尝不是不幸的双胞胎呢?“你的眼睛拥有黑暗而进入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而“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母亲》)。现实中的难以获得让诗人唯有再次进入“夜境”中“憧憬”,①却只闯入了“渐渐感到害怕”(《夜境》)的“噩梦”中无法自拔。在“黑夜”中探询、质疑和呐喊的诗人是痛苦、敏感甚至神经质的,而黑夜中偷窥到的世界则是变形、异化甚至可怕的。原因在于扰乱诗人内心平静的“被看”和“看我”的立场,使得诗人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缺乏安全感,充满猜忌和不安,“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5] 除了躲避白昼,隐藏自我之外,消除猜忌和缓解不安情绪的另一方式不是噤声——噤声只会加重不安,而是不停地言说,呶呶不休地自说自话,这是诗人获得“在场感”的最直接和最简单的方式,表现在翟永明早期诗歌创作中,便是组诗体式和独白话语方式的大量运用。19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翟永明创作了大量的组诗,无论是早期的《女人》组诗、《静安庄》《称之为一切》还是90年代的《莉莉和琼》《道具和场景的诉说》《十四首素歌》,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组诗的方式。尽管翟永明曾多次申明,她所尊奉的诗歌写作技艺是“少就是多”(密斯·凡·德罗语),但是情感的长期积压和酝酿以及亟须疏导的焦躁情绪,使诗人不得不以喷薄的方式来抒写内心,“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激情、痛苦甚至绝望要表达。她以滔滔不绝的语势、一泻千里的激情,诉说着女人的痛苦与渴望,以尖锐的声调向世界发出了几近拒绝的回答。”[6]在此种情况下,谁听并不重要,“我说”才是诗人惟一想达到的目的。于是喋喋不休的独白体与诗人当时的情感需求达成了契合,并成为翟永明,也是很多女诗人钟爱的话语方式。“它(诗歌)只听从命运的召唤,并把这种召唤说出来,而且只说给自己听。它是自言自语式的、独白式的;它遵从的说与听范式是:我/我关系。”[6]对我/我关系的情有独钟,使“我”成为诗人看问题的惟一出发点和落脚点。于是在翟永明的笔下,出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我的世界和他人/它物的世界:我的世界沉静、忧伤、自闭、神秘;他人的世界喧嚣、异化、粗暴等等。诗人的身份也由此分裂为二:自我世界中的受害者、反抗者和低语者;他人世界里的旁观者、冷漠者和智者,这在《女人》组诗之后的诗歌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在另一首组诗《静安庄》中,诗人刻意忽视“他者(包括人和物)”的存在,力图以独白者“我”的姿态进入静安庄,并营造一个“静安”的、在心灵上与世隔绝的世界。“我的脚听从地下的声音/以一向不抵抗的方式/迟迟到达沉默的深度”(《第四月》)。“我”想让内心听凭的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地下”的声音的召唤。对外界而言,诗人想到达沉默的深度,对诗人自己而言,则需要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营造抵御外界声音的沉默境界。于是,诗人刻意回避村庄中的各种声响,而一直执着地寻找进入“这鸦雀无声的村庄”(《第二月》)的入口。然而,试图以感受沉默的方式抵抗“看我”者敌意目光的诗人并没有在“静安庄”到达“沉默的深度”,自然、生物、劳动和生命循环的声响无时无刻不打扰着诗人渴望静安的心。因为,心所不想见者,并非眼睛看不见者,目光所及之处恰好与诗人的内心期待相背离。按照“眼耳辩证法”(敬文东语)的逻辑,“耳朵成为眼睛的下属、眼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让看包容了听、统辖了听。”[2]70在自我世界虚拟的“静”与静安庄现实的“动”的悖论面前,诗人于“被看”的目光中被迫打开了耳朵,无声的、甚至渴望以死亡的方式到达的沉默境界与公鸡打鸣、分娩的声音、村庄的声响混杂和缠绕在一起,无法厘清和剪断。于是,呈现于读者面前的《静安庄》,是一个矛盾分裂的文本,至少从声音诗学维度而言是两个声部并存的:抵抗“被看”身份的沉默无声和以旁观者身份被迫“看/听”的喧闹嘈杂。诗人反复言说和重复的“到达沉默的深度”增加了诗歌情感基调的沉寂、沉闷、沉重与沉痛。向死而不能,融入而不得的现实只能让诗人发出这样的慨叹: 距离是所有事物的中心 在地面上,我仍是异乡的孤身人 ——《静安庄·第十二月》 “我永远无法像男人那样去获得后天的深刻,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7]性别的不可选择和无法变更把诗人置于“被看”的角色定位上,她既想反抗又不得不接受无法消除的宿命感。于是在众目睽睽的他者目光中,诗人时而立世高歌,时而孤独呓语,在自信与怀疑、惶恐与期待中将自己包裹成厚厚的茧,以排他性和反抗者的姿态蜷缩在自己缔造的孤独世界里,愤怒、惊恐与凄楚。“黑夜”的时空选择和“独白”的言说方式虽然可以暂时摆脱“被看”的窘境,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因为缺少“被看”而无从证明和彰显自我的怪圈,“我的夜的隐秘无法被证明”(《证明》)。因此,“被看”成为诗人无法摆脱的魔咒和宿命,无论是高歌还是呓语,诗人试图冲破的、渴望获得的始终无法摆脱和拥有,“夜还是白昼?全都一样”(《旋转》)。于是诗人只能仍以一个“迷途的女人”的身份,承认无法完成和没有成功的结束,并在“整个冬天在小声的诘问:完成之后又怎样?”(《结束》) 二 我看……/我看世界 整个宇宙充满我的眼睛 ——翟永明《女人组诗·臆想》 “看的艺术,不光是眼睛的延伸,更重要的是精神之延伸,即布勒松所言:事实并不见得有趣,看事实的观点才重要。”[8]自《称之为一切》开始,“翟永明进入了漫长的探索期和裂变期。这首明显有着自传性质的长诗开始有意识地放缓了语调,也开始有意识地试图从独白中出走,以便进入吵吵闹闹的日常生活的集市去寻找对话者。”[6]“看”的主客体在翟永明的诗歌中开始了置换之路。“我”不再只是“看”的客体或者是“被看”对象,更是“看”的主体;诗人反复吟唱的主旋律也不再是“……看我”而是“我看……”,“我”和省略号位置的置换,不单纯是物理位置的移动,置换背后有很多内容需要探究:当“我”处于宾语位置,省略号处于主语位置时,我是受动者,是目光聚焦的中心,作为施动者的省略号毋宁说象征一种无法被拒绝的巨大压力和无上权威,类似石头一样“砸”在诗人的身上,而他者目光也像聚合光一样完全投射到诗人的心上,“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我”。于是便有了诗人“黑夜”中的低回与独白,自恋与自怜。而当“我”由受动者变成施动者时,“我”成了发光体和出发点而不是绝对的中心,并以扇形展开的姿态打开眼睛,观照外物,当目光在每一根扇骨上挪移的时候,“我”得以认知世界,世界和外物才是落脚点。当然,这种位移翟永明并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论证、争辩才到达的,是渐进的过程,从《称之为一切》便开始出现这种新的质素。还需说明的是,诗人由“看我”到“我看”的立足点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看我”立场的完全放弃,而是暗含于“我看”的视阈之下,因为女性性别本身无法被改变,“上一世纪的女人/与本世纪的女人并无不同”(《马克白夫人——致田蔓莎》)。但是于“不变”中所孕育的“变”,却致使翟永明诗歌内质发生了裂变:如果说在“被看”的场景中,她的诗歌是指向内心的话,那么在“我看”的立场上,则是向外打开/敞开的。诗人心灵的触角穿透了硬硬的自缚的茧,伸向了毛茸茸的生活本身,诗人愿意聆听的声音和诗歌内部的音频也发生了变化: 必须倾听变化的声音 当我看到年历在洁白地行走 有人在红色连衫裙下消失殆尽 变化的声音在内部行走 站在镜前,她成为衰老的品尝者 她哭喊着,从悲伤中跌下来 倾听变化的声音使我理智 让我拉开与生命对立的位置 假装我是一个顽强的形体 ——《某一天的变化》 当时间伴随着被撕下的日历,一天天逝去的时候,对镜自怜的“看我”行为注定是无效和失败的,甚至是疯狂和不理智的,“你凝视自己看她怎样在劫难逃”(《肖像之四》)。“倾听变化的声音”才能“使我理智”。“倾听变化的声音”至少有两层意思,既要学会接受和习惯自我思想和心理的变化,同时还要学会感受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这双重变化表现在翟永明的诗歌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由自我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位移;“我”之外的单复数人称代词的频繁使用以及“文本时间”②的反向延展。上述变化皆因“看”的主客体置换和目光在时空中的挪移而出现。同时三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空间的位移让更多他者进入诗人的视阈,而空间的位移又与时间的延展相辅相成。 进入90年代,翟永明完成了对以自塑自怜为特征的私人空间的突围,开始向公共空间位移,并形成了新的“空间意识”。在封闭空间的自我建构和过度想象,只能让生活像谜面本身一样暧昧不明,向着公共空间的敞开才能寻找到答案,“广大的空间成为谜底”(《称之为一切》),才能洞悉生存的真相。“80年代,我更关注的是内心的表达;90年代以后,我更多地在现实生活中进进出出,对现实的现场情景有了更强烈的感受。”[9]27翟永明坦言这种改变的缘由,是由女性诗人向酒吧老板兼诗人身份的转变,“90年代,我开了‘白夜’(酒吧)以后,对我来说,我的世界打得更开了,我对外面的观看更多了,而我开白夜就迫使我跟这个社会有所接触。这样的一种接触把我的视角打开了,因为整个现实生活涌进你的世界里面,是你无法回避的。”[10]于是,小酒馆、咖啡馆、公园、急诊室、电影院等毫无诗意的“中性”公共空间进入翟永明的诗歌,从而打破了此前“卧室体”和“私宅体”自说自话的格局。在充满交往、沟通和多种可能性的公共空间里,双重身份(酒吧老板兼诗人)的存在使诗人由自我言说中心变成了宽容的旁观者和思想者,或以看客身份客观地评价他人的故事和事故,或以配角的姿态进入与他人交往的场域,“有人在看/有人在被看/没有人错过/灵魂的一幕幕上演”(《道具和场景的述说》),并因此剔除了“我”的绝对中心立场和错觉。即使是看的主动者,诗人也没有像从前一样,假扮成圣母高声调地呐喊,而是采取了倾听和对话的方式与世界亲近,与社会对话。在异乡(曼哈顿)的咖啡馆里,诗人勾画了不同性别、不同国别的人们的生存群像:“我”、秃头老板,来自外州的一对夫妇、邻座的美女轮番登场,在交谈论辩中,或悲伤、或回忆、或慨叹,用不同声部合唱了一曲“咖啡馆之歌”;在“小酒馆”中,男和女,他和她在酒精或香精的作用下,演绎着看似美丽、实则丑陋的故事,于拒绝、坚守和沉沦中人的真实本性得以彰显。“在一个封闭空间和一个特殊时刻,人是最松弛的。也是最真实的。这是对人性洞察和描摹的最佳角度。”[11]随着诗人眼界的开阔,更广大的公共空间进入诗人的视域,翟永明以语言为思考终结点和言说根本,以诗意的方式溶解了现实、生活现场和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非诗本性,并剔除了道德审判、新闻记录等伤害诗意的毒素,拓宽了诗学言说范畴和文本表现空间。诗人处理了“汶川地震”、“广渠门事件”、“尘肺病”、歌星自杀事件甚至“政治”、“全球化”等棘手的“大”题材,创作出了《老家》《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最委婉的词》《大爱清尘》等“噬心”之作,挖掘出了现代化、都市化进程中“时代的诗意”(翟永明语)。 “我已不再年轻,也不再固执/将事物的一半与另一半对立”(《时间美人之歌》)。当诗人主动把视点转向公共空间领域时,随之变化的便是对他者的关注和凝视。在《称之为一切》中,除了“我”仍是诗人倾心言说的对象之外,还出现了“颓败的家族”。这似乎可以看成是翟永明诗歌变化的某种信号。组诗中出现了“我”之外的其他人,而且是包含着“他”和“她”两种性别,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出现的男性是现实存在的。此前翟永明诗歌中的“他”多为虚构,是由“我”分裂出来的“他”,“我”臆想中的“他”,而非真实存在的“他”,其本质还是“我”。由于诗人早期对自我空间和他人世界的主观对立性建构,我对虚构的“他”的看法是畸形和异化的,诗歌中被想象被建构的男性身上永远携带着恶魔和弱者的基因,“你的眼睛装满/来自远古的悲哀和快意”(《渴望》)。尽管在《称之为一切》组诗中,“长得像小狼一样”的兄长形象依稀可辨诗人对男性的固有异见,但是更多男性形象的涌入诗行,也在修正着诗人的某些看法,“我的叔伯兄弟蹲在死者中间/口袋装满种子/修房补墙”(《称之为一切》)。尽管阴性力量仍然被夸赞,“潮湿的母亲把整个下午安抚”(《太平盛世》),但是男性已经由空洞畸形的符号变成有血有肉的个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物种繁殖与建造“家园”的重任。当然,面对现实中的男性,想象中的对立面,诗人内心的情感是矛盾犹疑的,“我们兄妹情深”、“我的脸和你一点不像”(《南方的信》),压抑的气氛和沉郁的意象也仍旧弥漫于诗行,但是诗歌中他/她甚至它的单复数在大量使用,却让诗人获得撬动全新诗歌宇宙的杠杆。 “由于第三人称(‘他’)的引入,‘我’再也成不了中心,也充当不了界定世界的法则。我/他关系在更大的程度上表明:‘我’站在‘我’的位置上(但不是中心)观察‘他’。”[6]于是,诗人在叙述语式上由独白变成了对话。不再是自怜或者自傲,而是以平和心态与他者进行对话或者潜对话,并由此出现了戏剧性因素,单一的抒情也变成了克制内敛的叙述。《咖啡馆之歌》《重逢》《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剪刀手的对话》《壁虎与我》等等都是如此。在《壁虎与我》中,诗人开篇便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姿态与壁虎展开对话,把它当成异乡可以暂时诉说的对象,“你好!壁虎”,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了解/各自的痛苦”,但是“当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我们的目光互相吸引”(《壁虎与我》),并聊以慰藉思乡之苦(之情)。“在这里,诗中的‘说话人’冷静地观照所书写的‘对象’,在情感经验表达上,‘我’与‘它’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对象不再是‘我’情感经验和意志‘独白’的单纯载体,而是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们与‘我’构成场景—对话关系。”[12]在场景—对话关系中,诗歌表现的空间和诗歌内部的张力也由此得以扩延。 当翟永明冲破私人领地,以主动介入姿态“看世界”时,进入她视界的除却当下空间以外,还有历史空间,诗人在通过当下洞穿历史,进而对“文本时间”进行反向拉伸。于是在诗歌中,一系列历史时间、历史人物跳跃于诗行。通过对时间的拉伸,诗人力图重临两个起点:一是通过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新进入,挖掘出隐藏在古老时空里的“文化根性”,完成对现代汉诗的血液透析。比如《在古代》《在春天想念传统》《英雄》等诗歌;二是潜入历史细部完成对知音的找寻和确认,并“返身进到女性生存的历史场景中,质疑并改写已经被男权话语所书写的女性故事”。[13]如《鱼玄机赋》《前朝来信》等等。《在古代》中,诗人把古代和现代的生活方式进行了一系列饶有意味的对比,其目的绝不只是用古代的“慢”来凸显现代的“快”。恰好相反,现代只赢得了“快”的速度,而失去的却是速度之外的很多东西。“慢”生活节奏中的友爱、感情甚至诗歌理想,都被一种叫做“速度”的东西,远远地抛到古代时空里,诗人能做的只有《在春天想念传统》,实现了与古代在时间和情感上的对接: 在春天,当一树假花开放至酡颜 我想念传统 那些真的山 真的水 真的花鸟和工笔 一生中 总会与一颗高隐之心 相遇 在某些诗里 在某些画里 在莲叶里 或在鱼行间 由于女性的性别角色限定,翟永明更关注古代女性的生存状况。在《鱼玄机赋》中,诗人以历史打捞者的身份,对鱼玄机的履历进行了再现与还原,“她像男人一样写作/像男人一样交游”,但是“美女身份遮住了她的才华盖世”,只能在“如果我是一个男子”的假设和遗憾中,聊度余生。翟永明以当下为立足点,“以历史和现实中具有符号意义的女性为焦点,追溯和重新命名历史与当下的女性,波澜不惊却更为有力地颠覆了男性霸权建立的二元对立的精神/身体等级制度。”[12] 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还是对古代女性诗人价值的重新体认,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退步和文化守成,而是一种抵达文化、思想和语言根部的努力——回到文化被构建、思想被裹挟之前的时代和状态。这种努力是现代汉诗发展道路上非常重要且可贵的一步。诗人不再只把目光锁定在西方或者远方,而是以回望历史的姿态重新到达现在,并深入诗歌内脏,“借用人间的腹部/由此地走向最终的出口”(《转世灵童——给天外的我》)。 “看”与“被看”立场的延异、交叠与缠绕构成了翟永明进入世界的基本视点,成为其诗歌“变”与“不变”的决定性因素,并由此带来诗歌文本和诗学观念上的更新、变异与恒在。从诗歌创作的历时性维度而言,诗人的主体立场经历了由“被看”到“我看”之“变”,但是“被看”立场并没有被“我看”视点完全取代,而是以“暗线”的方式潜藏于诗人心灵深处和诗歌内部,这在诗人90年代及以后的创作中尤为显豁。在“变”中还有很多“不变”的因素存在,“从1984年的《女人》到1996年的《十四首素歌》,黑夜意识仍然贯穿于诗中,性别处境也依然是我(翟永明)关注的主题,不同的是我不再仅仅局限于身份,而是关心性别在不同历史和不同生命状态下的真实,以及它给写作带来的意义。”[14]这是作为女性兼诗人的翟永明,在主动修正诗学创作理念和难以逃脱“被看”命运两种处境之间博弈和互否的结果,“终于一种不变的变化/缓慢地,靠近时间的本质/在我们双肘确立的地方”(《十四首素歌之黑白片段之歌》)。“不变的变化”使得翟永明诗歌有着无法言尽的复杂性和无限阐释的空间。 2013年,翟永明出版了诗集《行间距:2008—2012》。拥有“被看”和“我看”双重视点的诗人,就像拥有“重瞳”的智者一般,在打通古今,持续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同时,进行着一种对自我和现实“重新发现”的努力。“重新发现,意味着一种特殊的对待世界和对待事物的方式,意味着对人类普遍生存境况的更深的洞察,意味着一种诗性的参与、一种自由思索的方式的参与,它是与时代和生存境况有关的。”[9]22充满着无可能性的“行间距”延展了翟永明的诗学空间,并在“不变的变化”中,不断靠近“关注现实”和“回到内心”的双重目标: 从容地在心中种一千棵修竹 从容地在体内洒一桶净水 从容地变成一只缓缓行动的蜗牛 从容地、把心变成一只茶碗…… ——《行间距:一首序诗》 注释: ①夜境、憧憬和噩梦都是《女人》组诗中的标题,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突围无力的种种矛盾和挣扎扭结在一起的状态。 ②这里所说的文本时间和一般意义上的文本时间内涵不同,主要是指翟永明诗歌中出现的不拘于时空的时间,比如古代,比如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