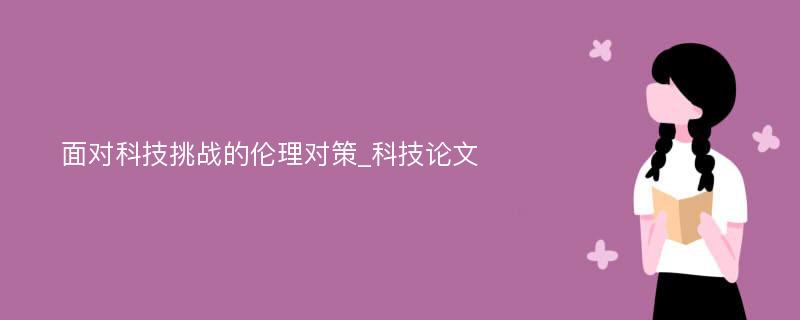
面临科技挑战的伦理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对策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01)04-022-02
伦理学如何应对科技挑战的问题就是尽量避免科技的负面影响并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的问题。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二是对人类自身的影响。
科技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的科技发展诸如炸药、原子能、化工技术、造纸技术、纺织技术、生物技术等在给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战争升级、环境污染和生存条件的恶化。正是由于资源枯竭、人口膨胀、大气和水的严重污染、酸雨、干旱、荒漠化等现代的生态环境的危机给现代人带来灾难,人类才开始从伦理的视角来探讨环境问题。当人生存于其中的无机物和动植物环境之异己已不再能提供人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个异己也有不可剥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人类在经历了一个失去伦理尺度的发展阶段之后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和伦理之间寻找一个新的统合方式,既要寻求物质生活的满足,又要使自己的精神生活过得充实,还要使自己真正明白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科技伦理学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人与环境的矛盾关系问题。因此,人类要制止这种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恢复或重建人类的美好家园,从根本上认识生态环境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如果说20世纪的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更多的是人类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的价值的渺小的话,那么21世纪生物科技的发展,如生物芯片、基因工程等许多技术所衍生的伦理道德问题,那更会令人惶恐不安。21世纪将是以人类基因组研究为中心的生命科学技术世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现,其影响之深远、震撼之剧烈远比原子弹爆炸、宇宙飞船上天对人类环境和心理的影响程度深。
然而,当梦想只是停留在潜意识的时候,人类的“超我”已经竖起了“达摩克利斯剑”——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及其应用一开始就产生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并将受到伦理的制约。人类基因组研究与物理学研究不同的是,它一开始就有伦理问题。例如,在遗传学家取血样作DNA分析前要考虑会不会侵犯提供DNA样本的人的知情权等。21世纪的生命科学技术无疑会为人类和生物界造福,但它带来的伦理挑战更是恐慌性的。例如,实施植物基因工程能解决温饱、营养问题,实施动物基因工程能保护和抢救濒危动物,人的生殖性克隆技术能保护和抢救濒危人种,干细胞克隆技术能进行自体器官移植和防止衰老,基因治疗能根治癌症、脑心血管病、艾滋病等等。同时,在21世纪,基因干预、辅助生殖、生命维持技术能使生老病死的人工安排在更大程度上代替自然安排,药物、电和化学刺激、脑芯片、脑移植、基因操纵等能使人体结构、心理、行为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人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生命科技的发展侵犯人权的可能和机会也就更大更多。试想,当个人隐私权、自主权受到侵犯,人被当作“客体”的东西加以对待,人被“客体化”时,人将何以找到“自我”,“超我”的良心到哪里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际上以及在一些先进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的经费中必须拿出一部分进行相关伦理问题研究的原因。20世纪末,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我国对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及其投入,尤其是“应担更多责任”的科技工作者对这一点的认识却停留在“本我”的水平上。
怎样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呢?需要伦理学作好充分的准备。结合我国的实际,笔者认为,伦理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科技的挑战:
一是科学精神人格化。荣格有句名言:“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美利坚文化造就了美国人,中华文化造就了中国人。当美国人G.萨顿在1920年发出“科学必须人性化”的呼吁的时候,中国才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兴起学习西方的新文化运动;当西方科学孕育出成熟的工具理性的时候,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似乎只停留在价值理性上面。而把中国看作科学人文主义肇始地之一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42年却说:“没有什么比欧美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合流更伟大”,如今又有不少西方学者发出了“东药西治”的感叹。记得江泽民主席1997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直到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保持了千年的领先地位。中国人的这些发明创造,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道德理想相结合的理性光辉。”科学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代表科学理性的“天道”与代表道德理想的“人文”是彼此契合关联的,其衍生出的伟大的科学人文精神已经确立了崇高的伦理道德范式,对后现代科学的启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未来科技发展也必定要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老子和庄子在意识到当时的文化困境的同时深刻地顿悟到文化对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导致的人类与自然界的疏离,从而构想出依据理性的引导复归于自然之“道”的理想出路。老子和庄子依据认识的相对性敏锐地提出了人类知识的可靠性和合理性问题,即人类知识的基础和是否能给人以幸福的问题,这即是科技伦理的问题。道家人道主义的自然观,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善等三个层面勾画出了一幅科技伦理的美妙图景。道家在2000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20世纪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带来的个人、社会和环境矛盾的加剧显得越来越具有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不啻为一副医治“科技病症”的方剂。当我们放眼世界,回眸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科学精神的人格化始祖在中国,科学人文主义源于中华文化。可见,不能把科学精神置于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来讨论,科学精神本应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就个体而言,科学精神是一种内外兼修的个性人格修养,对社会来说,当代科技文明的困境要求科学人性化。作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何尝不能汲取世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将科学人文主义发扬光大呢?
二是科技活动规范化。狄尔鲍拉夫在《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逐渐向其能力所及的领域扩展,这种时候应考虑的问题是凡是人‘能够做到的事,做什么都可以吗’?是不是要限制人类的任性和放纵?是不是要有一个类似行动指南的规范?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技术性行为要受道德原则的支配。”科技伦理规范是观念和道德的规范,它要规范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从观念和道德层面上规范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行为准则,其核心问题是使之不损害人类的生存环境条件和生命健康,保障人类的切身利益,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社会行为,承担着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从这点来说,在科技活动中遵守伦理规范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科技活动必将遭到人们的异议、反对,被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2000年12月2日中国人类基因组社会、伦理和法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声明,承认人类基因组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坚持人权的国际规范,尊重参加者的价值、传统、文化和人格,以及接受和坚持人的尊严和自由。科技伦理赋予科学家理智和冷静,它与法律和规章一起,保证科技专家的科技活动始终沿着造福于人类的正确方向前进。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对科技工作者的约束,同时具有普遍意义。试想,当普通老百姓心有余悸地吃着转基因食品或毁坏农作物时,当美国烟民在法官面前拿回几十亿美元烟草公司的赔偿时,我们看到的是伦理道德的力量还是法律的胜利?当我们在感受后工业社会科技与道德斗争的余波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及早着手使科技与伦理规范达到和谐的统一?因此,加强科技伦理的研究和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国家的决策者应从政策、经费、人力等方面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利、合理的科技发展机制,让国家的科技活动在一定的规范下进行。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应该重视科技伦理问题,了解、宣传科技伦理知识,让科技活动与伦理建设在合理的尺度内进行。再者,作为享受科技发展带来好处的广大群众也应该自觉加强科技伦理的修养,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否“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衡量政府一切决策、活动的根本标准和行为准则。“以人为本”永远是衡量技术发展与社会之间、科技发展与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规范。
三是科技主体责任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作为科技主体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并将技术成果应用于实践的时候,科技成为了一种独立力量的过程,工具理性日益脱离价值理性,异化为不依赖于人的敌对力量的过程,这就是手段和目的的错位和异化。但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的劳动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科学家从事科技活动的目的应该使科技造福于人类。这就是科学家的伦理责任。1948年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突出强调科学家个人或团体对于科学、社会和世界应尽的责任。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第5次大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对科学家的责任和义务作了更详细的规定,明确提出科学家要保持诚实、高尚、合作的精神,要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重视与发展科学技术所具有的人性价值。1999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科学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新世纪科学的发展应该更加富有“人性”、更有责任感。也就是说,科学应该更自觉地为人类的利益服务,更好地满足人类发展的需求,为对付疾病和抵御自然灾害服务。科学界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需求,关注公众对科学负面影响的不安,自觉地保证科学知识得到正确应用。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江泽民主席所说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是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的关于科技伦理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国科技工作者与世界其他科学家一样,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正如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在2000年23期《求是》杂志上撰文写到的:“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队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支科技队伍。无论是在新中国初创时期还是在60、70年代的困难时期,科技工作者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尤为可贵的是,这支由人民哺育的队伍深深懂得自己的神圣使命,无怨无悔地承担着爱因斯坦所提倡的比普通人对社会进步的‘更多的责任’”。
四是科技成效合理化。科技伦理的根本问题就是科技研究及运用中的道德关系问题,即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所产生的成效对人类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由于人类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局限性、失当性甚至破坏性,因而科技的研究和利用同样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有利和有害的问题,也就是科技成效的合理性问题。为了实现促进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根本价值目标,我们在研究、应用科技成果的同时,要尽可能避免、克服、减轻不合理的科技成效的潜在负面影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度对科技成效的合理性评价有不同的伦理标准,但不管有怎样的不同,都不能超脱对人类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这样一个根本准则。在我国迫切需要发展高科技的今天,高起点地处理这一问题,是十分重要和具有远见卓识的。21世纪,科技对我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精辟论断之后,江泽民同志继而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国从来不会像21世纪那样更需要科学技术。20世纪末,我国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总体水平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差15~20年,这个差距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尽管我国对科学研究投入资金的绝对量逐年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十分悬殊。发达国家R&D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3%,而我国还不到1%,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70%~80%依靠科技进步,而我国相距甚远。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加速对科技的研究和运用,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但同时我们也应吸取唯科学主义的教训,不能使科技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却危及人类自身的长远发展。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伦理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当科技的力量足以克服可能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时,人们依然会笑纳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春天。
收稿日期:2001-0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