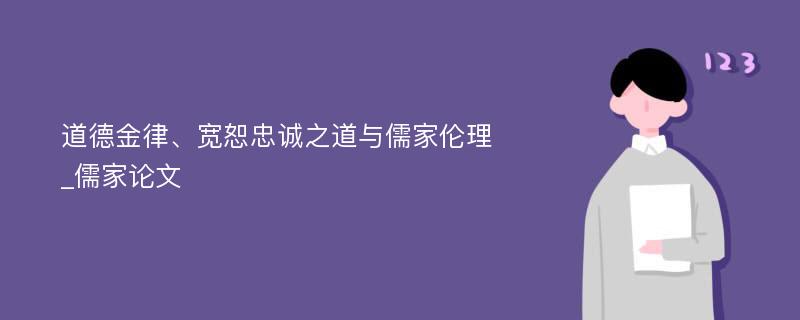
道德金律、恕忠之道与儒家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之道论文,伦理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在古典西方的基督教伦理学还是在传统东方的儒家伦理学中,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一直被视为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第一准则(注:应当指出有关道德金律的思想不仅仅出现在西方基督教与东亚儒家的道德哲学中,它还以各各不同的形式分别出现在诸如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等其它宗教文化中。有关道德金律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表现的讨论,参见罗斯特(H.T.D.Rost)的《论道德金律》(弃治·罗纳出版社, 1996)和布鲁斯·阿尔顿(Bruce Alton)的博士论文《考察道德金律》(密西根大学微缩软件中心。1996), 尤其是第一章。 杰弗锐·瓦特(Jeffery Wattles)的《论道德金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对西方历史上有关道德金律的探讨作了迄今最为详尽与系统的介绍。)。在西方,这一准则又被称为道德金律。然而,在过去的两百年间西方主流伦理学的讨论中,这一金律似乎逐渐失去了它往日的金辉与尊贵的地位,它屡遭冷落,不再被视为伦理学的第一律令。例如,在著名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中,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反对将道德金律与他的普遍绝对道德律相提并论。在康德看来,传统的道德金律不可能也不应当作为人们道德伦理行为的基石。相反,道德金律只能按照普遍绝对道德律的精神进行修正与限制,它只有在接受了普遍绝对道德律的检验之后方可作为一有效的道德准则发挥作用(注: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哈克特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参见芬格莱特:《美国宗教学术杂志》1980年第57期,第388 页。)。英国哲学家,西方近代主流伦理学的另一重要代表密尔(John Stuart Mill)尽管没有直接摒弃道德金律作为伦理学的第一律令,但也毫不犹豫地认定基督教道德金律应当被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取代(注:参见密尔:《功利主义》,哈克特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为什么道德金律在近代伦理学中丧失了它原先的黄金地位?本文的研究力求指出,在西方基督教道德金律内部实质上隐含着两条相互矛盾与冲突的原则,即普遍公正原则与人际间关爱原则。这两条原则曾在基督教伦理学中借助于超越性上帝的绝对之爱的观念达成一种和谐与平衡。随着近代上帝绝对神的权威的被削弱与被怀疑,道德金律中原本存在着的两条原则间的冲突也就拱显出来,并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上述两原则间的失衡。作为这一失衡的结果,人际间关爱的原则在近代伦理学的思考中被边缘化,而绝对性的普遍公正原则在道德伦理评判中占居了统治地位。所以,所谓道德金律黄金地位的丧失不过是这一冲突及其结局的表现之一而已。此外,绝对性的普遍公正原则在现代伦理学中占据统治与优先地位,并不意味着现代伦理从此找到了坚实的、不可怀疑的根基。这仅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由于传统的上帝或神的唯一性、绝对性地位遭到挑战、动摇与削弱之后,现代人试图取代上帝的绝对地位,再造绝对神时产生的一种幻象。从对基督教道德金律现代命运的讨论反观由孔子首先倡导的恕忠之道(注:儒家的传统表述应为“忠恕之道”。本文采用“恕忠之道”,意在表达孔子对道德金律思想中的“恕道”优先原则,评细讨论请见下文以及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对“忠”的解释强调其个人心理特质而非公众社群特质,用“心中”来代替“中心”作为“忠”的词源学解释。这种解释的优点在于将人类社群生活的道德伦理准则规定为天理,并将这一天理与个体内在的与神秘的人心契合起来,以保证宋儒所倡导的经由尽心、知性、事天的内在超越道路。但这一传统解释的缺陷至少有三点,第一,这一对“忠”的个人心理解释很难在《论语》中找到很强的文本上的支持。第二,这种以个体心理之心与至上天道合一的内在超越道路往往导致儒学难以避免陷入以禅学、心学为代表的佛学唯心主义与神秘主义。第三,这一解释混淆了孔子“忠”与“恕”的界限,从而使得“恕”在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中心地位为“忠”所取代,导致宋儒走向界定“忠”、“恕”关系为“天理人情”“本/未”,“体/用”的歧途。限于篇幅关系,笔者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讨论传统儒家,特别是宋儒关于“忠”“恕”两概念之间关系发展的解释的论题。这一论题将留待另文涉及。儒家“忠恕之道”说法的传统起于曾参的解释。参见《论语》4∶15。本文为,“子曰:“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的这一解释至少在两处伸延了老师的本意。第一,夫子之道包含有“忠”与“恕”两重成份。第二,“忠”与“恕”之间,“忠”为主,“恕”为“次”。这就开了后来儒家解释忠恕关系为“天人”、“本未”、“体用”关系的先河。这里,我并不想置疑曾子的解释可能是儒学史上对夫子之道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解释。但问题在于,是否可能有不同于曾子的,而且也有意义的其它解释存在?笔者在这里的解释不妨可视为一种尝试。),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对伦理学基础的思考路向上的根本不同:与基督教道德金律的神谕本质相违,孔子的恕忠之道从一开始就是人间之道。它没有,也不需要一个超越的绝对性上帝作为保证。由于此,儒家的恕忠之道所倡导的公正就只能是相对的和具体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和普遍的。这种相对的和具体的公正观念,非但不象在传统西方的道德金律中与人际间关爱原则冲突,反之,前者植基于后者之上,这也就是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的真意。所以我认为,正如基督教的道德金律揭示出西方绝对律令型、规范性伦理学的本质,孔子的恕忠之道作为人间之道则彰显出儒家教化型、示范性伦理学的本色。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的讨论将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基督教道德金律的现代命运。第二,道德金律的“真义”。第三,恕忠之道与道德金律。第四,恕忠之道的三重优越性。第五,儒家伦理学的本色。
一、基督教道德金律的现代命运
众所周知,在西方,基督教道德金律的正面表述是:你若愿意别人对你这样做,你就应当对别人做同样的事情。其负面表述为:你若不愿意别人对你这样做,你就不应当对别人做同样的事情(注:这一道德金律的流行表述可以溯源到《圣经》,参见《太福音》7∶12; 《路加福音》6∶31。)。显而易见,这两种表述的基本精神就在于, 我对别人对我行为的所欲所求应当成为我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的道德规准。
现在的问题是,我对别人对我行为的所欲所求真的应当成为我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的道德规准吗?在近代西方有关此问题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这一道德金律至少有两个问题(注:关于这两个问题详细讨论,参见阿兰·葛维兹(Alan Gewirth)的“使道德金律理性化”一文。此文收在《中西部哲学研究集刊》第三集(1978),第133—147页。)。第一,我对别人对我行为的所欲所求与在同一情况下某一他人想要得到的对待并不总是相同的。例如,在我饱受疾病折磨,生命垂危之际,我希望我的医生帮助我实现安乐死的要求,以期我能尽量少痛苦的和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假如我是一个医生,我能假设我所有的病人都有同一愿望,所以我应当帮助他们实现安乐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我能论证安乐死的道德合理性,这一论证也不应当建立在我个人的所欲所求之上。道德金律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即使在我对别人对我行为的所欲所求与某一他人想要得到的对待是相同的情形下,遵循这一原则行事也不能保证永远是道德的。例如,假设我是一腐败的官员,我通过贿赂我的上司谋得提升,再假设我的下属与我是一路货,他也贿赂我,而且我们都认为贿赂与受贿是天经地义,道德上无可指摘。他贿赂,我受贿,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我们知道,这种贿赂受贿双方的一致并不能改变贿赂受贿行为的不道德性。很显然,道德金律作为传统伦理学的第一律,不能允许其内部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有两条途径似乎可以帮助解决上述问题。第一,我们承认道德金律的表述本身不严格,有缺陷,需要对之加以修正。第二,道德金律本身无问题,问题出在我们对道德金律的理解。近代许多哲学家取第一条道路。在他们看来,各人具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历史背景与个人爱好,这些都会给人们带来个人的偏见,阻止我们从一超越个人的公正立场来想问题、干事情。但是,道德金律的本意并不是想让我们从自我出发来决定我们对他人的行为。恰恰相反,其本意是想让我们进入他人的角色,从而超越自我的偏见。从这一考虑出发,倘若所有的人都超越自我的偏见,将自己在想象中置身于他人并扩而广之,我们最终就能达至一普遍与超越的基地,在这一基地上我们建立起对一切人具有绝对规范性与普通有效性的伦理准则。因此,道德金律的真精神不在于它立足于个体或主体的主观性,而在于它力求超出这一主观性,达到一种道德评判上的客观性,不偏不依与普遍性。这样看来,道德金律所隐含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它主张道德评判上的偏颇与主观性,而在于它所主张的规范性与有效性还不够绝对与普遍,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使得偏颇与主观性从后门溜进了道德审判的殿堂。
例如,著名的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享利·司纪韦克(Henry Sidgwick)正是以上述方式批评道德金律的。司纪韦克首先指出, “道德金律的表述方式显然不甚严格”,但是,道德金律所言的真理,“倘若能得到严格地表述,则会得到彰显”(注:参见亨利·司纪韦克:《伦理学方法》,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890年版,第380页。)。那么, 什么是司纪韦克见到的道德金律中的真理呢?司纪韦克说,“当我们中的任何人在评判某一行为对自身而言为正确的时候,他同时隐含着断定这一行为对所有相似的人在相似的情形下都是正确的。”(注:参见亨利·司纪韦克:《伦理学方法》,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890年版,第380页。 )根据这一对道德金律的理解,司纪韦克修正了道德金律并企图给道德金律一更为严格的表述。司纪韦克指出,经过修正的道德金律的严格表述应当为:“对于任意两个不同的个体,甲与乙,倘若他们之间情形的不同并不足以构成不同的道德考量的基础,那么,倘若甲对乙的行为不能反过来同时对乙对甲的同样行为为真的话,这一行为就不能被称之为在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注:参见亨利·司纪韦克:《伦理学方法》,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890年版,第380页。 )”司纪韦克对道德金律的这一修正可以说是得失参半。就得的方面说,这一修正保留并突出了道德金律作为无偏颇性的普通性的道德基本原则的真精神。但就其失的方面而言,这一所谓对道德金律“真精神”的严格表述是以其丧失它在情理道德评判中的“黄金”或基础地位为代价的,因为这一表述充其量不过是康德道德哲学的绝对普通律令的另一变种罢了。
当代美国哲学家马尔寇斯·辛格(Marcus Singer )在这一点上似乎看得比司纪韦克更明白。他在关于道德金律的一篇文章中区分了道德原理与道德规则这样两个概念。道德规则在特定的行为中给予人们具体的道德方面的指导,而道德原理则是作为规则的“规则”来起作用,即它并不告知我们在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哪些是该做的,哪些为不该做的。它仅仅评判哪些规则应该作为道德规范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中起作用,哪些则不该。按照这一区分,在辛格看来,道德金律应当作为道德原理而非道德规则来起作用。作为道德原理,道德金律所弘扬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人们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遵循他们乐于加诸自身之上的同种规则与标准。”(注:辛格:“论道德金律”,《哲学杂志》1963年第38期,第301页。)这也就是说, 道德金律强调的仍是一种形式性的要求,而非实质性的规定。这种形式性的要求隐含着一种普泛性。它不指导具体行为,只评判行为中的规则是否恰当。辛格把他的这种解释称为对道德金律的“一般性解释”。相对于对道德金律的“具体性解释”,辛格的这种“一般性解释”乍一看来,似乎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道德评判的主观任意性,因为现在我们所进行的道德评判所根据的不再是个体主观的好恶和癖性。例如,我不应根据我具有自虐的癖性论证我虐待他人的正当性。这一道德评判立基于带有客观性、普遍性的原则之上。但是,更深一步的思考告诉我们,这种“一般的解释”并非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解决的“推延”,因为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从有限个体出发的道德金律如何确保具体道德规则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是否在道德金律之外,我们还应当再加上什么或立基于什么之上才能达至这种客观性与普遍性呢?倘若如此,姑且不论这种客观性与普遍性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我们还能有足够的自信坚称道德金律为伦理学中的“黄金律”吗?
二、道德金律的“真义”
道德金律在现代伦理学中凋落的命运无法逆转了吗?是否还有其它的途径来“拯救”道德金律?是否上述许多现代哲学家对道德金律的理解从根本上就错解了道德金律的真精神?这也就是说,道德金律的表述也许并不存在不严密或不严格的问题,问题出于我们现代人对道德金律真精神的误解——德国学者依·唯·赫斯特(E.W.Hirst )在他的一篇不长但富于洞见的有关道德金律的文章“论范畴律令与道德金律”中作如是说(注:参见赫斯特:“论范畴律令与道德金律”,《哲学杂志》1934年第9期,第328—335页。)。赫斯特认为,尽管现代哲学中对道德金律的批评提出了对传统表述的种种修改,但这些批评与修改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道德金律所代表的道德哲学的“真意”在于谋求一种“超越个体人格”的“无偏颇”的中性,客观的伦理评判出发点。这一出发点, 用当今著名的美国道德、 政治哲学家托马斯· 奈格(Thomas Nager )的话说就是“无角度的视角”( the
view
from nowhere)(注:参见奈格:《无角度的视角》,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但在赫斯特看来,这种“无角度的视角”是对道德金律的一种片面性的理解。这一理解忽视了道德金律中的另一要素,即道德金律作为“人际间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道德金律所处理的是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一个个经过抽象净化的伦理单位之间的关系。所以,任何经由将具体人格、具体生活情境抽象化的途径来达到普遍化、客观化的改写道德金律的尝试都只能是走入歧途。基于这一对道德金律的理解,赫斯特得出结论:“道德金律与人相关,所涉及的乃是共同体的观念。”(注:参见赫斯特:“论范畴律令与道德金律”,《哲学杂志》1934年第9期,第332页。)
我认为赫斯特对道德金律真精神的讨论至少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第一,赫斯特指出,道德金律将人类伦理道德关系的本质定位为“人际问的”(inter-personal)而非“超人间的”(extra-personal)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话说就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这是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世间关系。正是这一立足点,将道德金律与现代伦理哲学中的其他主要律令,诸如康德学派的“道德普遍律令”,功利主义学派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原则”,契约论学派的“均等原则”区别开来。第二,赫斯特并不简单地否弃伦理学中的普遍性、无偏颇的公正性概念。他的目的在于在道德金律的精神下对之进行重新解释。在赫斯特看来,道德金律所强调的无偏颇性并非建立在作为抽象的人或抽象的道德行为主体之上。道德金律孕育并滋养着实实在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着的无偏颇性”(impar- tialityof regard)。正因为如此,赫斯特有意识地选用“共同体”(unity),而非“普遍性”(universality)来表述道德金律中“普遍的无偏颇性”的思想。
依照赫斯特的解释,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把握道德金律的真精神,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道德金律在近代伦理学中凋落的原因。显然,人际间的关爱与普遍的、无偏颇的公正性是道德金律内部的两项基本原则或要素。这两种要素之间是否以及如何统一与和谐的呢?这个问题被赫斯特称为道德金律的自身的“和谐一致性”(coherence)问题。 一方面,人际间的关爱依据的是个体性原则,另一方面,道德评判的无偏颇公正性依据普遍性原则。道德金律在现代的命运正是由于这样两种内在的、互不兼容的原则相矛盾冲突的结果。因此,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在伦理道德评判中从个体的独特性走向绝对的普遍性以及如何使得那超越个体,无偏颇的普遍性同时又在独特的个体性中显现出来?
赫斯特所建议的目标是人类的生活“和谐一致性”。这种和谐一致性不是少数人之间的,而是作为人性整体的和谐一致性,这一整体展示并激发每个人在其独特意义上的参与。但是,这种作为人性整体的和谐一致性又是如何达到的呢?赫斯特认为这种和谐一致性仅仅在人的世界中是难以达成的。于是,赫斯特引导我们走向上帝的神圣之爱:
“道德金律,无论就其在基督教的框架里,还是在犹太教的传统中,均将对自我和对邻人的爱与对上帝的至爱联接在一起。在这里,行为与天祷结合。至于说到和谐一致性,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致性借助于我们与作为神圣意识、作为理智、作为人格与爱的大全的和谐一致性而达到。”(注:参见赫斯特:“论范畴律令与道德金律”,《哲学杂志》1934年第9期,第333—334页。)
显然,赫斯特对有关道德金律内在矛盾冲突的解决建筑在他对上帝以及上帝的神圣之爱的信仰基础之上。人际间的无偏颇的关爱与和谐一致只有借助于天国的和谐一致与神威方可到达。但是,这种借助于、植基于上帝与天国之爱的人间之爱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如何可能与如何发生的呢?在这里,我们面临如下的问题:第一,并非每个人都是基督徒,都信奉上帝的神圣与普遍之爱的神力,从而不仅爱他的家人,而且无偏颇地去爱他的邻人,甚至敌人。因此,一旦去除宗教的神圣光环,在理论上,赫斯特所建议的道路难以避免以下两重疑难:一方面,就本质而言,倘若没有全善的神性保障,我何以能确定我对他人的“关爱”的欲念和行为永远是“善”的欲念和行为而非可能是“恶”的欲念和行为?另一方面,就范围而言,倘若没有全能之上帝的神性保障,我何以能确保我对某个他人的善的欲念与行为也可以同时对一切人、在一切范围内的一切可能的环境下均为善的?赫斯持的解释所隐含的第二个问题不在理论层面上,而在实践层面上。这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假定道德金律的所有施行者都是基督徒,都在理念上信奉我对他人的关爱必须经由上帝和耶稣基督之爱的中介,我们也很难在实践层面上防止道德金律被由于过分强调神性而流于形式和陷于虚伪,从而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作为真正的道德律起到实际的效应。黑暗的中世纪欧洲教会史,应当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足够的教训与借鉴。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有限的、世俗的人类试图拔高自己,扮演无限与超越的上帝角色,接踵而来的大概更多的可能是伪善与罪恶。
上述讨论引导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对道德金律的基督教解释和这一解释的诸现代修正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区别。这两种类型的解释似乎都是通过拔高金律内“神性”的或“普遍性”的因素,即抑或以上帝纯粹的普遍性的、神圣的爱的形式,抑或以超越个体的普遍的、无偏颇性的正义原则的形式来理解道德金律的真意。而与此相应,道德金律内的另一要素,即人际问的关爱,则由于其具有世间的、个体独特性与偏颇性的特征,遭到边缘化。这样,它被贬斥出现代伦理学讨论的主流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恕忠之道与道德金律
我们知道,在中国哲学思想传统中,与西方伦理思想中道德金律所表达的观念相近的是由孔子首先阐发的儒家恕忠之道。鉴于恕忠之道与道德金律在中西各自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对两者以及由这两者所代表的伦理思路之间细致和深入地比较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西方伦理理念本质异同的理解。这一比较也对我们在新时期中对传统道德伦理基础的批判性考察与重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德金律在西方的理解中具有双重因素,即无偏无依的普遍性与人际间的关爱。与此相当,孔子的恕忠之道也由“忠”和“恕”这两个在中国伦理思想传统中极为重要而又相互贯通的观念构成。“忠”这个概念在英文中常常被译为“loyalty”,意为“忠实”、“忠诚”; 在汉语的日常用法中,这一概念作为一重要的道德品性,似可被解释为以规定个体与其在之中的,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历史社群共同体之间的信任与责任关系。根据儒家的理想描述,这一社群共同体不应被理解为社会中本不相干的原子式个人的群集。我们日常就生活在其中并且是其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它是我们由之出发来界定自身的有机整体。基于这一解释,儒家“忠”的概念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其一,尽管“忠”时常以忠于某个个人或忠于某一职守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古时人们常说“忠君报国”,但这里“忠君”仅只是形式,其实质在于始终认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而在古代常由君王来代表的政治、文化,生活共同体——国家。正因如此,绝对的、无条件的“忠”,即“愚忠”,在儒家思想占主导的中国文化中,并非全具褒义,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忠”只是迂腐的象征罢了(注:参见《论语》5∶9,1∶4,3∶9,5 ∶28等。在西方学者中,赫尔伯特·芬格莱特首先观察到,并详细地讨论了“忠”的这一重要社群性质。参见芬格莱特“沿循论语的一贯之道”,载于《美国宗教学术杂志》1980年第57期特刊,第373—405页。大卫·列韦森(David Nivison )在其“中国道德哲学中的道德金律论断”(收入布那恩·凡罗登Bryan W.Van Norden辑《儒家之道——中国哲学研究》,Open Court出版社1996年版,第59—76页)一文中也讨论了“忠”的这一特质。)。其二,忠作为个体对其在之中的生命;生活共同体的认同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加,而是社群中诸个体基于共通文化、历史而出自内心的要求。所以,基于诸个体内心欲求之上形成的“中心”就构成了任一自然社群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基础。忠正是这种个体之心与“中心”相通的表达以及个体之心对社群共同体“中心”认同的要求。忠的这层含义似可通过在古汉语中“忠”字由“中”和“心”两字组合而成表现出来(注: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对“忠”的解释强调其个人心理特质而非公众社群特质,用“心中”来代替“中心”作为“忠”的词源学解释。这种解释的优点在于将人类社群生活的道德伦理准则规定为天理,并将这一天理与个体内在的与神秘的人心契合起来,以保证宋儒所倡导的经由尽心、知性、事天的内在超越道路。但这一传统解释的缺陷至少有三点,第一,这一对“忠”的个人心理解释很难在《论语》中找到很强的文本上的支持。第二,这种以个体心理之心与至上天道合一的内在超越道路往往导致儒学难以避免陷入以禅学、心学为代表的佛学唯心主义与神秘主义。第三,这一解释混淆了孔子“忠”与“恕”的界限,从而使得“恕”在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中心地位为“忠”所取代,导致宋儒走向界定“忠”、“恕”关系为“天理人情”“本/未”,“体/用”的歧途。限于篇幅关系,笔者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讨论传统儒家,特别是宋儒关于“忠”“恕”两概念之间关系发展的解释的论题。这一论题将留待另文涉及。)。
倘若说孔子恕忠之道中的忠表现出社群共同体中个体与社群整体的之间的“向心”关系,恕这一概念则是孔子用来表明应当如何处理社群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心”关系。这说的是,恕就其本质而言,倡导的是我与你之间在我们的社群共同体中的相互关心与爱护的关系。正是这种相互关爱,使得我们的社群共同体成为可能。恕就其实现途径而言,体现在孔子提倡的“能近取譬”,将心比心之中。基于这一理解,恕的概念在孔子那里,其正面的表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参见《论语》6∶28。);其负面的表达则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参见《论语》12∶2,15∶24。)。
十分明显,西方基督教与东方儒家在对道德金律的理解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关于这一点,不少学者有专文论述(注:例如,芬格莱特在“沿循论语的一贯之道”一文中列举了基督教伦理学和孔子对道德金律理解的至少四种显著的相似之处。参见《美国宗教学术杂志》1980年第57期,第375页。)。但是,关于两种理解的差异与区别, 却鲜少有人谈及。在这里,我想讨论两个方面的重要区别。
首先,与传统的解释孔子之道为“忠恕之道”,从而强调“忠”的天道、天理性质不同,我以为孔子之道是建立“恕道”理论基础之上,隐含着恕道优先的原则。这一恕道优先的原则充分展露出孔子之道从一开始乃人间之道的特色。这一特色与基督教道德金律的神道优先的特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基于这一理解,传统儒家的“忠恕之道”理应重新命名为“恕忠之道”(注:儒家“忠恕之道”说法的传统起于曾参的解释。参见《论语》4∶15。本文为,“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的这一解释至少在两处伸延了老师的本意。第一,夫子之道包含有“忠”与“恕”两重成份。第二,“忠”与“恕”之间,“忠”为主,“恕”为“次”。这就开了后来儒家解释忠恕关系为“天人”、“本未”、“体用”关系的先河。这里,我并不想置疑曾子的解释可能是儒学史上对夫子之道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解释。但问题在于,是否可能有不同于曾子的,而且也有意义的其它解释存在?笔者在这里的解释不妨可视为一种尝试。),因为“忠”作为定位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德性,只有在“恕”,即群体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爱关系的基础上方能成立和有效。这也就是说,在相互关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群共同体乃是“忠”得以施行的前提条件。孔子在《论语》中就多次提到这一恕道优先的思想。例如,在《论语·卫灵公15.24》中,“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语·雍也6.28》中,孔子将“恕”的思想表述为“能近取譬”,并称誉其为“仁之方也”。有意思的现象在于,在《论语》这两处极重要的孔子谈论道德金律的地方,竟然都没有提及“忠”字。相反,当孔子在《论语·公治长5.19》中被问到“忠”与“仁”的关系时,他明确指出,仅仅“忠”并不能算是仁(注:参见《论语》20∶20, 5∶28。)。假如我们同意“仁”乃孔于思想中的最核心概念,我们就应该承认作为人际间关爱关系之伦理表达的“恕”应当在孔子对道德金律的理解中占据主导地位。看不清这一点,就会导致我们对孔子道德金律基本精神的误解并从而混淆我们对东西方伦理学思路本质区别的认识。
当今美国孔子研究的著名学者赫尔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教授在探讨孔子道德金律中“忠”与“恕”的关系时, 就对孔于思想中这一恕道优先原则缺乏一种清晰与一贯的认识。在其讨论孔子“忠”与“恕”之间关系的重要论文“沿循论语的一贯之道”中,芬格莱特一方面正确地指出“恕”在孔子之道中占据着一种中心地位,但另一方面,他又断言,“恕”在孔子的道德金律中不可能扮演一种实质性的角色,因为它不可能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原则为我们的道德行为提供实质性的指导。它只是通过要求我们在想象中把自身置入他人之境,从而起着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作用(注:参见芬格莱特:《美国宗教学术杂志》1980 年第57期,第387页。)。与“恕”相较,芬格莱特认为“忠”倒是在孔子道德金律中扮演一种更为实质性的角色,这种实质性乃是由于“忠”的“超越性功能”所决定,因为“忠”要求:“超越……偶然性的与纯粹个人性的欲望、品味、志趣、感受与倾向”。由于“忠”的这种超越偶然性与个体性的性质,按照芬格莱特的说法,“恕”就更应被理解为是一种“辅助性的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个别性与个体性,说它是“辅助性的”,其意义就在于“[恕]可以消融死板、暴政与诡辩。因为它涉及的是作为主体,作为生活经验的活生生的人”(注:参见芬格莱特:《美国宗教学术杂志》1980年第57期,第388页。 )。基于这一理解,芬格莱特得出结论,“‘忠信’使得人类社群生活成为可能,而“恕”则使得这一社群更加人道化。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模仿康德,缺乏恕道的忠信在伦理上是空洞的,缺乏忠信的恕道在伦理上则是盲目的”(注:参见芬格莱特:《美国宗教学术杂志》1980年第57期,第391页。)。
芬格莱特正确地观察到在《论语》中,“忠”这一概念常常与“信”的概念并用。在芬格莱特看来,通过“礼”表达出来的“忠”、“信”,其存在与施行“使得人类社群生活成为可能”。芬格莱特还正确地指出,正是这种通过“礼”表达出来的,作为人类社群生活德性要求与象征的“忠”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初儒家思想中,成为夫子“一贯之道”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芬格莱特在强调“忠”作为“礼”的德性要求在组构、规范人类社群生活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孔子关于“忠”、“信”、“孝”、“悌”这些礼的德性要求应当建立在作为当下直接的人际问关爱的表现的“恕道”基础上的思想。这也就是说,“恕”不应当被认为仅仅具有“辅助性的”和“方法论”上的意义,或者被认为在人类社群生活中仅仅起着一种第二性的调节与缓和的功能。这种第二性的功能,正如宋儒对“忠”、“恕”关系的定位,标明“忠”与“恕”的关系乃是“天理”与“人情”,“体”和“用”的关系。在我看来,在原初孔子的思想中,这种关系似乎恰恰应当颠倒过来。“恕”不是简单作为“礼”的德性要求的“忠”、“信”、“孝”、“梯”的辅助与补充。相反,“恕”乃是,并应当被理解为“忠”、“信”、“孝”、“梯”这些使人类社群生活成为可能的、通过礼表达出来的人的社群德性要求的源头活水。关于这一点,孔子本人看得很清楚。一方面,他十分强调礼在引导、调节人们日常社群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将礼视为静止不动、亘古不变的死板规条,繁文褥节。更为重要的是,孔子还多次明确表明礼的晚起性质与礼乐源出于野的道理。例如,在《论语·八佾3.8》中与子夏讨论《诗》时, 孔子用“绘事后素”来表明“礼”后起的道理。在《论语·先进11.1》中,孔子认为“先进于礼乐”的“野人”甚至高于“后进于礼乐”的君子,这充分展现出孔子礼源出于野,留存于野的思想。因此,离开了“恕”的源头活水,“忠”、“信”就只能成为“愚忠”与“盲信”。孔子的这一恕道而非忠道优先的思想后来成为孟子“民重君轻”命题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应当被视为是孔子、孟子以及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圣贤所留传给我们后人的最重要的哲学文化遗产之一,应当在我们现今重新理解、认识、建构中国文化传统过程中发挥作用(注:强调“恕”在孔子“恕忠之道”中的领先与关键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忽视“忠”和“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相反,这一强调使得我们可能将“忠”、“信”、“孝”、“悌”等社群性德性莫定在更为牢固的生活基础之上。)。
与上面所论述的恕道优先性质相联系,中西方关于道德金律理解的第二点重要区别在于孔子的恕道概念对“身体性质”的强调。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认定人间之关爱源出于、并应当隶属上帝的以及对上帝爱的基本假定不同,孔子的恕道所体现的人间关爱却没有假定这一超越的、神圣的源头。恕道所体现的乃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实实在在的人间之爱。这也就是说,恕道所体现的关爱不是通过上天的神灵,而是借助于世间的身体来实现的。正如“忠”在词源上可追溯到“中”与“心”,可解读为“众心聚集之中央”,“恕”则可以从“如”与“心”来解释。倘若我们可以说“忠”的概念更多地强调“公众之心”的原则,那么,“恕”的概念作为“如心”则更多地在说“个体之心”的原则。无论“公众之心”,还是“个体之心”,忠和恕的立足点都落实到“心”上。我们知道,在中文以及中国古代哲学传统中,“心”的概念首先并不是在西方哲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心灵”(mind)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心首先是五脏之一,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在孔子那里,“心”常常与“欲”、“情”,而非象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常常与纯粹意识、理智能力相联用。例如,在《论语·为政2.4》中, 孔子在谈到他的学习过程时说:“吾……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我们把孔子“恕忠之道”与“心”的关联以及“心”与“体”、“欲”的关系结合起来考虑,“恕道”与“身体”在孔子思想中的关联就变得比较清楚了(注:参见《论语》5∶12,6∶28,12∶2,15∶15,15∶24。)。 点明孔子恕的概念的身体性质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与把捉孔子恕忠之道的人世间本质。换句话说,孔子所理解的、建立在“恕”与“忠”基础之上的道德金律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什么神圣的“天条”,而是源于人,为了人,成于人的人间之道。这与西方基督教传统对道德金律的理解中将人间的关爱隶属于神圣的上帝普适之爱的出发点截然不同。至于这种植基于神人隶属关系之上的爱,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有过一句一针见血的评论:“我从未为了我的邻人的缘故去爱我的邻人。我爱他仅仅是因为这里体现神的恩泽。”(注:参见阿伦特:《爱与圣奥古斯丁》,娇娜·司各特与娇梯·斯达克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四、恕忠之道在哲学上的三重优越性
和西方对道德金律的理解比较起来,孔子的“恕忠之道”对道德金律的理解,由于其“恕”作为人际间关爱的优先性与“恕”的身体性特质,在哲学上至少有着三重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第一重优越性我称为存在论上的优越性。在古代汉语中,“体”这一概念同时具有“整体”与“肢体”的双重含义。这在哲学存在论上就隐含一种有机性的“整体/肢体”关系而非机械分析性的“普遍/个别”的关系。由于“体”的这种存在论上的内在关联关系,在实践恕忠之道的过程中,我的心体与周围世界中他人的心体之间就不应有什么无法融通和合的鸿沟。所以古人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假设什么外在于身体、超越出世界的神秘要素或天命来揉合心体。万物本来一体,无需在存在论上先把世界析分,然后再孜孜追问如何方能整合的虚假问题(注:应当指出,这种在存在论上将整个世界万物视为一有机整体的观点并不专属儒家,它可以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各主要流派的共同的存在论出发点。这一出发点在惠施的著名命题“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中得到充分表达。)。正是在这一“整体/肢体”的存在论视野下,我的心与他人的心相通、理解就成为一种简单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只要人类生存一天,这种借助于身体的沟通与理解就不应当在存在论上成为问题。因此,孔子将我自己的“己”理解为“心体”,并将此作为恕忠之道的出发点,显示出孔子对道德金律的理解植基于一种与西方基督教理解不同的存在论基础之上,这一不同的存在论基础,使得孔子的“恕忠之道”得以避免象存在于西方对道德金律的理解中的如何进入“他人心灵”的难题。
孔子的恕忠之道在哲学上的第二重优越性可以被称为认识论上的优越性,这一优越性帮助我们在哲学上避免象西方在对道德金律解释时所遇到的“主观道德论”以及“绝对不偏不依的公正性”的批评与责难。我的心的身体性质不仅在存在论上澄明我的心体与他人心体相互并存、关联的一体性,而且也在认识论上使我充分意识到我自身的有限性质,即由我自己的身体所决定的我的关爱之心的所能、所欲的有限范围。因此,孔子的恕忠之道中的“恕”的概念,作为从我的身心出发,推己及人,就正如美国学者戴大维(David Hall)与安乐哲(Roger Ames)所说,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单向的”,它势必是有来有往的“双向度的”或“多向度的”(注:参见戴大维、安乐哲合著:《孔子思微》,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289页。)。这里有二点值得进一步说明。第一,无论我在我的主观愿望一方面是多么想关心和爱护我的亲人、邻居、朋友、同志、同类,但往往是我的“身体”,而非我的意识更能提倡我作为“自我”的有限性;以及他人作为“他人”的存在之不可替换性。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的“恕”的概念中,从来不应当隐含有将我对自身的愿望强加于他人的意思,即便这是一种在我看来是关爱他人的善意。恰恰相反,“恕”更多地是要求我体察他人的共同存在并尊重他人与我之间的差别,这是因为此种体察与尊重乃是“恕”得以实行的基本前提;第二,“恕”作为一种自我身心的对他人关爱的要求,虽然一方面提醒我们有关自身的局限性,但另一方面也为从我的心体达到他人的心体的“延伸”创造了条件。相对于在想象中将自身虚拟地置于他人之境,“恕”强调“设身处地”,这是一种真正的“延伸”。在实行“恕道”的过程中,我“超越”我的心体以及我处身其中的具体情境的局限,触及他人。在这里,每一个心体都既为“自我”,又为“他人”。既是自我的“自我”,又为他人的“他人”。按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设想的社会理想,倘若一社会群体中的每个心体都承认并遵循恕道,我们就会在这一相互“设身处地”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充满关怀与开放的“公心”或“公众性”,形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局面。当然,这种以开放、关怀为其本质的公众性不可能从植基于绝对权威之上的“一言堂”中导出,它应当是通过双向和多向度的接触、对话、沟通而来的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结果。正是这样形成的公心与公众性,才是使我们人类社群以及其中的诸个体得以生存、繁荣、发展的基础。
与前二重哲学优越性相应,第三重优越性是方法论上的优越性。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孔子在谈到实行恕忠之道的过程中强调“取譬”的重要性决不是偶然的(注:参见戴大维、安乐哲合著:《孔子思微》,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290页。)。但我这里想进一步强调“能近”这个概念在孔子那里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孔子将“能近”与“取譬”联用,并暗示“譬”乃是由“近”而来。什么是孔子所言“能近”的涵义?为什么孔子说通过“能近”与“取譬”我们就踏上了通往仁的大道(注:参见《论语》6∶30。 )?我以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应当从孔子“恕忠之道”的“身体”性质方面来寻找。
在我们日常的汉语表达中,我们常常使用诸如“体会”、“体恤”、“体察”、“体谅”、“体贴”、“体验”等术语来表示我们身体所具有的“认识论”上的或理解沟通方面的功能。所有这些均可被解释为孔子所言的“譬”的不同形式。这些形式指明在实行孔子“恕忠之道”过程中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途径,这些途径在哲学方法论上显然与前面所述的西方道德金律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分析与逻辑推理方法不同。这种种途径,植基于作为身体的人心,引导我们走向直接的、面对面的充满人性关爱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因此,“譬”在孔子的方法论层面上首先既不是指逻辑概念的推理,也不是指心理、移情的想象,因为它们都假设一种纯粹心灵的优先性。“譬”首先说的是作为“身体”的“心”与“心”的能近。这种“能近”乃是不同文化、不同种类、不同环境、不同经历的人类个人相互理解、宽容、沟通、和合的,先于哲学的前提。此外,这种能近并非一种静态的、关于空间位置的说明,它更是一种动态的、心与心之间的靠近过程。这种动态的靠近过程一方面强调“近”与“譬”并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想象中的或逻辑假设中的虚拟位置互换,而更是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实际中的相互交谈与交流。另一方面,这种“靠近”的过程永远只是接近而已,它不可能抹杀差异,达到完全的相同性,这也是由于我们“心”的身体性质所决定。所以,“近”和“譬”作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伦理学的方法论,在其本身就隐含着人类社群生活中不可否认和消解的、因而应当得到尊重的“他人性质”。
五、儒家伦理学的本色:规范性伦理学还是示范性伦理学?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两种有可能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提出的、对孔子关于道德金律的解释的批评。对这两种批评的深入讨论将可能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伦理学的本色。
如前所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传统将恕忠之道作为伦理道德行为以及评判的基础。对这一立场所可能提出的第一个批评在于经过如此解释的道德金律不可能引导我们达至道德评判的普遍性与规范性。而这种普遍性与规范性在西方通常被认为是伦理学的本质要素与特征。正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海尔(R.M.Hare)在他的名著《自由与理性》中所指出的那样,“道德理性有两条基本的规则,即规范性与普遍性。…倘若我们不能使一种规范普遍化,它就不能成为一种应当”(注:参见海尔:《自由与理性》,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9—90页。)。可是,在孔子关于伦理学基础的思考中,这种普适于一切人的行为的普遍性与规范性似乎从未真正成为孔子所关注的问题。孔子及其传人所关心的,更多地倒是一种伦理行为的“共通性”(Communalizability )。正如普遍性这一概念表明西方伦理传统中的神性性质,建立在恕忠之道基础之上的共通性概念则展现出东方儒家伦理学作为人学的本色(注:例如,杜维明教授在其《释中庸》一书中,对此区别作了明确地说明。杜维明说,“与[西方]将既清晰又确定的带有神性的知识作为道德的最后根基不同,中庸强调人类的共通经验应当成为道德秩序所赖以成立的中心”。参见杜维明《中心性与共通性》,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03页。)。正也因为如此,在孔子那里, 道德金律从来不是什么从超越性的上帝那里颁布的绝对律法或命令,而是植基于人心的、考虑到特定人生处境的人间之道。中文语境中“恕忠之道”的“道路”而非英文“道德金律”(Golden Rule)中的“律法”、“规则”、 “命令”的概念,充分显现出“恕忠之道”作为“道德金律”,并非由天而降、尔等我类必得遵从的“天条”。相反,它是根于我心、起于我行的人间之道。这也是为什么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缘由。在这一“弘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靠近,人类的群体生活得以可能。所以,孔子的以“恕忠之道”为本的伦理学并不企求什么超越具体生活的、具有绝对性质的、笼罩着神性光环的普遍性。相反,孔子的“恕忠之道”所要求仅是一种人世间的、建立在社群生活基础之上的相对普适性。这种相对的普适性,一方面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另一方面则强调这种克服固执与随意的自我的途径不可能经由逻辑分析的道路,即通过将“身体性”的自我还原为“纯粹的”、抽象掉任何具体生活和历史情境的、无差别的社会原子的方式来实现。恰恰相反,这“身体性”的、有血有肉的、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与他人关联着的“自我”正是我们每个个人担负“弘道”大任的出发点。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理解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与“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与否弃超越身体原则的无差别的绝对普遍性相应,孔子也不太可能赞同以绝对命令式的“规范性”来表述伦理学的本质特征。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孔子有关恕忠之道的理解来看,孔子所理解的伦理学的本质应当更多地倾向于“示范”而非“规范”,“教化”而非“命令”,“引导”而非“强制”。基于这一理解,有些学者指出孔子的“恕忠之道”主要以“否定性的方式”,而不是象西方基督教的道德金律,主要是以“肯定型”的方式表达自身(注:例如, 罗伯特·艾林森( Robert Allinson)指出, 孔子“恕忠之道”的否定型表达方式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表明孔子避免道德伤害和鼓励道德成长的企图。参见艾林森,“儒家的道德金律:一种否定型的表达。”《中国哲学杂志》1985年第12期,第305—315页。戴大维与安乐哲也持相近的立场,见《孔子思微》,第288—290页。)。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否定”、“肯定”截然二分的说法似乎过于简单与绝对。一方面,正如已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孔子那里,“恕忠之道”也不乏“肯定型”或近似肯定型的表述(注:不少学者认为孔子道德金律思想的肯定型表述可从《论语》6∶30中得到支持。参见芬格莱特的有关论述, 《美国宗教学术杂志》,第377页;冯克兰:《中国哲学简史》,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53年版,第42—3页;陈荣捷:《中国哲学原始著作》,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另一方面,即使孔子的“恕忠之道”大多采取一种“否定型”的表述,这种“否定”也绝不具有严格的、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排它性(注:参见《论语》15∶15。)。所以,真正使得孔子的恕忠之道与西方众多关于道德金律的表述所不同的地方倒并不在于它们的表达方式是肯定型的还是否定型的。“恕忠之道”是肯定型的,但这种肯定并不是“命令式”。“恕忠之道”也是否定型的,但这种否定绝不意味着绝对的逻辑意义上的排除。无论是基督教的道德金律还是孔子的“恕忠之道”,无疑都作为一种人类伦理行为的“范式”而存在,但本质性的区别在于这种范式被理解为“规范”还是“示范”。以孔子“恕忠之道”为代表的示范型伦理学,并不企求从上帝的神性寻求价值的源头。作为人间之道,伦理学乃从人间而来。从古人,从今人,从自己,从旁人所经历的生活事件以及由这些生活事件而设定的“范例”中我们引申出道德、伦理,价值的要求(注:参见《论语》7∶22。 )。这些范例,在我们现今的日常伦理道德生活中,起着一种“示范”的功能,帮助我们判定日常生活中的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忠与奸。它们鼓励、激发、引导、教育民众,而非规定、命令、强制民众去行善事,做好人。正如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参见《论语》2∶3。)。从这一立场出发,以孔子的代表的儒家伦理学,坚持道德并不本于律法或政治权威,不企求什么“千篇一律”。道德基于人心,成于示范教育与自我修养。因此,先假定道德评判的绝对普遍性质与律令规范性质,然后由此出发批评孔子及其伦理学的做法在其根基处至少是值得疑问的。
第二种对孔子关于道德金律思想的可能批评在于置疑孔子所倡导的恕忠之道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这一批评可能会说孔子的“恕忠之道”,仅是前现代中国农业社会及文化生活的产物。作为基本的道德伦理准则,这一原则在古代社会以家庭、村落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中也许十分有效,但这在当今以工业、信息生产、科技更新为特征,以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人为基石的现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已不可能再起到象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那样的实质性效用。因此,“恕忠之道”作为孔子及其儒家传统对道德金律精神的理解,正象西方基督教对道德金律的传统解释一样,是历史的产物,仅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与效用。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以及它的“黄金地位”被现代社会中更高一层的、具有绝对普遍性质和律法规范效应的“普遍正义律”所取代也就成为理所当然和不可避免的。
在我看来,上述批评至少有两方面的缺陷。首先,这一批评植基于现代性的“进步”概念。这一概念预先认定“现代”比“前现代”,“工业城市”比“农业乡村”,“绝对普遍性”比“历史个体性”,“抽象理性”比“具象感性”具有更高的发展层次与优越性。但是,这一预先认定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进步”概念本身并不是无可置疑的。正如我在前面所述,现代伦理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在于它的人间性而非神道性。这一本质特征影响着现代人对当今伦理思想中诸如“正义”,“公平”等基本概念的理解。这也就是说,“正义”、“公平”等现代伦理哲学中讨论的基本价值不是什么自上而下,由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威的天神上帝颁布的神圣律令,而是植基于人心的,在人间生活大地上历史的、文化的生长出来,用以保障和推动人类社群生活持存、繁荣与发展的条件。在现代西方有关伦理道德基础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传统的、在超越人间生活的“天空”寻找人类道德价值根基的企图。道德价值规范的“普遍性”离不开人间生活的“大地”。 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伦理哲学教授迈克·瓦尔策(MichaelWalzer),在他的《厚和薄:内与外的道德论断》一书中批评传统思想将伦理学视为从“薄的伦理学”(即从简单的,具有绝对普遍性与公理性的伦理规则开始),在具体历史实践过程中逐渐到达“厚的伦理学”(即适用上述规则于具体性、特殊性的社会生活)的过程。在瓦尔策看来;一条相反的途径,即由所谓“厚的伦理学”到达“薄的伦理学”也许更能提供真实的、人类伦理发展的图景:
“伦理学的开端是‘厚实’的。这一开端有着一种文化上的整体性与深厚的内蕴。当它遇到具体的情境,需要为了特定的目的说出道德判断之际,它通过‘稀薄化’的方式表明自身”(注:瓦尔策:《厚和薄:内与外的道德论断》,圣母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瓦尔策教授旧日在普林斯顿的同事、当今美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教授则将瓦尔策的观点, 往前更推进了一步。在罗蒂看来,康德所奠定的某些现代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诸如“正义源于理性而忠诚诉诸情感”和“唯有理性方可为普适的、无条件的道德律令立法”,也许仅仅是一些哲学幻觉。道德的本源图像反倒应当是:
“道德不是从律令规范肇端的。道德的开端是紧密相联的某一群体,诸如家庭、民族中的相互信任的关系。道德的行为就是去做象父母子女之间或者象民族成员之间自然而然地相互对待那样的事情,这也就是尊重别人所赋予你的信任”(注:罗蒂:“公义作为扩展了的忠诚”,第七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的讲演,第5—6页。)。
基于这一对道德本源的理解,罗蒂认为在所谓的普遍性公义与区域群体的忠诚之间并无本质性的区别。所谓“忠诚”就是缩小了范围的“公义”,而“公义”则是扩大了范围的“忠诚”。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罗蒂有关“公义”就是在量上扩大了的“忠诚”的观点,但我赞同他所说的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就其本质而言,这两者都植根于人类之间由于身体而相互联接的情感与关爱关系,而这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恕忠之道的思想所要表述的。因此,借助于瓦尔策一罗蒂的理论,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孔子的“恕忠之道”所表达的思想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它应当且实际上也仍旧在我们今天的道德评判过程起着本质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认为孔子“恕忠之道”作为旧时代的伦理学已经过时和不中用的批评所具有的第二个缺点,在于这一批评所依据的是一幅过于简单化的现代社会生活及现代人的图景。用著名社会批判理论家赫尔伯特·马尔康塞(Herbert Marcuse)话来说,这种对现代社会生活与现代人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种“单维度的”。我并不想否认在当今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某种“稀薄化了”的道德,例如强调普遍性与不偏不依的公正性的道德,起着直接的、伦理范式的调节和评判作用,而且这种趋势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延展。这也就是为什么杰诺米·边泌(JeremyBentham )所提出的功利主义的口号“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当作一个(伦理单位),而且仅仅是一个(伦理单位)来对待”在今天如此流行。但是,应当承认,也正是这种把社会生活的人“单位化”与“量化”使得现代伦理学的绝对普遍性与不偏不依性或为可能。但是,这其间的代价是,每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在这里仅仅成了一个或一个可以被计算,被量化增减的“伦理单位”,而非一个“人”。这里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朝两个方向的分化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生活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我越来越多的是作为整个人类的一分子,作为世界公民,作为大街上的一名陌生人,作为信用卡的一个号码,作为计算机网络中的一个网址被认定。这里强调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性,与此相应的道德评判要求则是绝对普遍性与不偏不依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活发展的社群化、私人化趋向。我们看到,这两种趋向并非总是相互冲突的、例如,我的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定并不同时排除我作为家庭群体中的一员,父亲或母亲、丈夫或妻子的身份,作为社会人所惯于称呼的“铁蛋”,或邻里乡亲所认定的“杰姆大叔”而存在。所以,现代社会伦理道德评判过程中对普遍适用性与不偏不依的公平性的强调并不同时意味着象孔子“恕忠之道”所代表的、植基于人类具体群体生活实践的“厚”的伦理学的死亡。恰恰相反,这种强调显示出诸如“恕忠之道”的“厚重伦理学”在人类伦理生活趋向浅薄化的今天,更多地是起着一种默默地,间接性的奠基工作。这也就是说,尽管它可能不再显赫,但它的“黄金地位”是不容改变和不应轻视的。再者,这种强调普遍适用性与不偏不依的公平性的“薄的伦理学”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许多领域的运用并不代表它适用于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如,没有人会责备一位妈妈“不公平”,因为她把最后一盒巧克力糖留给了最喜爱巧克力糖的女儿,而没有将之在女儿与二个儿子之间“平分”。同理,很少有人去责备一位父亲,当这位父亲发现他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一起处于危险境地时决定首先去救他的孩子而不是其他人的孩子。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这孩子的父亲,而这孩子是他的孩子而非许多之中抽象的“一个”。当然,一旦具体情境改变,道德评判所依据的范式也会随之变化。例如,让我们现在假设这位父亲是一战地指挥官,他的儿子恰巧是他部队的一个士兵。假如这位父亲运用他的职权将儿子留在后方,而将其他年轻士兵派往危险的前线,并且他用之为己辩护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轻人是他的儿子。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父亲/指挥官理应在道德受到遣责,甚至在军法上受到惩处。其原因很简单,这位父亲/指挥官在这里混淆了自己的双重身份。不错,他是一位父亲。作为父亲,他有责任在危险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儿子不受伤害。但是同时,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更重要的是一位战地指挥官。他的行为在道德上理应受到遣责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父亲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军官,并且他的儿子主要是作为一个士兵在这种情境中被认同。上述例子表明,当今社会生活具有多种层次,多种领域,每人在其中某个特定的时刻与情境下扮演的角色不同,所以与此相应的道德范式也可能是不同的。相对于不同的社会角色,每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也不尽相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很难划一条清晰的道德界线,决定取舍。古言“忠孝不能两全”就是这种情形的典型例子。然而这种模糊情形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作为较大的社群的成员的认定(例如作为国家的公民)总是要在道德考虑上优先于作为较小的社群的成员的认定(例如作为家庭的成员),或者如同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所断言,根本无所谓道德基础,只要我自由地作出行为的决定并愿意为此负责,任何行为都是道德上正当的。正是这种将现代社会生活以及现代人简单化的倾向导致我们误认为“薄的伦理学”可以替代“厚的伦理学”,导致我们在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混淆作为道德主体与作为法律主体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常常混而为一,立法取代了伦理教育,法庭取代了良心,道德与不触犯法律成为同义语,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也同时成为人们道德行为的最后裁判人(注:本文批评现代西方语境中价值评判的泛法律化的倾向,并不意味作者赞同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运作上取泛道德化的立场。应当同样指出,这种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泛道德化,从而忽视甚至否认社会个体作为公民身份拥有的、无差别的、普遍性平等权利,乃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威权社会中一种普遍现象和弊病。但是,应当看到,就其哲学实质而言,“泛法律化”与“泛道德化”犯得是同样的错误,即是将具有多种层次,多种领域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种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特定的时刻与情境下扮演各各不同角色的复杂人格简单化,单一化的结果。)。
基于对现代社会生活伦理本质的上述种种讨论与考虑,我希望我对孔子的有关“恕忠之道”思想的解释,对中西方关于“道德金律”真精神的理解,以及在这一理解中展现出的对不同思考路向的批判性比较,能够有助于我们对道德与法律的人性基础的把握。道德金律的“黄金本位”并不在于别的,而仅在于它植基于作为“人”的“我心”与“他人之心”。在人心交融之处,人性与德性合二为一,我以为这就是孔子的“恕忠之道”所留给我们后人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注:本文系在英文稿(载Philosophy East & West杂志1999年10月期)基础上修改而成。)
标签:儒家论文; 赫斯特论文; 道德论文; 伦理学方法论文; 论语论文; 孔子论文; 基督教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伦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