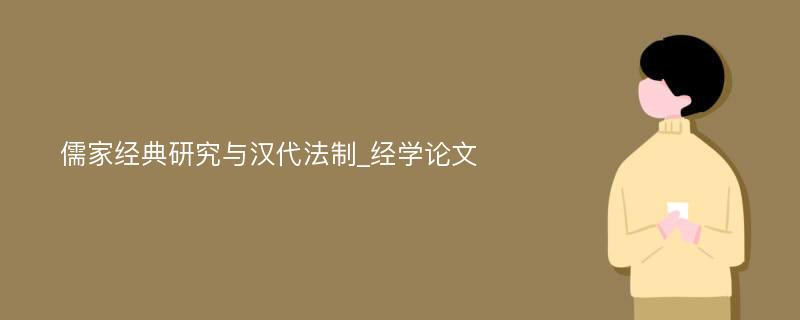
经学与汉代法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汉代论文,法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汉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家经学渗入法律并对它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和记载作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或经义决狱。对经学与汉代法制的结缘及其后果,本文似做一浅探。
作为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秦王朝尊崇法家学说,大搞严刑酷罚,施暴于民,结果二世而亡。汉王朝建立后,总结秦亡的教训,实行“无为而治”,把黄老学说当作制定统治政策的理论依据。但是,黄老学说并不是提倡完全无所作为,而是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与刑名法术之学颇多相通、相近之处。汉初,萧何参酌秦法,作律九章,确定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其后法律条文不断增多,至汉武帝时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又有死罪例13472条。文书充盈几阁,连司法官吏都看不完。刑法繁苛,狱吏上下其手,断狱岁以万数,犯罪者比肩而立,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另一方面,借助于“无为而治”的思想氛围,地方割据势力大肆活动,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扩充实力。即使在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还有一些诸侯王蠢蠢欲动,试图与皇帝抗衡。地方上一些强宗豪右的势力也在迅速膨胀,成为强化皇权,推行统一政令和法律的巨大障碍。很显然,作为指导思想,黄老学说越来越不能适应汉王朝现实政治的需要,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法制建设的需要。
与此同时,儒家经学的影响逐步扩大,其社会政治作用也开始显示出来。经学倡导大一统,主张尊王(君),强调“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经学虽力主仁义德治,反对严刑峻法,但并没有否定法律的功效。特别是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吸收了包括法家在内的诸家思想,提出了德刑并用,德主刑辅的系统理论,统治者可以藉此将德治与刑法结合起来,推行恩威并用,宽猛兼施的统治政策。汉武帝即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汉王朝的指导思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成为统治者确立、实施各种政策和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理论依据,其中《春秋》又受到特别重视。汉代治经儒者继承、发挥孟子的观点,认为孔子作《春秋》,意在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使乱臣贼子惧”,是为后王立法,甚至是为汉代制法。在他们看来,《春秋》的“微言大义”,也就是孔子的政治观念和理想,具有治理国家、纲纪人伦、维护社会秩序的非凡作用,所有政治上、法律上的现实问题都应该而且也能够在其中找到答案。另外,经学尤其是汉代经学中确实有着丰富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内容。而承于秦制的汉代法律制度本身并不完备,利用儒家经义正好可以弥补其缺陷和不足。于是,经学与法制结缘了,《春秋》决狱也应运而生了。
最早运用《春秋》决狱,将经学引入法律之中的,当推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公孙弘。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春秋》决狱的一些原则,后“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①。公孙弘则以《春秋》经义缘饰法律条文,并因此登上相位。另外,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也曾以《春秋》专断淮南王刘安谋反案。在此以后,治经儒者竞相用经学思想对现行法律、刑典加以解释和阐发。班固著《汉书》,设《刑法志》,专从经学之旨立论。马融、郑玄等则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分别对刑律做了数十万言的注疏。
《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或者说经学渗入法律的突出特征,是“原心定罪”(又称“论心定罪”、“原情定过”),即在判案时根据犯罪事实,考察犯罪者的内心动机来定罪。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盐铁会议上,“文学”更明确提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②汉王朝在司法实践中也贯彻了这一原则。哀帝时,薛宣之子薛况雇人刺伤父亲的政敌申咸。御史中丞主张处以弃市之刑。廷尉则提出:“《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结果薛况被减去死罪,改判戍边③。顺帝时,霍谞的舅父宋光遭人诬告而入狱。霍谞上呈文给大将军梁商,称“《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力辩宋光无犯罪之动机和可能,要求明察。于是梁商奏明顺帝,赦免了宋光④。在这里,当事人动机的善恶,成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如果动机是善的,即使触犯法令也当免刑;如果动机是恶的,即使行为合法亦可处以刑罚。那么,如何判断动机的善恶呢?名曰依据儒家经义,实际是依靠司法官吏的主观意志。这就为统治者任意解释法律,滥用各种刑罚开了方便之门。
与“原心定罪”相关联的原则,是“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昭公元年》,意谓凡是蓄意杀害父母、君上而谋乱的,即使并未付诸行动,也当与叛逆同罪。这就是说,只要存在谋乱的念头,就应处以刑罚。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谋反,胶西王刘端奏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⑤新莽时期,皇孙王宗密谋篡位,事泄自杀。王莽为此下诏:“《春秋》之义,君亲毋将,将而诛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乌乎哀哉!”⑥这条原则,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维护皇家威严,是大有帮助的。
“诛首恶”也是与“原心定罪”相关联的一条原则。《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年》:“虞,微国也,曷为序乎大国之上,使虞首恶也。”汉代治经儒者由此将“诛首恶”总结为《春秋》的一条经义,引入法律之中,强调从重惩罚共同犯罪中的“首恶”。董仲舒曾指出:“《春秋》之听狱也,……首恶者罪特重。”⑦成帝时,广汉发生农民起义,太守扈商无力平息。益州刺吏孙宝则亲入山谷,劝说起义农民回归田里。事后孙宝上疏,“奏商为乱首”,强调“《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结果扈商被捕下狱,参与起义者无罪赦免⑧。“诛首恶”与“原心定罪”有关联又有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如何定罪,前者偏重于如何量刑。“诛首恶”原则的运用,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汉王朝既要对危害封建政权的人施以重刑,杀一儆百,又力求多用德教,少用刑罚,使更多的人安心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
此外,经学对法制的影响还表现在“亲亲得相首匿”、“恶恶止其身”、“以功覆过”等决狱原则上。“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隐庇犯罪,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孔子曾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⑨《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也提到:“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董仲舒曾遇一案:甲无子,于道旁拾一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大而杀人,甲藏匿之,他人告甲有罪。董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之,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之。”⑩但是,这一原则在当时并未普遍运用,汉武帝甚至推行首匿相坐之法,父子、夫妇不得例外。直到宣帝时才废除这一法令,“亲亲得相首匿”之法始颁布于天下。宣帝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11)不过,这种首匿仅限于上面提到的几种亲属关系,而且也并非什么罪犯都可以隐庇,象犯有谋反、不道等重罪的即不在其列。凡遇此类案件,其亲属不但不能相匿,反而还得告发,否则将受到严重处罚。
“恶恶止其身”,又称“罪止其身”,是指断狱时只对犯罪者本人进行处罚,而不株连他人。这一原则源于《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汉光武帝时,赵熹为平原太守,会同诸郡讨捕盗贼,斩杀其头目,余党当判刑者达数千人。赵熹上书称:“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光武帝同意了(12)。安帝时,居延都尉范邠犯了贪污罪,按惯例父子两代不得为官。太尉刘恺则提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安帝认为其说正确(13)。然而这一原则与首匿一样,不适用于谋反、不道等重罪。
“以功覆过”,是指犯罪者如果曾对国家有功,审判时可以将功抵过,免于刑事处罚。这一原则主要运用于朝廷大臣犯罪的情况下。其义亦出于《春秋公羊传》。汉宣帝时,大司农田延年因盗取公物,被人告发。御史大夫田广明称“《春秋》之义,以功覆过”,要求大将军霍光考虑田延年在参与拥立宣帝一事上的功劳,给以宽大处理(14)。“以功覆过”使一些官僚士大夫超然于法律之外,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一个具体体现。
汉王朝除了将以上原则运用于定罪、量刑,在确定有关法律的大政方针时,也多以儒家经义为宗镜。如汉成帝感于“律令烦多”,便援引《甫刑》(即《尚书·吕刑》)之语,诏命“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15)。章帝时,陈宠为尚书,称述《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之义,主张“荡涤烦苛之法”,为章帝所接受。后陈宠为廷尉,“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并提议朝廷平定律令,只保留“与礼相应”,“应经合义者,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16)。章帝本人也曾依据《春秋》和《礼记·月令》之义,“咨访儒雅,稽之典籍”,“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17)。安帝时,司徒鲁恭根据《周易·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建议“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安帝同意实施(18)。经学与法制的结缘,还引起了司法队伍结构的变化。专职司法官吏开始留意和重视经学及治经儒者的作用。如汉武帝时廷尉张汤十分器重儒士兒宽,并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参与审理案件。此外还有许多出身狱吏、法律之吏的官员开始亲自研习儒家经典,且用力颇勤,见效极快。如“少学法于父”,“亦为狱吏”的于定国,宣帝时任廷尉,“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19)。又如陈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20)。这就提高了司法队伍的文化素质。与此同时,大批治经儒者直接涌入司法队伍,更使经学迅速渗入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
应该说,儒家经学与法律结缘,《春秋》决狱的出现,使汉朝的封建统治者获得暴力和怀柔这两种统治方法,以充分发挥刽子手和传教士的双重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改变了繁法严诛的局面,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空间,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象兒宽为政,“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得人心”(21)。又如陈宠“为理官,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和)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22)。另外,就法律本身的发展而言,经学介入法律,使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法律的指导思想,并使“引礼入法”开始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法制史上意义重大。然而,儒家经学内容庞杂,派别众多,《春秋》等儒家经典所表达的观念和理论并不象法律条文那样明确,甚至有前后抵牾之处,所在在判案时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解释。再者,《春秋》决狱多是对经学著作断章取义,缺乏固定界说,容易造成同罪不同罚的混乱情况。这些都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侵害了人民的利益,妨碍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魏晋以后,随着经学的政治作用日趋减弱和封建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备,经学对法律的影响尽管依然存在,直接以儒家经义定罪、量刑的现象虽然仍有发生,但已远不如两汉时期那样明显和普遍了。
注释:
①《后汉书·应邵传》。
②《盐铁论·刑德》。
③《汉书·薛宣传》。
④《后汉书·霍谞传》。
⑤《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⑥《汉书·王莽传》。
⑦《春秋繁露·精华》。
⑧《汉书·孙宝传》。
⑨《论语·子路》。
⑩《通典》卷六十九。
(11)《汉书·宣帝纪》。
(12)《后汉书·赵熹传》。
(13)《后汉书·刘恺传》。
(14)《汉书·酷吏传》。
(15)《汉书·刑法志》。
(16)(20)(22)《后汉书·陈宠传》。
(17)《后汉书·章帝纪》。
(18)《后汉书·鲁恭传》。
(19)《汉书·于定国传》。
(21)《汉书·兒宽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