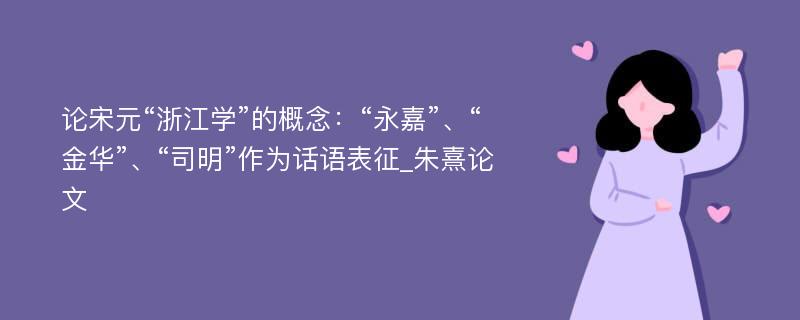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永嘉论文,宋元论文,表象论文,话语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1-0110-06
通过比较探讨《宋元学案》对永嘉、金华、四明学派的评价,以究明其“浙东学术史”观,乃本文之目的。不过,笔者在本文中将《宋元学案》看作是“表明话语之书”,而非“记述事实之书”。《宋元学案》既是一本详细致密的“实证书”,又是一本有时代与地域局限性、从某种视角提出的“意见书”。本文以清代前期浙东地方人士之话语为着眼点,分析《宋元学案》中的“浙学”概念。(注:只是现在还没涉及到该书是许多话语的复合体即带有某种“同床异梦”性这一点。此乃今后的课题。另外,关于《明儒学案》的思想史整理是“江浙”中心主义这一点,小岛毅在他的《中国近世之礼的话语》(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中已有论及,本文也深受启发。)
一
本文力求彻底摆脱关于学派研究的两个“决定论”——暂名为“环境决定论”和“构造决定论”。一直以来,人们在对某一思想学派进行历史性研究时,总指望研究师承关系、交际关系等具体实态。而如果是根植于某一土壤的学派的话,还要对其所处的自然、文化、社会、历史性环境等同时加以研讨。毋庸置疑,这种实态研究至今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也是今后还应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视角也往往隐藏着轻易陷入“环境决定论”的危险性。因为,无论有多少“客观性的事实”,也无法根本说明为什么某思想家热衷倡导某一思想。何况我们所面对的思想学派几乎都没有明确的成员约定和成员名册,所以在具体判定谁是其成员时,后人智慧的介入不可欠缺。纵然再三强调是“客观性事实”,总会有论者的个体意识偏差以及例外的存在吧。
首先,所谓“客观性”的环境与风土是不存在的。奥格斯坦·贝鲁克在《地球与存在的哲学——超越环境伦理》一书中写道:“风土中的一切都与人类的存在相关联。各种事物只存在于人类将自己固有的存在赋予这些事物作为具体内涵之时”[1](p.89);“风土中的一切均因其内涵而产生价值。而且,此种具有生态象征的价值与我们的存在相关联,并向我们发问”[1](p.117)。当时人们之所见和我们所要见的对象既然已经带有“内涵”、“价值”,也就无法认为纯粹的客观性的环境单方面地规定着人类存在的样式。自然环境如此,人的交往、文化传统等社会性、历史性环境也同样如此。
其次,人们在对某一学派进行哲学研究时,往往着眼于甲学派与乙学派思想的构造有何不同。不否认这很有意义,但我以为此种方法有危险性。其危险性在于,“构造”上的不同只不过是后世之人以某一视角抽取出来而已,但我们却将其固定化,并以此替代当时人们的实际感受而加以理解(如,辨别朱熹与陆九渊思想差异之研究的累积,会给人一种印象:他们当时的主张截然相反,关系水火不容),以及以其思想的后世评判来加以整理(如,朱熹的学问后来成为系统性学术理论,或者说现代人往往认为他的学问在思想构造上较为优秀的事实,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当时他一直领导着思想领域)。
毋庸赘言,《宋元学案》是一部恩泽于后世的优秀的思想史著作。然而,本人认为,它还是陷入了以上所述的“两个决定论”中。因此,我们今天避免重蹈覆辙,自觉地、策略性地利用此书尤为重要。
那么,怎样才能不陷入“两个决定论”呢?这不是一个能简单回答的问题。本文尝试性地导入“话语”、“话语表象”、“故事”等视点。这里,并非单纯地将“浙学”、“永嘉学”等视为“客观性事实”,而是作为“话语”,“话语表象”和“故事”来处理的。“话语”是产生于具体环境中的语言意义上的“话语”,“话语表象”是集合性意识以话语来表述,“故事”是传达、解释事态。当然,“浙学”、“永嘉学”等孕育于“浙东”、“永嘉”……我们无法将它们隔离于那些土地加以论述。但是,那些土地在被提及时已非等价于位处中国浙江省东南部的那些土地。人们在谈论它们时,其言下集结的是各自心怀的“浙东”、“永嘉”……也是作为所谓“内涵”、“价值”的“浙东”、“永嘉”……因此,在对作为“浙东”、“永嘉”……的学问之“浙学”、“永嘉学”加以研讨时,就无法无视当事人在使用这些语言时脑里所浮现的形象、听者在闻其言时所产生的价值意识、自发意识以及其语言能成为集团结合原理的力学等东西。我们更需要研究的并不是作为物理性存在的“浙东”、“永嘉”……以及在那里形成的具体实在的士大夫(及他们所编制的网络)本身,而应该是既与它们相关联,又从中游离出来加以刨根问源、添赋内涵的内容。
只是我们不应实体化和固定化地把握这里所说的形象、意识等。我们应该强烈地意识到这些东西是被“表达”的东西。正如野家启一在《叙述的哲学——柳田国男与历史的发现》一书中所说:“某一事件由于被编入了后续发生的各种事件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之中,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叙述文因对其再记叙、再再记叙而使我们的经验地平变得越来越多层化。以此意义而言,所谓叙述文就是‘经验解释装置’,它由现在的展望出发去再释过去,从而使历史性传统的本来面目发生改变。”[2](p.84)“历史性事件只有通过故事的表述才得以确立其作为历史事实的身份。故事通过把想到的各种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并将它们在一定的‘故事’背景中再行配置来架构历史性事实。”[2](p.115)我们所要处理的“形象”、“意识”既是一个“历史性事实”,同时又是已经被讲“故事”过了的东西。本文将以上述观点为依据,对“浙学”、“永嘉学”、“婺学”等进行“话语”、“话语表象”、“故事”的剖析。
二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浙学”一词是南宋朱熹为批判当时活跃在永嘉、永康等地的所谓“事功、功利学派”而提出来的。对“浙东”人而言,“浙学”是一个历史上打着被责难、被辱骂烙印的词汇。“永嘉学”、“婺学”同样如此。但是,大概自元明起,围绕“浙学”的语言环境逐渐起了变化,至《宋元学案》时,其语调明显有了很大的转换。《宋元学案》虽然充分意识到朱熹之批判,然反其道而行,以“浙东”一词来颂扬浙东学术思想的意义。如:
A.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人则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尝从蓝田吕氏游,非横渠之再传乎?鲍敬亭辈七人,其伍人及程门。晦翁作《伊洛渊源录》,累书与止斋求事迹,当无遗矣。而许横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谓为晦翁未成之书,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3](p.405)。
此乃全祖望对北宋时期永嘉地区几代思想家的解说。其特点在于,一是强调了永嘉之学不仅是“洛学”而且还继承了“关学”的学统;二是认为“浙学”的起始在永嘉地区。这种解说在某种意义上已成定论,它对其后思想史的理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疑,《宋元学案》对此这一学术定论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但在以《宋元学案》本身为探讨对象的本文中若以“定论”来考虑问题就无任何意义了。可以说,将当时永嘉地区的思想动向冠之以“浙学”之名全然是一种后智,而且赋予“浙学”以历史生命(尽管是贬义)的始作俑者朱熹本人在“九先生”的时代还未登上历史的舞台。
永嘉地区在这一时期思想大家辈出,这也许是无争的事实。不过,将其理解为“浙学隆盛的开始”和“继承了洛学·关学的学统”是有问题的。“永嘉”并非等价于“浙”,也非脱离了“洛”、“关”就无法存续。将“永嘉”理解为“继承了洛学、关学的学统”、“是浙学隆盛的开始”,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意见”)罢了。
“婺学”的境况也相类似。笔者曾在另文中对“婺学”的概念进行过探讨。若要简单介绍其中一部分探讨成果的话,所谓“婺学”一词:(1)针对婺州人士在吕祖谦死后急于强调“事功”色彩的动向,朱熹心怀畏惧之念,为对其批判而开始使用“婺学”一词;(2)自南宋末至元代,继承了朱熹女婿黄干之学统的“金华四先生”在婺州登场,对“婺学”的认识从“朱熹批判之敌”转变为“朱子学嫡子们之学统”;(3)由于元末明初宋濂等的活跃,此意义上的“婺学”被更加强化,也因方孝孺之死而告终结。
本文所讨论的“浙学”是处于(1)阶段的,朱熹认为“忧人现象”决非只有“婺州”一处,所以使用了此词(因此,我们经常见到的对《宋元学案》混用了“婺学”和“浙学”的批判实在无甚意义)。“忧人现象”在永嘉说来是叶适的抬头,在四明说来是陆学的传播普及。常有“永嘉永康学派”之说,连接永嘉和永康的结合点、催化剂是吕祖谦,而四明陆门与吕祖谦之弟祖俭有密切的交往。祖谦之死与祖俭之“变节”又是朱熹忧虑的最大焦点,由此忧虑而产生了“婺学”或“浙学”的说法。若果真是如此,那么“浙学”问题的构成(或话语表象的“浙学”)也确实产生于此时。
如上所述,《宋元学案》虽充分意识到了朱熹的批判,但反其意而利用之。朱熹忧虑之最大焦点“婺学”的继承者,被赞赏如下:
B.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4](p.215)
金履祥确实是当时令人注目的大儒,算是值得称道的人物吧。然而,坦率而言,没有必须将其称之为“浙学之中兴”的必然性,有的只是在“浙学之中兴”的问题构成中,试图拽住他而已。
另外,刚才还简单触及到了四明陆门。《宋元学案》指出,在四明地区除此以外还有能与婺州比翼的重要学统。
C.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日钞》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渊源出于辅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4](p.394)
在此必须老调重弹,即黄震无疑是南宋末年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将其视为“浙产”,归入“浙学”的脉络只不过是一种“解释”而已。这就是我将《宋元学案》视为“表明话语之书”的原因所在。
三
本人绝对不认为由于《宋元学案》的作者几乎都是“浙”人,所以他们会从狭隘的地缘意识出发,不惜歪曲史实以颂扬“浙学”。此书仍不失为是“公平”、“客观”的“学术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他们想对多样化的现实联上一根脉络时,必定同样遇到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若不明了这一点,也许终究只能再产生同样的故事。
说到“地缘意识”,此书反而很不充分。从以上引用过的资料不难看出,人们认为永嘉不仅传承了“洛学”,而且也继承了“关学”;金华是“勉斋之传”即传承了朱子学;四明与金华同例。关于四明要补充的是,此资料特意介绍“四明之专宗朱氏者”的缘由是因为如前所述,在这片土地上前前后后出现了很多“陆学”的重要弟子。
以上全部内容仅将“浙学”放在与外来的“洛学”、“关学”、“朱学”、“陆学”之相关关系中进行评价而已。这些学派确实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称为胜利者。然而这也难道不是一种后智吗?至少,“受容”了这些学派的浙东思想家们并没有以黄宗羲、全祖望那样的视点来认识这些学派(注:本人不很熟悉中国学界的状况,总体看来似乎到现在仍没克服该视点。给人的感觉是,关于“浙东学术”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只有那些全国有名的、在教科书中有刊载的思想家才受重视。这难道不是根本没认识到“浙东”的独特性吗?)。即他们不是以历史的胜利者,而是以事实上正在不断生成的(似乎很有魅力,但至今仍未完成)同时代者(或者若干先行者)来认识这些学派的。
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西方冲击”说一样,我不得不认为,在论定“浙学”时必须搬出“洛学”、“关学”、“朱学”和“陆学”(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洋之冲击”说,参见Paul A.Cohen:"Disceve-ring History In China",198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日文版)
,佐藤慎一译《智的帝国主义——东方主义与中国像》,日本平凡社1988年版。)。这也许说得有些唐突。简言之,“西方冲击”说认为,西方是永远有“合理性精神”的“赢家”,它所关注的是该“赢家”是怎样动摇了“顽谜”的中国,即怎样“启蒙”了中国。这里,根本就没考虑西方对于中国而言是否真的是重要的存在,人们几乎没有考虑在中国内部有了怎样的带有思想史必然性、内在性变化的胎动。
在浙东,某人可能是二程的或者是朱熹的弟子,也许这在其思想形成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然而,了解程朱学发展结果的人们必须极力避免站在后智的基础上去片面地整理过去的浙东的情况。浙东有浙东的,正确地讲,永嘉有永嘉的、金华有金华的、四明有四明的推动学问隆盛的基础,即应该有过各种各样的知识传统和知识环境。与“浙学”对峙者首先应该弄清这一点。当然,要不断注意避免陷入第一节中所述的“决定论”中。
应该马上补充的是,确实,本人引用了《宋元学案》中实际上记载着的语言,但我这样的操作又仅是一种解释而已。既然《宋元学案》是一个多样性话语的复合体,那么就不能只将此书片面地看成是“颂扬浙学,但为程朱学的观点所束缚之书”。如本文第一条注释所述,对于其复合性将留待今后探讨。在此,想更详细地探讨一下此书是如何来论述“浙学”的。因为《宋元学案》所述的“浙学”虽然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很有意义的“故事”。
第二节中介绍了有关“永嘉”(A)、“金华”(B)、“四明”(C)的资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发现三个问题:(1)将这三个地域的思想动向称之为“浙学”;(2)“程学”、“陆学”等是评价它们的指标;(3)“永嘉”(A)、“金华”(B)、“四明”(C)的关系似乎可以理解为是在一根时间轴上展开的。关于(1)、(2)已多次言及,不再累述。现在就(3)加以探讨。就结论而言,我认为“浙学”这个“故事”是以“永嘉”起始、“金华”中兴、“四明”最终胜利者为线索来描写的。
《宋元学案》对“永嘉学”的兴起描写如下: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5](p.314)
接着是前面引述资料A的时代,即“九先生”的时代。经过这样的积淀,迎来了永嘉学的隆兴。
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艮斋之父学于武夷,而艮斋又自成一家,亦人门之盛也。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然观艮斋以参前倚衡言持敬,则大本未尝不整然。[6](p.50)
永嘉诸子,皆在艮斋师友之间,其学从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斋最称醇恪,观其所得,似较艮斋更平实,占得地步也。[6](p.73)
使永嘉学产生转机的是叶适。
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6](p.106)
“弟子多流于辞章”的结果是,永嘉学(被描写为)趋于衰退。在其后展开中值得评价的是与朱子学合流的一派。
永嘉为朱子之学者,自叶文修公与潜室始。文修之书不可考,《木钟集》犹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学者,渐祧艮斋一派矣。[6](p.506)
嘉定而后,私淑朱、张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4](p.125)
依然有“程朱”中心史观的偏向。虽然再三言及永嘉地区的独自性,但最终还是以程朱学的价值观来整理。其“礼乐制度”、“事功”性的学问对程朱学而言也只有辅助学的作用,“流于辞章”一语甚至将辅助学作用都否定了。
当然,对程朱学严谨的哲学性议论,本人深具敬畏之情,对仅流于辞章的议论实非本人所好。但是,在那样一种“思想信条”和“思想史理解”之间必须在某处划上一线。在永嘉历史上,真的只有过“礼学制度”、“事功”、“辞章”吗?退一步讲,假定除此以外没有过其他存在,那为什么仅有从属于程朱学那样的思想史地位呢?只停留在《宋元学案》的视点上,就根本无法来议论这一问题(注:可能与笔者上述谈的问题意识上出发点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可参见何俊的“宋代永嘉学派的兴起”一文(《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因为他试图从程朱中心史观中摆脱出来,并立足于永嘉地区的思想文化、“历史上的文化因素”来进行分析。)[7]。
接下来是关于金华。有关金华的学统描写如下:
(1)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6](p.356)
(2)东莱学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传而至黄文献、王忠文。一自王文宪,再传而至柳文肃、宋文宪。皆兼朱学,为有明开一代学绪之盛。故谢山云“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云。[6](p.914)
(3)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4](p.217)
(4)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至公而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犹幸方文正公为公高弟,一振而有光于西河,几几乎可以复振徽公之绪。惜其以凶终,未见其止,而并不得其传。[4](pp.299-230)
详细论点暂且不论,与对永嘉学的叙述相比有类似性却是一目了然。在此也被高度评价为是吸收了朱子学的一派,由于流于“文章”而招致了学派的衰退。与永嘉的最大不同可能就是金华有吕祖谦这样的中心点。事实上,他的存在即使在其死后也仍继续给予金华地区以向心力。然而,这也是以朱熹为坐标来对他展开叙述的。
那么,四明又如何呢?(注:可能写不完整,因为在对“四明”进行探讨时,遇到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到现在为止所列举的事例有很多是使用“永嘉”等关键词搜索网上已公开的《宋元学案》的数据库得来的。关于“永嘉”、“婺州”基本能用此方法得到满意的事例,但“四明”、“甬上”、“甬东”、“明州”等使用各种方法检索都行不通。某种意义上说,作为“话语表象”即思想史上的商标,它比其他二地缺少凝聚性。反言之,似乎有融通性。)如前已引全祖望所述,出现了“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的状况。继所谓“庆历五先生”(注:关于发端于他们的四明地区之学问传统,参照佐藤仁“全祖望撰《庆历五先生书院记》考”载方祖猷等编《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的活跃之后,是前面提及的“四明陆门”及黄震等的活跃了。从此意义而言,“浙学”的“兴起”不只是永嘉,“中兴”也不只是金华了。显然,《宋元学案》的“浙学发展史”构想并没有像本人前面说的“永嘉→金华→四明”图示那么简单。但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是需要时就将永嘉、金华也称作“浙学”而加以颂扬,不需要时就排除“浙学”以突出永嘉、金华。或许这种印象是一些人的后智,他们知道黄宗羲、全祖望在四明地区学问传统的发掘、传承中怎样地倾注了热情。对此,本人将另文对黄宗羲、全祖望思想进行批判性分析。
以上笔者试图对《宋元学案》中“浙学”概念进行话语、话语表象及故事等方面的探讨。以朱熹的批判为起端的“浙学”之概念,被以各种样式引用传承下来。《宋元学案》将其诚实引用并开拓性地进行整理这一点是值得赞赏的。但笔者以为,只要我们今天不从那种视角的框框中解放出来,那就无法真正颂扬这本书。作为那个视角的框框,本文指出了“浙学”这一概念的地域战略部分和《宋元学案》所持的“程朱学、陆学”的中心史观。至于这一指出本身所缺乏的实证性和多样性,有待今后再费时填补。诚望诸方家指正。
[收稿日期]2001-04-19
